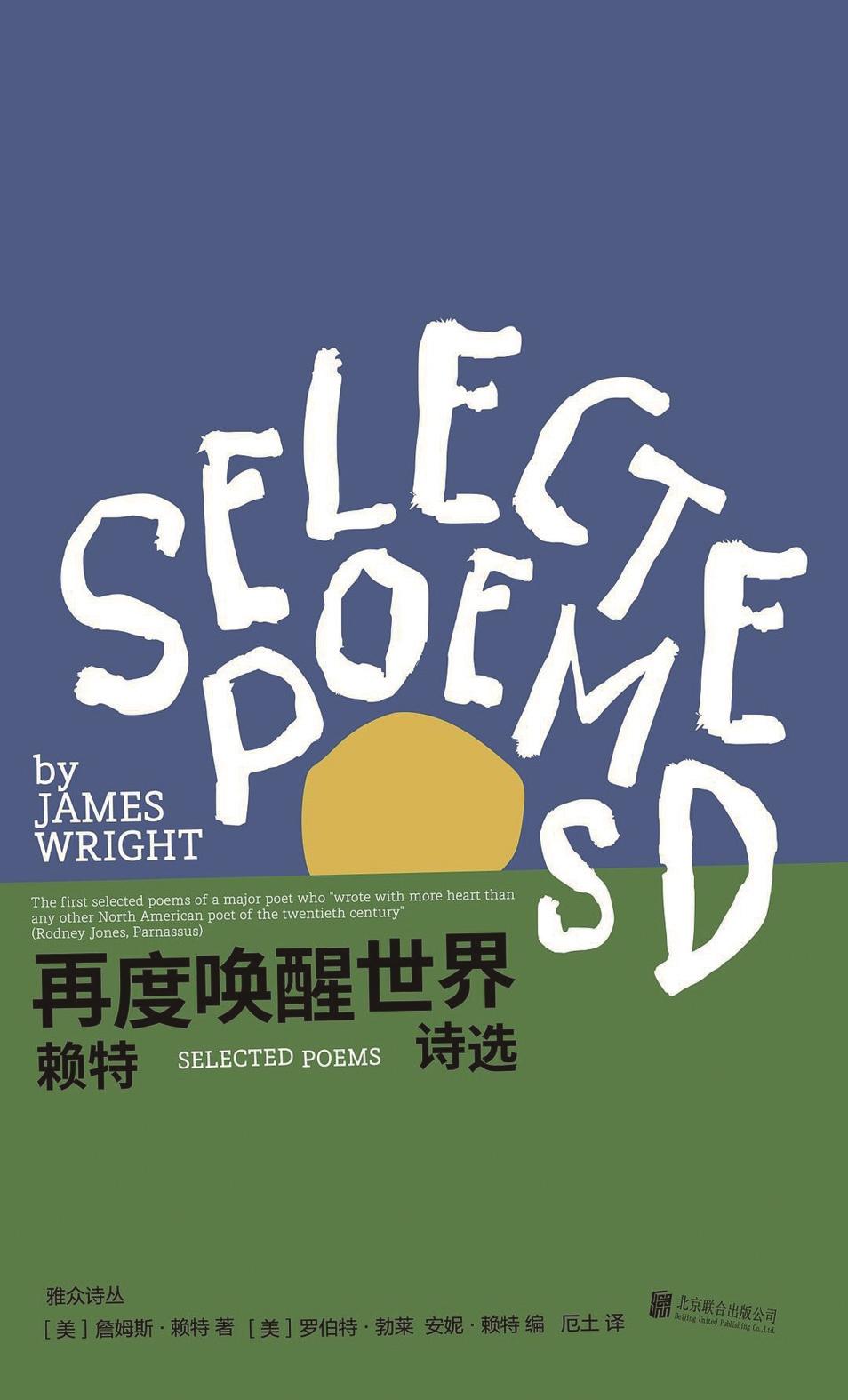□思郁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喜欢上了这首诗,《火旁的两种姿态》,这是一首描述父亲的诗歌,其中最打动我的部分是,儿子回家看到了父亲在火炉旁边酣睡:“今夜,俄亥俄,我曾/追逐和诅咒自身孤独的地方/向我展示我的父亲,打碎过石头/和巨大机器搏斗并掌控之的父亲/如今他休息了,可爱的脸庞在阴影里”。诗歌中的父亲奋斗了一生,开始衰老,他曾寄希望于儿子,但孩子归来时,并未带来荣耀。
这首诗的作者是美国诗人詹姆斯·赖特,诗歌选自他的诗选《再度唤醒世界》,这是在他去世后,他的妻子安妮·赖特和他的好友、著名诗人罗伯特·勃莱从赖特出版的众多的诗集中精选出了八十二首诗歌的选集。
赖特的一生足够波折,他于1927年出生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马丁斯费里,父亲在小镇上的一家玻璃厂工作了一辈子,母亲是一名洗衣店工人。赖特的名篇《在被处决的谋杀犯墓旁》开篇就是这样的自述;“我名叫詹姆斯·阿灵顿·赖特,出生/在离这方不洁的坟墓二十五英里远的地方/在俄亥俄的马丁斯费里,一位/黑兹尔-阿特拉斯玻璃厂的奴隶成了我的父亲/他试图教导我善良。”
赖特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二战结束后,就读凯尼恩学院,师从新批评学派的著名诗人和批评家约翰·克兰·兰色姆。赖特很早就对诗歌感兴趣,他对诗歌的痴迷贯穿了一生。他不断地写作、翻译,编杂志,从世界性的诗人身上吸取各种营养,这种沉淀最终都体现在那一首首风格各异的诗歌上面。他对文学的热情,也体现在他非凡的记忆力上,在《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中,赖特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随口可以吟诵那些大段的诗歌和散文,基本上不会出错。勃莱也回忆说,有次读诗会后,某位英语教授嘲讽赖特根本不懂英语文学,赖特回击的方式就是当场一字不差地背诵了《项狄传》的最后一章。
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访谈者询问有哪些诗歌是他一气呵成的。赖特提到了两首诗,一首是《父亲》,收录在他的第一本诗集《绿墙》里,另外一首是《祝福》,收录在我最喜欢的那本诗集《树枝不会折断》里。他还说,“如果你问我,它们从何而来?我或许只能答道,我怎么知道?作为一名诗人,有时,你得任由自己被生活摆布,但生活并不总是仁慈的。”
赖特的一生深受抑郁症和躁郁症的困扰,高中的时候就曾精神崩溃过,接受过电击治疗。他的第一段婚姻触礁,跟自己的孩子分隔两地,他长期陷入到酗酒的困境之中,他一生都在抽烟,最终查出了舌癌,1980年去世。这种负面的情绪在他的众多诗歌中都有所折射,很多挑事儿的批评者甚至故意挑出他的诗歌中使用黑暗的词汇的频率有多高。
如果让我选这本书中最喜欢的诗歌,我会选那首《火旁的两种姿态》,如果让我选最喜欢的部分,我会选《树枝不会折断》。这也是赖特的诗歌代表作,这部分的诗歌都写得简洁、清晰、富有感染力,自由自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版后,震惊诗坛,很多评论者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评价,称之为一种“超现实主义”。这大概是我看到最荒唐的一个评价,这怎么是超现实主义呢。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比如这首《又到乡间》:“那座白房子静悄悄/朋友们还不知我已来到/生活在田边秃树上的啄木鸟/啄击一下,寂静良久/我静静地伫立在暮晚里/转过脸,背向太阳/一匹马在我长长的影子里吃草”。
赖特翻译过很多诗歌,喜欢从很多海外不同文化和国籍的诗人那里寻找灵感,而中国的古典诗歌恰好是他的诗歌写作源泉之一。稍微对中国诗歌有所了解的人都该知道,这更接近中国的古典诗歌中最常见的那种田园诗,贴近自然,富有禅意。如果非要用个术语概括评价这种诗歌,大概就是一种中国古典现实主义。
我非常喜欢赖特对诗歌的一种描述,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他说,一首诗不仅是一件可被创作的、构思精美的独立作品,而且诗歌也是一种可以被不断创作甚至几乎可以实现一种自我再造的事物。
赖特说,诗歌是一种类似春天的事物。这是对诗歌下过最美的一个定义。
■好书试读
很久以前,人们坐飞机时还常常会跟邻座旅客搭讪。有时会有人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可能回答说:“我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主要跟有暴力倾向的罪犯打交道。”于是,微微的好奇很快变成了惊讶:“你是说,你真的会跟那些人谈话吗?”随后,可能会引出一通即兴的感叹,比如,为这种“魔鬼”而“费心”是一件“多么不值得的事”。还有更过分的,比如会不解地反问:“可是这种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他们难道不是生来就那样的吗?”这时,这位只是碰巧与我同行的英国旅客可能还会凑到我的耳边,压低声音补上一句:“坦白说,我认为议会应该恢复绞刑。”
如今,上飞机后坐下来系安全带时,要是邻座再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会说我是一位花店老板。
——《深渊回响》
[新西兰] 格温·阿谢德
[美] 艾琳·霍恩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获得家教工作不只需要熟悉关于德国统一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了解这群居住在第五大道的焦虑的人。
也就是说,仅仅上过哈佛、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还不够。我即将进入的这个世界不允许肥胖的存在,没有人会发型不整,甚至老师都穿着德尔曼平底鞋。在这里,没有痤疮的重要性不亚于阅读过乔治·艾略特作品全集。
我的第一个学生是15岁的苏菲。我们见面那天,她像一阵旋风一样从铺满纯白地毯的豪华旋转楼梯上跑下来。这座位于纽约公园大道的复式公寓洁白无瑕:陈列着白色沙发、白色长绒地毯,两只白色的迷你贵宾犬围绕在苏菲脚边狂叫不止。
——《我在上东区做家教》
[美] 布莱斯·格罗斯伯格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