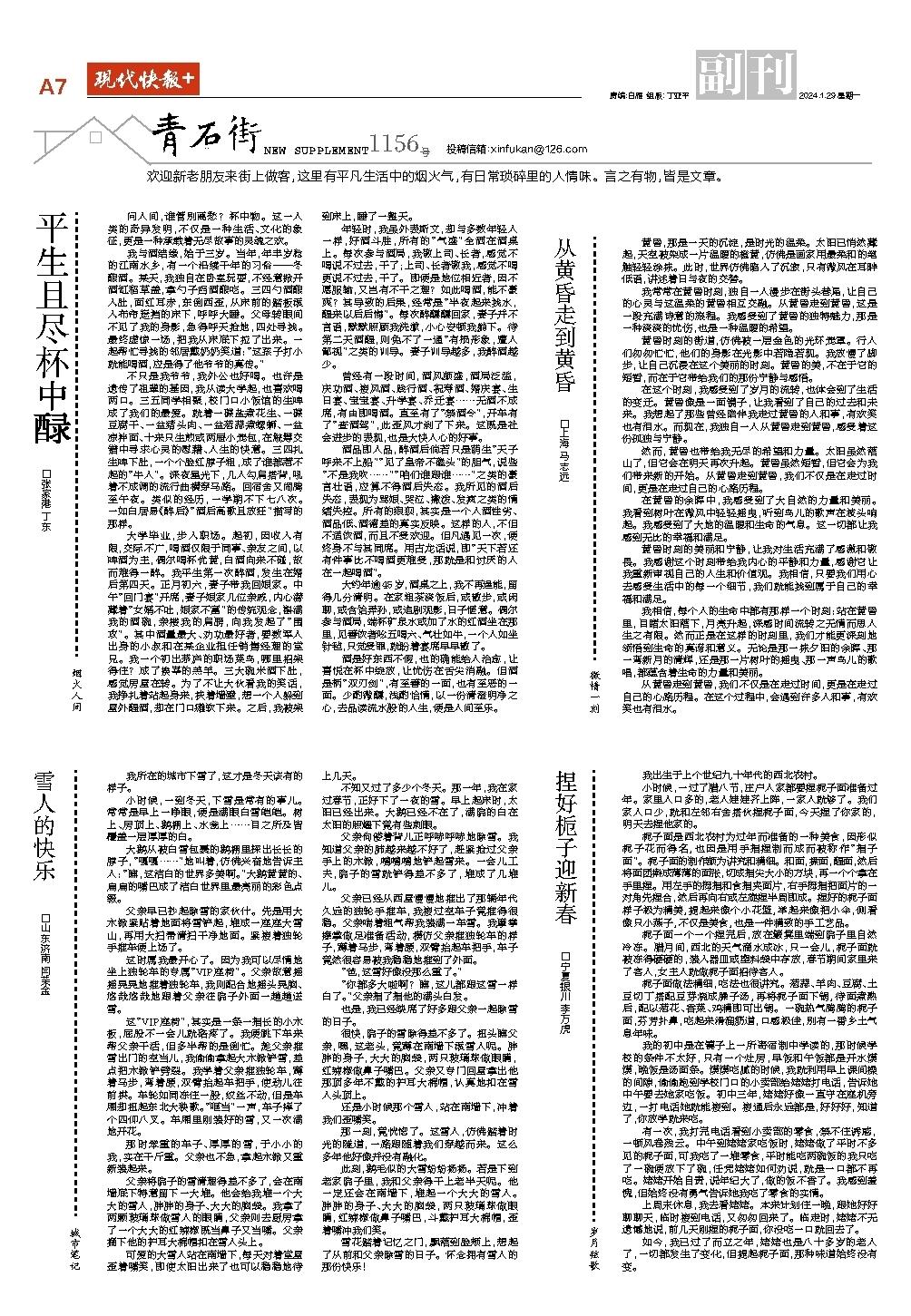□山东济南 闫荣金
城市笔记
我所在的城市下雪了,这才是冬天该有的样子。
小时候,一到冬天,下雪是常有的事儿。常常是早上一睁眼,便是满眼白雪皑皑。树上、房顶上、鹅棚上、水瓮上……目之所及皆覆盖一层厚厚的白。
大鹅从被白雪包裹的鹅棚里探出长长的脖子,“嘎嘎……”地叫着,仿佛兴奋地告诉主人:“瞧,这洁白的世界多美啊。”大鹅黄黄的、扁扁的嘴巴成了洁白世界里最亮丽的彩色点缀。
父亲早已抄起除雪的家伙什。先是用大木锨紧贴着地面将雪铲起,堆成一座座大雪山,再用大扫帚清扫干净地面。紧接着独轮手推车便上场了。
这时属我最开心了。因为我可以尽情地坐上独轮车的专属“VIP座椅”。父亲故意摇摇晃晃地推着独轮车,我则配合地摇头晃脑、悠哉悠哉地跟着父亲往院子外面一趟趟送雪。
这“VIP座椅”,其实是一条一指长的小木板,屁股不一会儿就硌疼了。我便跳下车来帮父亲干活,但多半帮的是倒忙。趁父亲推雪出门的空当儿,我偷偷拿起大木锨铲雪,差点把木锨铲劈裂。我学着父亲推独轮车,蹲着马步,弯着腰,双臂抬起车把手,使劲儿往前拱。车轮如同冻住一般,纹丝不动,但是车厢却扭起东北大秧歌。“哐当”一声,车子摔了个四仰八叉。车厢里刚装好的雪,又一次满地开花。
那时笨重的车子、厚厚的雪,于小小的我,实在千斤重。父亲也不急,拿起木锨又重新装起来。
父亲将院子的雪清理得差不多了,会在南墙底下特意留下一大堆。他会给我堆一个大大的雪人,胖胖的身子、大大的脑袋。我拿了两颗玻璃球做雪人的眼睛,父亲则去厨房拿了一个大大的红辣椒既当鼻子又当嘴。父亲摘下他的护耳大棉帽扣在雪人头上。
可爱的大雪人站在南墙下,每天对着堂屋歪着嘴笑,即使太阳出来了也可以稳稳地待上几天。
不知又过了多少个冬天。那一年,我在家过春节,正好下了一夜的雪。早上起床时,太阳已经出来。大鹅已经不在了,满院的白在太阳的照耀下竟有些刺眼。
父亲佝偻着背儿正呼哧呼哧地除雪。我知道父亲的肺越来越不好了,赶紧抢过父亲手上的木锨,噌噌噌地铲起雪来。一会儿工夫,院子的雪就铲得差不多了,堆成了几堆儿。
父亲已经从西屋慢慢地推出了那辆年代久远的独轮手推车,我接过空车子竟推得很稳。父亲喘着粗气帮我装满一车雪。我摩拳擦掌做足准备活动,模仿父亲推独轮车的样子,蹲着马步,弯着腰,双臂抬起车把手,车子竟然很容易被我稳稳地推到了外面。
“爸,这雪好像没那么重了。”
“你都多大啦啊?瞧,这儿都跟这雪一样白了。”父亲指了指他的满头白发。
也是,我已经缺席了好多跟父亲一起除雪的日子。
很快,院子的雪除得差不多了。扭头瞧父亲,嘿,这老头,竟蹲在南墙下滚雪人呢。胖胖的身子,大大的脑袋,两只玻璃球做眼睛,红辣椒做鼻子嘴巴。父亲又专门回屋拿出他那顶多年不戴的护耳大棉帽,认真地扣在雪人头顶上。
还是小时候那个雪人,站在南墙下,冲着我们歪嘴笑。
那一刻,竟恍惚了。这雪人,仿佛踏着时光的隧道,一路跟随着我们穿越而来。这么多年他好像并没有融化。
此刻,鹅毛似的大雪纷纷扬扬。若是下到老家院子里,我和父亲得干上老半天呢。他一定还会在南墙下,堆起一个大大的雪人。胖胖的身子、大大的脑袋,两只玻璃球做眼睛,红辣椒做鼻子嘴巴,斗戴护耳大棉帽,歪着嘴冲我们笑。
雪花踏着记忆之门,飘落到脸颊上,想起了从前和父亲除雪的日子。怀念拥有雪人的那份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