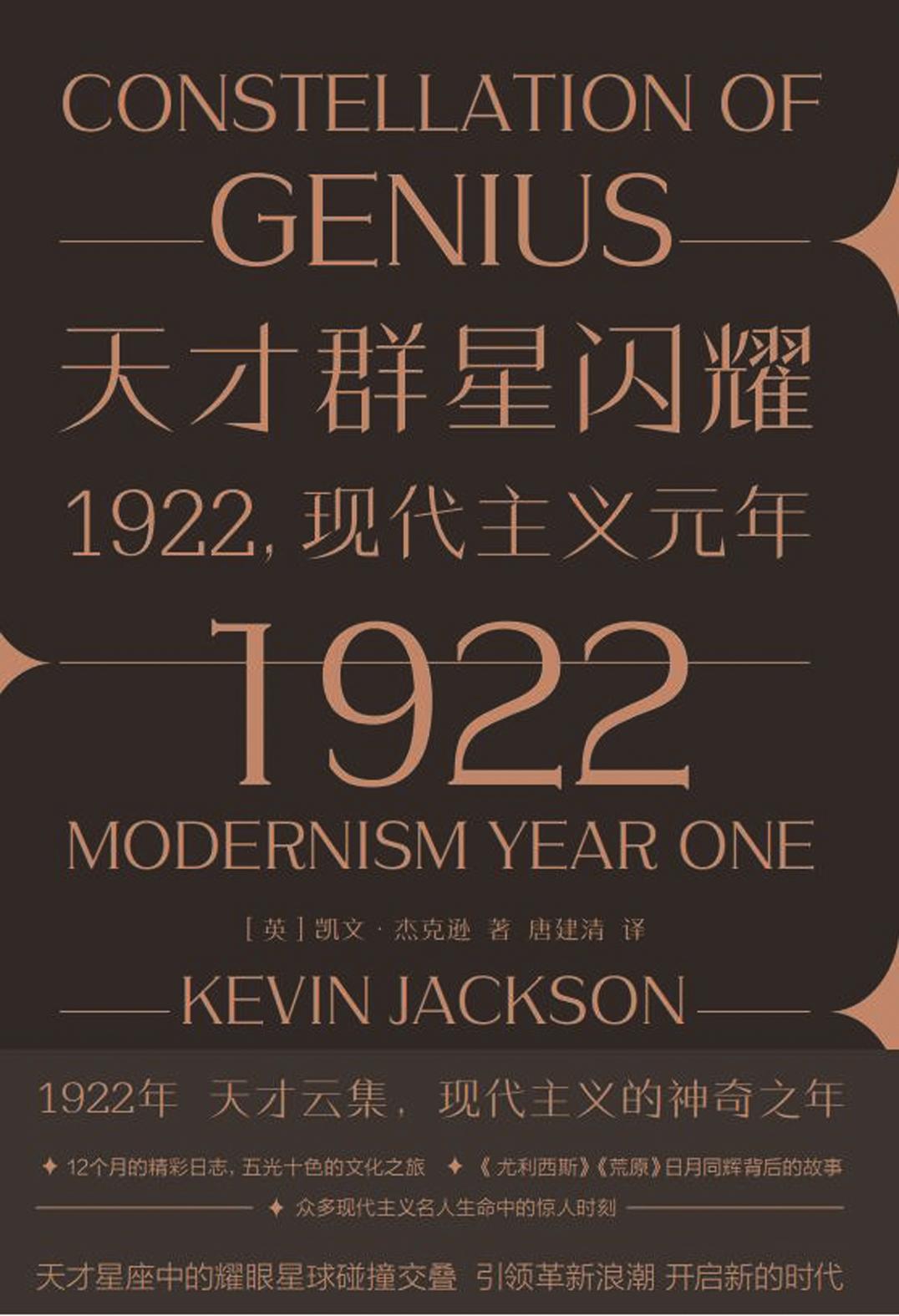□思郁
最好的时代,天才总是成群结队而来。最坏的时代,天才才会孤独前行。
文学史上,有几个时期和文化中心总会被后代人铭记,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纽约。它们的存在构成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正与其中一个时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关,这本书叫《天才群星闪耀》,作者是英国专栏作家凯文·杰克逊,讲述了1922年,以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的出版为核心,引发了文学史上一连串的共振效应,催生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诞生。1922年,也被后人称为新时代元年。
新时代元年这个说法,来自诗人埃兹拉·庞德,在他看来,上一个时代已经于1921年10月30日结束了,当天乔伊斯完成了《尤利西斯》的最后几句话。这当然只是一时兴起,也根本禁不起推敲。《尤利西斯》从来没有完成过,如果不是乔伊斯有迷信,想要在他四十岁生日那天出版《尤利西斯》,要不是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西尔维娅·毕奇,强行从他手中收走一直在修修改改的文稿,这本书大概不知道何时才能出版。如果艾略特没有说服他的资助人为文学季刊《标准》出资,在上面刊发他的长诗《荒原》,那么他的诗作出版大概也会延期。当我们考虑到这么多偶然性的因素,总会下意识怀疑庞德夸大了1922年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抽身回望,又不得不佩服庞德敏锐的判断。因为1922年,原来有这么多值得记录的经典出版。
稍微略举一些。1922年,卡夫卡开始写作《城堡》;里尔克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两首组诗《杜伊诺哀歌》和《致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海明威正在通过新闻报道的写作摸索他的写作风格;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出版了《美丽与毁灭》和《爵士时代的故事》;尤金·奥尼尔的戏剧《白猿》开演,总共演了127场;乔治·奥威尔刚刚从伊顿公学毕业,他要加入缅甸的印度帝国警察部队;纳博科夫的父亲被枪杀,在柏林流亡的纳博科夫开始用“西林”的笔名发表作品,当年出版了四本书;福斯特正在写他的《印度之行》;T.E.劳伦斯完成了《智慧七柱》;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出版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改变了人类学的学科研究;伊迪丝·华顿出版了备受期待的小说《月亮的隐现》,三周卖了六万册;普鲁斯特在修改《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一卷时去世;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巴比特》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出版,第一次印刷就高达八万多册,最终加印到了百万销量……
当然,这并非全部,我们要知道,文学从来不简单地发生在文学领域。那个时代从来不单单是文学繁荣的时代,奥斯曼帝国的消失,爱尔兰内战爆发,意大利的法西斯抬头,列宁中风,苏联大饥荒,斯大林上台,英国广播公司成立,埃及的图坦卡蒙墓被发现,等等。杰克逊在书中不断地列举当年发生的事件,某种意义上,跟文学艺术的诞生形成了一种呼应。现实的复杂和混乱,制造了某种自由的缝隙,催生了一个精神上反叛时代的诞生。
《尤利西斯》和《荒原》,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主义的文学经典,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精神的象征,与这两本书的主题内容都有很大的关系,用杰克逊的原话总结说就是,“让我们尝试想象一下,1922年,一个毫无准备,满足于啤酒、游乐和吉卜林作品的普通读者的反应。突然闯入一个瘦骨嶙峋、衣着寒酸的爱尔兰人和一个整洁而阴沉的美国人,他们一心要炸毁现实主义小说和乔治时代所珍视的一切”。
这还远远不够。无论从任何意义和时代来说,《尤利西斯》和《荒原》都是小众的文学作品,但是争议才是最好的宣传。在这方面,庞德作为这两部作品的幕后推手功不可没。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1922年都是现代主义的奇迹之年,但是正如书中列举的那些大事记,我们也会发现,这也可能是黄金时代的最后余韵。因为随着电报、广播、传真和电影的发明,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即将到来的时代。文学从此之后只有采用娱乐的功效,才能占据我们的一部分注意力。而那些现代主义的文学经典,从此都只是摆在神龛里,供学者们膜拜研究。普通读者,能读完的人越来越少。
■好书试读
有人说他精神失常了,他也曾经怀疑自己是否还正常。如今,尽管他的举止仍然有些古怪,他却感到很踏实、很快乐,内心很通透,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正忙着写信,近乎魔怔,好像是要写给天下的每一个人。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甚至被这些信给深深打动了,从六月底开始,不管去哪里,他总是带着一只手提箱,里面装满了信和信纸。他拎着这只手提箱从纽约来到玛莎葡萄园岛,然后马上又从玛莎葡萄园岛折返,两天之后,他又飞往芝加哥,紧接着从芝加哥来到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一个村庄。他“隐居”在乡下,不停地写信,坚持不懈,写给报纸,写给公众人物,写给亲戚朋友,最后也写给已经死掉的人,死人里面首先是始终默默无闻的自家先人,然后是曾经闻名遐迩的大人物。
——《赫索格》
[美] 索尔·贝娄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要看清鼻子底下的事情,你必须不停地进行挣扎。
——乔治·奥威尔,《就在你的鼻子底下》
关于爱是如何奇迹般地降临于人们的生命,西方文化有无穷无尽的表现方式:被天造地设的缘分击中的那神秘一瞬;期盼一通电话或一封邮件时那亢奋燥热的等待;还有某张面孔浮现在脑海里的时刻,那触电一样扫过脊柱的战栗。陷入爱情就是变得精通柏拉图,要能从一个人身上看到一种“理念”(Idea),完美而整全的“理念”。无数小说、诗歌或电影都在教导我们成为柏拉图门生的艺术——去爱我们所爱之人体现出来的完美。可是,我们小心避免爱上某人或者感到爱意消失的时刻,让我们彻夜难眠的人冷漠甩开了我们的时刻,从几个月甚至几个小时前还一起寻欢作乐的人身畔匆匆抽身离去的时刻——这些时刻同样神秘,但一个可以无休无止地谈论爱的文化却对此失语了。
——《爱的终结》
[法] 伊娃·易洛思 岳麓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