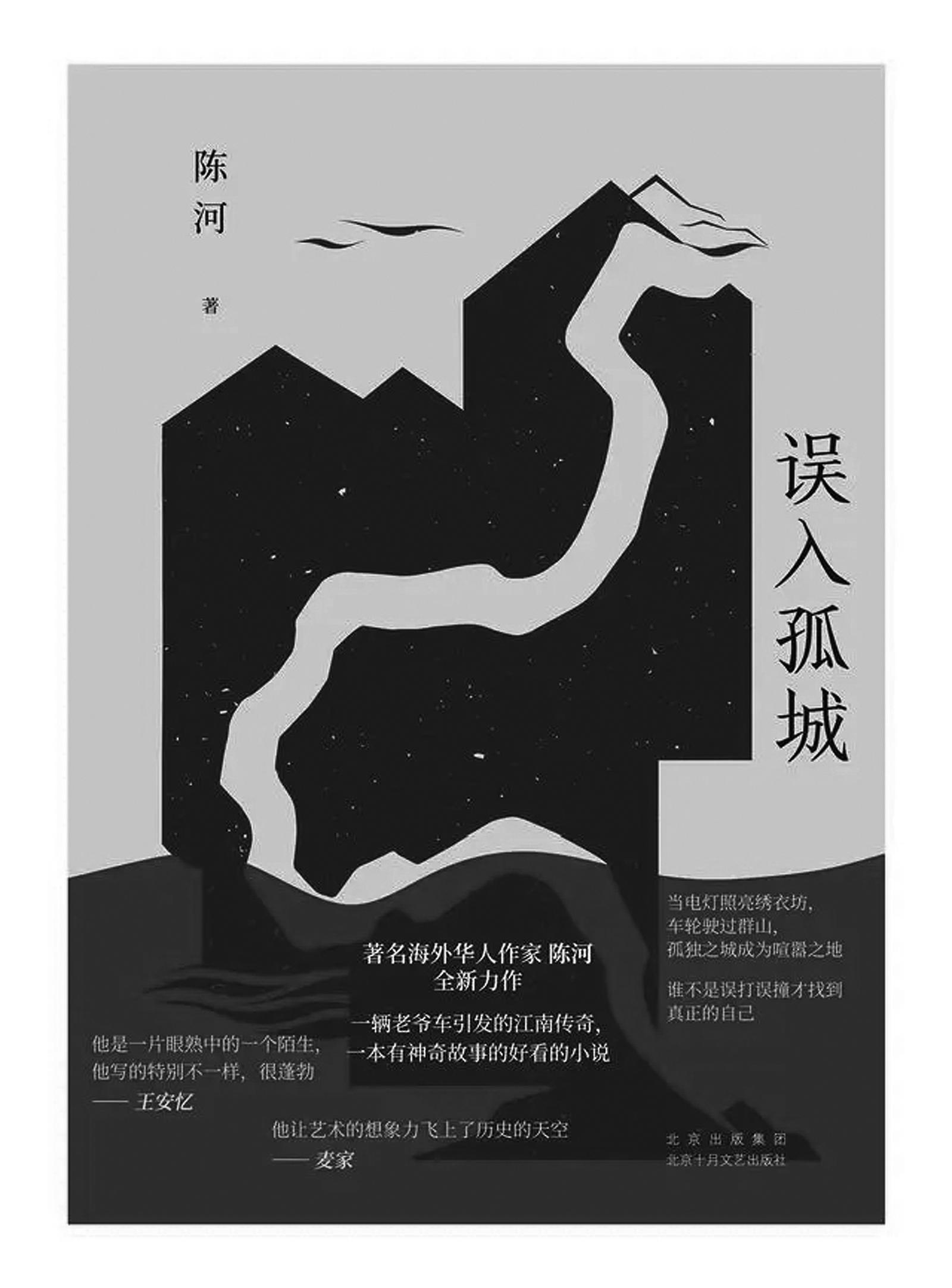□周倩羽
从异域题材到军事题材再到历史题材,出走半生之后,陈河的目光重新聚焦于故乡温州。川流不息的瓯江水,让他汲取了《布偶》《红白黑》《涂鸦》《蜘蛛巢》等作品的创作灵感,但《误入孤城》却是陈河在温州记忆之河中打捞到的一条大鱼,它曾经斑驳的鳞片由隐渐显,成就了一次完全洋溢着故乡气息的精神游弋。
这场游弋以作为外乡人的西北战士,军阀潘师长的司机——马本德的视角切入。小说中,他带着师长的亲笔信,驾驶一辆梅赛德斯越野车,千里奔赴到W城,只为寻找师长女儿潘青禾。随着马本德和汽车的一同“误入”,历史的车轮飞速转动,故事随即展开了对清末民初时期温州现代化进程的书写。字里行间,公路桥梁翻越群山,电器电灯照亮全城,“海晏号”游船熙来攘往,商贾百姓、军人政客等人物悉数登场,上演一场场奇特蓬勃、惊心动魄的历史剧集。
清政府的倒台、北洋军阀混战、残酷的抗日战争,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虽重如磐石,但是在作家神奇有趣的描绘里,故事却足以变成翱翔空中的白鸽、漂于海面的轻舟。小说中这一虚实相融的历史观,正与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提出的“轻逸”说,含有异曲同工的文学趣味。
《误入孤城》的轻逸感,率先来自小说中奇特的文学形象。不难发现,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与观念都极具现代性,循着马本德陌生化视角,我们在看待温州时满怀好奇。远道而来的马本德身上虽充满了原始的野性,却不是困囿于群山环绕的鲁莽蛮夷。他带着对师长及其女儿的忠诚,拆卸汽车跋山涉水来到W城,又“反客为主”投身于那里的公路和桥梁建设,误打误撞中凸显传奇色彩;师长女儿潘青禾不再是安于宅邸的单纯少女,而成了大胆追爱、普济苍生的新文化女性;柳雨农在灯火辉煌下左右逢源、志存高远但又急功近利、如履薄冰,于新旧变革之间摇摆不定;小说中甚至还有作为文学人物出现的朱自清,带着学生们春游写文章……
在《误入孤城》里,不同阶层的人只需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便可建立对话联系。身与身的性爱,是自然而然的生命冲动;新旧思想与血缘族群的碰撞,衍生出复杂深厚的爱恨情仇。小说人物焕发的精气神、旺盛的生命力和温州城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一组巧妙的互文关系。如果说,人物为小说在台前搭建了一座看得见的城市,那么在潜藏的幕后,陈河则苦心孤诣构造了一片可供人物自由穿梭的历史瀚海。这片瀚海既是清末民初确切的温州现代史,又是每个人魂牵梦萦的理想空间与精神故土。
陈河为何将人物的理想与精神都投射到这段纪实又虚构的历史当中?这与作家的个人游历和文学版图密不可分。“写作其实就是写作者不断地给自己的内心图景做自画像。”在《为何写作》一文中,陈河如是说。他的文学版图彰显着着行走于世界的姿态,他个人的世界性体验让温州故事与全球文化背景相融。曾于1994年前往阿尔巴尼亚经商的陈河,在走出国门、历尽千帆后再次回望原乡,就像与一位年少时期的朋友久别重逢,尤为情深意笃。如此一来,这座杂糅了粗粝与温情、琐碎与传奇的东南小城,才成了他穿越时空留载心海的精神依托。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马本德在误入孤城的最后,还是带着金乡族人从荒岛出发回到了祁连山。从来处来,又回到来处,小说叙事结构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然而,书外的我们还能回到最初一尘不染的洁净故土吗?那山、那海、那些人,难道还停在原地等待吗?马本德一行人能抵达应许之地吗?时代的变迁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让最真实纯粹的灵魂居所摇摇欲坠。或许,《误入孤城》中真正实现抵达的人士,便是那位英国护士窦维新。曾几何时,她在东方传教士先贤的激励下来到W城,终其一生都活在自己的热爱里,最后长眠于野栀子花的芬芳。窦维新行过万水千山,只为点亮心中的孤城。这何其幸运,又何其幸福!由此观之,陈河回首温州历史、讲述城市故事的同时,更是在进行现代性的深刻反思:梦醒时分,山海相接,物换星移,孤城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