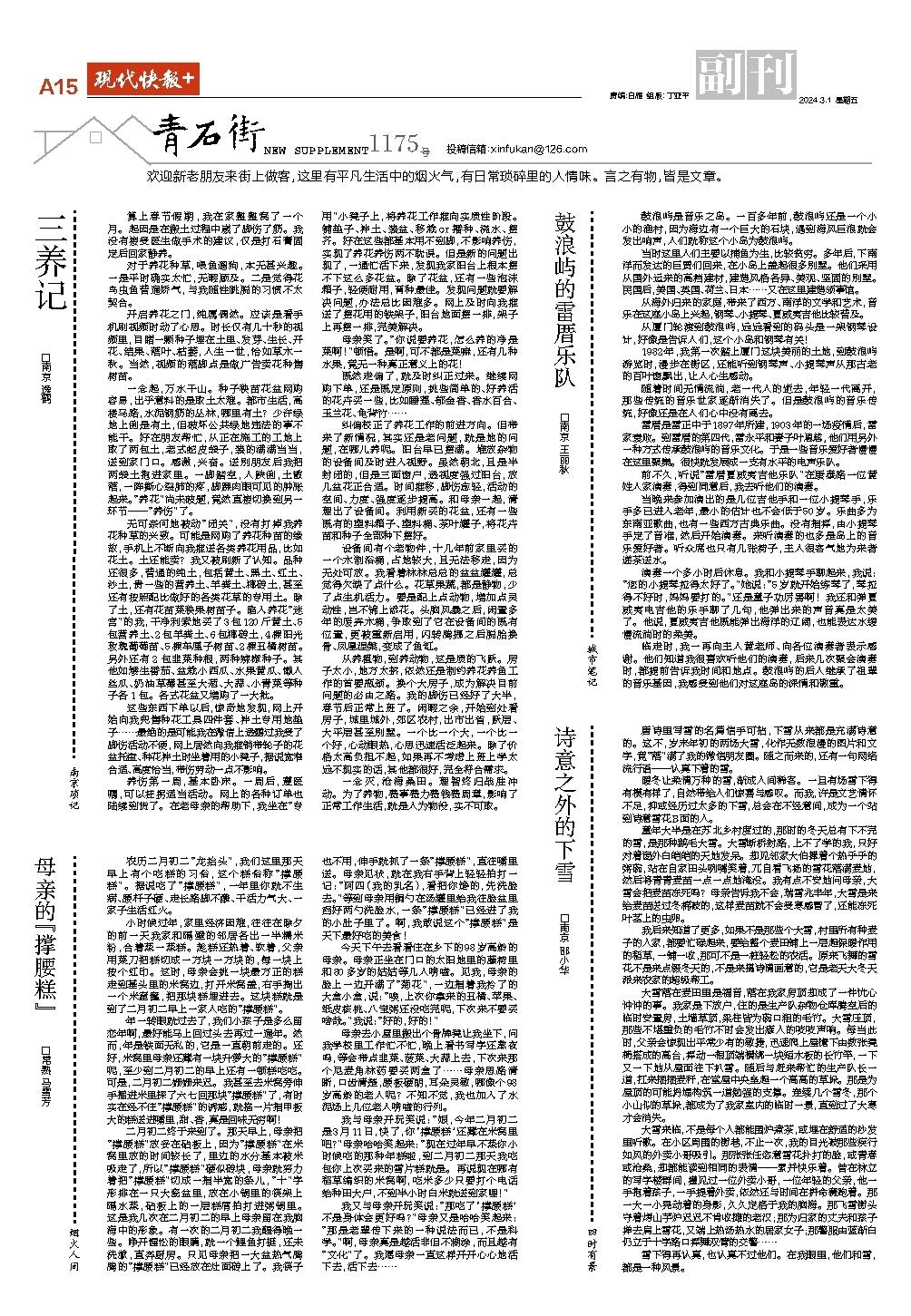□常熟 马雪芳
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我们这里那天早上有个吃糕的习俗,这个糕俗称“撑腰糕”。据说吃了“撑腰糕”,一年里你就不生病、腰杆子硬、走长路脚不酸、干活力气大、一家子生活红火。
小时候过年,家里经济困难,往往在除夕的前一天我家和隔壁的邻居各出一半糯米粉,合着蒸一蒸糕。趁糕还热着、软着,父亲用菜刀把糕切成一方块一方块的,每一块上按个红印。这时,母亲会挑一块最方正的糕走到基头里的米窝边,打开米窝盖,右手掏出一个米窟窿,把那块糕埋进去。这块糕就是到了二月初二早上一家人吃的“撑腰糕”。
年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们小孩子是多么留恋年啊,最好能马上回过头去再过一遍年。然而,年是铁面无私的,它是一直朝前走的。还好,米窝里母亲还藏有一块升箩大的“撑腰糕”呢,至少到二月初二的早上还有一顿糕吃吃。可是,二月初二姗姗来迟。我甚至去米窝旁伸手插进米里探了六七回那块“撑腰糕”了,有时实在经不住“撑腰糕”的诱惑,就掐一片指甲板大的糕送进嘴里,甜、香,真是回味无穷啊!
二月初二终于来到了。那天早上,母亲把“撑腰糕”放妥在砧板上,因为“撑腰糕”在米窝里放的时间较长了,里边的水分基本被米吸走了,所以“撑腰糕”硬似砖块,母亲就努力着把“撑腰糕”切成一指半宽的条儿,“十”字形排在一只大瓷盆里,放在小锅里的筷架上隔水蒸,砧板上的一层糕屑拍打进粥锅里。这是我几次在二月初二的早上母亲留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有一次的二月初二我醒得晚一些。睁开惺忪的眼睛,就一个鲤鱼打挺,还未洗漱,直奔厨房。只见母亲把一大盆热气腾腾的“撑腰糕”已经放在灶面砖上了。我筷子也不用,伸手就抓了一条“撑腰糕”,直往嘴里送。母亲见状,就在我右手背上轻轻拍打一记:“阿四(我的乳名),看把你馋的,先洗脸去。”等到母亲用铜勺在汤罐里给我往脸盆里舀好两勺洗脸水,一条“撑腰糕”已经进了我的小肚子里了。啊,我敢说这个“撑腰糕”是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今天下午去看看住在乡下的98岁高龄的母亲。母亲正坐在门口的太阳地里的藤椅里和80多岁的姑姑等几人唠嗑。见我,母亲的脸上一边开满了“菊花”,一边指着我拎了的大盒小盒,说:“唉,上次你拿来的丑橘、苹果、纸皮核桃、八宝粥还没吃完呢,下次来不要买啥哉。”我说:“好的,好的!”
母亲去小屋里搬出个骨牌凳让我坐下,问我学校里工作忙不忙,晚上看书写字还熬夜吗,等会带点韭菜、菠菜、大蒜上去,下次来那个尼麦角林药要买两盒了……母亲思路清晰,口齿清楚,腰板硬朗,耳朵灵敏,哪像个98岁高龄的老人呢?不知不觉,我也加入了水泥场上几位老人唠嗑的行列。
我与母亲开玩笑说:“娘,今年二月初二是3月11日,快了,你‘撑腰糕’还藏在米窝里吧?”母亲哈哈笑起来:“现在过年早不蒸你小时候吃的那种年糕啦,到二月初二那天我吃包你上次买来的雪片糕就是。再说现在哪有稻草编织的米窝啊,吃米多少只要打个电话给种田大户,不到半小时白米就送到家哩!”
我又与母亲开玩笑说:“那吃了‘撑腰糕’不是身体会更好吗?”母亲又是哈哈笑起来:“那是老辈传下来的一种说法而已,不是科学。”啊,母亲真是越活非但不糊涂,而且越有“文化”了。我愿母亲一直这样开开心心地活下去,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