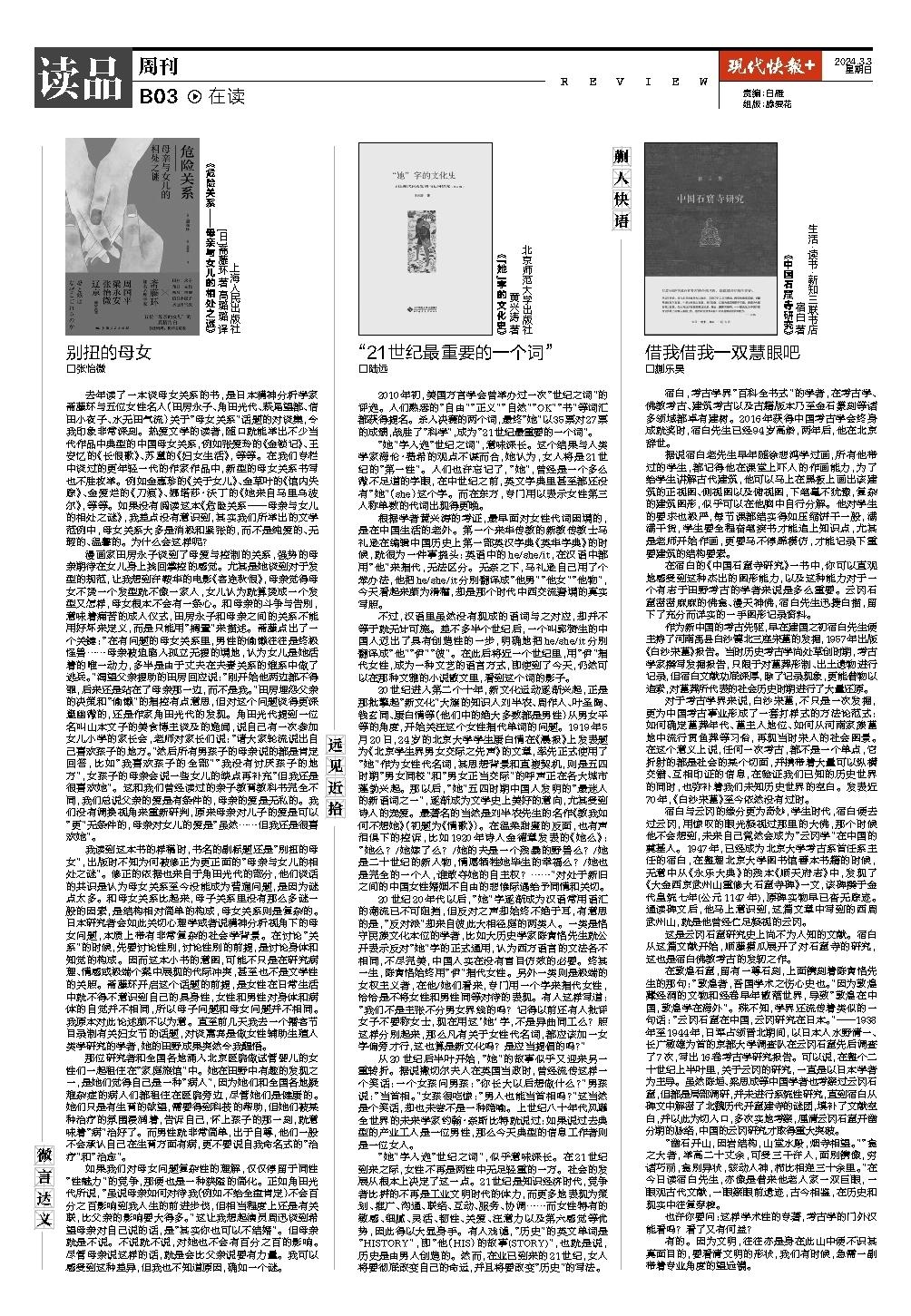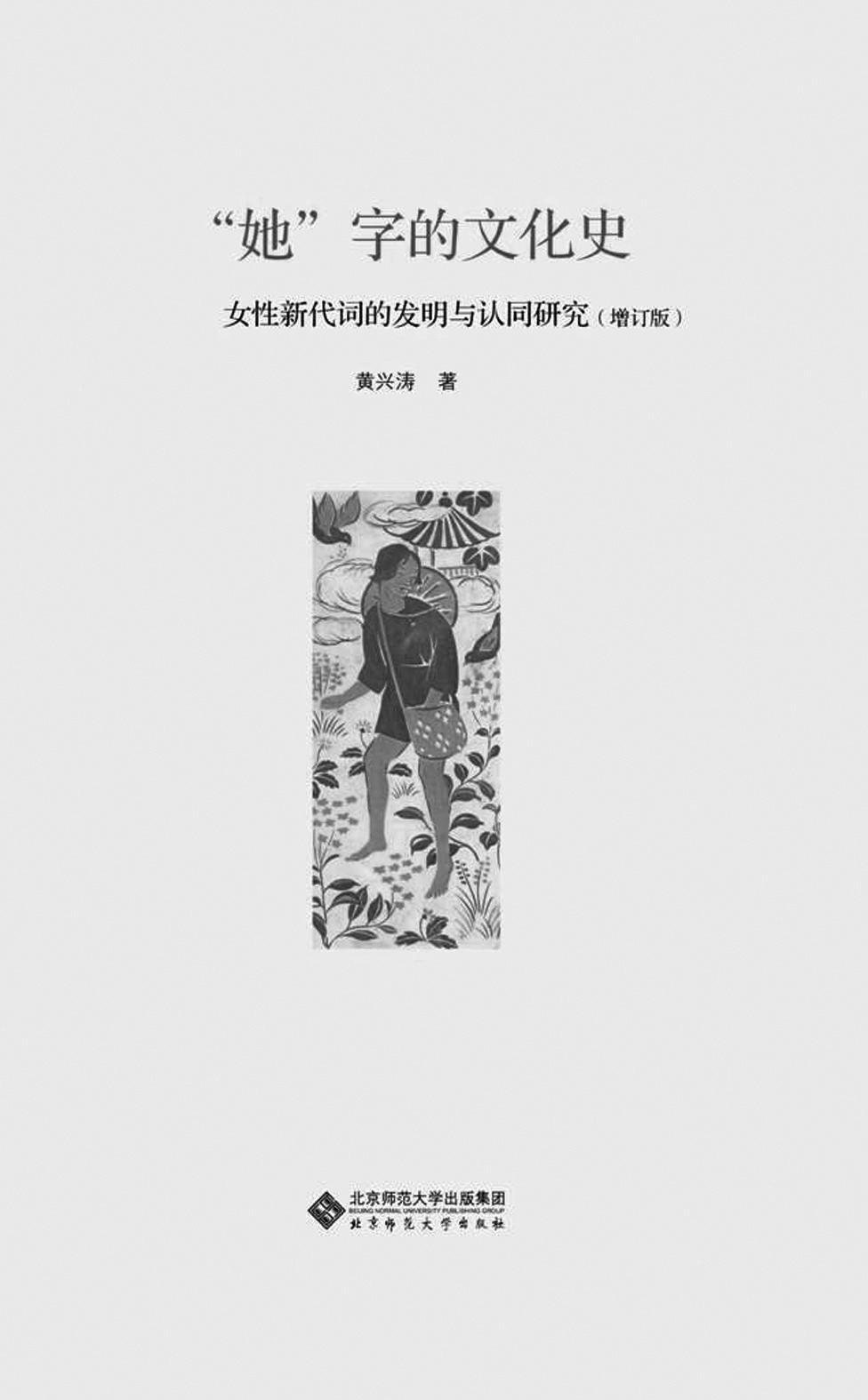□陆远
2010年初,美国方言学会曾举办过一次“世纪之词”的评选。人们熟悉的“自由”“正义”“自然”“OK”“书”等词汇都获得提名。杀入决赛的两个词,最终“她”以35票对27票的成绩,战胜了“科学”,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词”。
“她”字入选“世纪之词”,意味深长。这个结果与人类学家海伦·费希的观点不谋而合,她认为,女人将是21世纪的“第一性”。人们也许忘记了,“她”,曾经是一个多么微不足道的字眼,在中世纪之前,英文字典里甚至都还没有“她”(she)这个字。而在东方,专门用以表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代词出现得更晚。
根据学者黄兴涛的考证,最早面对女性代词困境的,是在中国生活的老外。第一个来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编辑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字典《英华字典》的时候,就很为一件事挠头:英语中的he/she/it,在汉语中都用“他”来指代,无法区分。无奈之下,马礼逊自己用了个笨办法,他把he/she/it分别翻译成“他男”“他女”“他物”,今天看起来颇为滑稽,却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流窘境的真实写照。
不过,汉语里虽然没有现成的语词与之对应,却并不等于就无计可施。差不多半个世纪后,一个叫郭赞生的中国人迈出了具有创造性的一步,明确地把he/she/it分别翻译成“他”“伊”“彼”。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里,用“伊”指代女性,成为一种文艺的语言方式,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可以在那种文雅的小说散文里,看到这个词的影子。
20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新文化运动逐渐兴起,正是那批擎起“新文化”大旗的知识人刘半农、周作人、叶圣陶、钱玄同、康白情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从男女平等的角度,开始关注这个女性指代单词的问题。1919年5月20日,24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康白情在《晨报》上发表题为《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之先声》的文章,率先正式使用了“她”作为女性代名词,其思想背景和直接契机,则是五四时期“男女同校”和“男女正当交际”的呼声正在各大城市蓬勃兴起。那以后,“她”五四时期中国人发明的“最迷人的新语词之一”,逐渐成为文学史上美好的意向,尤其受到诗人的宠爱。最著名的当然是刘半农先生的名作《教我如何不想她》(初题为《情歌》)。在温柔甜蜜的反面,也有声泪俱下的控诉,比如1920年诗人金德章发表的《她么》:“她么?/她嫁了么?/她的夫是一个残暴的野兽么?/她是二十世纪的新人物,情愿牺牲她毕生的幸福么?/她也是完全的一个人,谁敢夺她的自主权?……”对处于新旧之间的中国女性婚姻不自由的悲惨际遇给予同情和关切。
20世纪20年代以后,“她”字逐渐成为汉语常用语汇的潮流已不可阻挡,但反对之声却始终不绝于耳,有意思的是,“反对派”却来自彼此大相径庭的两类人。一类是恪守民族文化本位的学者,比如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公开表示反对“她”字的正式通用,认为西方语言的文法各不相同,不尽完美,中国人实在没有盲目仿效的必要。终其一生,陈寅恪始终用“伊”指代女性。另外一类则是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在他/她们看来,专门用一个字来指代女性,恰恰是不将女性和男性同等对待的表现。有人这样写道:“我们不是主张不分男女界线的吗?记得以前还有人批评女子不要称女士,现在用这‘她’字,不是异曲同工么?照这样分别起来,那么凡有关于女性代名词,都应该加一女字偏旁才行,这也算是新文化吗?是应当提倡的吗?”
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她”的故事似乎又迎来另一重转折。据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当政时,曾经流传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女孩问男孩:“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男孩说:“当首相。”女孩很吃惊:“男人也能当首相吗?”这当然是个笑话,却也未尝不是一种隐喻。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全世界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就说过:如果说过去典型的产业工人是一位男性,那么今天典型的信息工作者则是一位女人。
“她”字入选“世纪之词”,似乎意味深长。在21世纪到来之际,女性不再是两性中无足轻重的一方。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点。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竞争者比拼的不再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体力,而更多地表现为策划、推广、沟通、联络、互动、服务、协调……而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灵活、韧性、关爱、注意力以及第六感觉等优势,因此得以大显身手。有人戏谑,“历史”的英文单词是“HISTORY”,即“他(HIS)的故事(STORY)”,也就是说,历史是由男人创造的。然而,在业已到来的21世纪,女人将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将要改变“历史”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