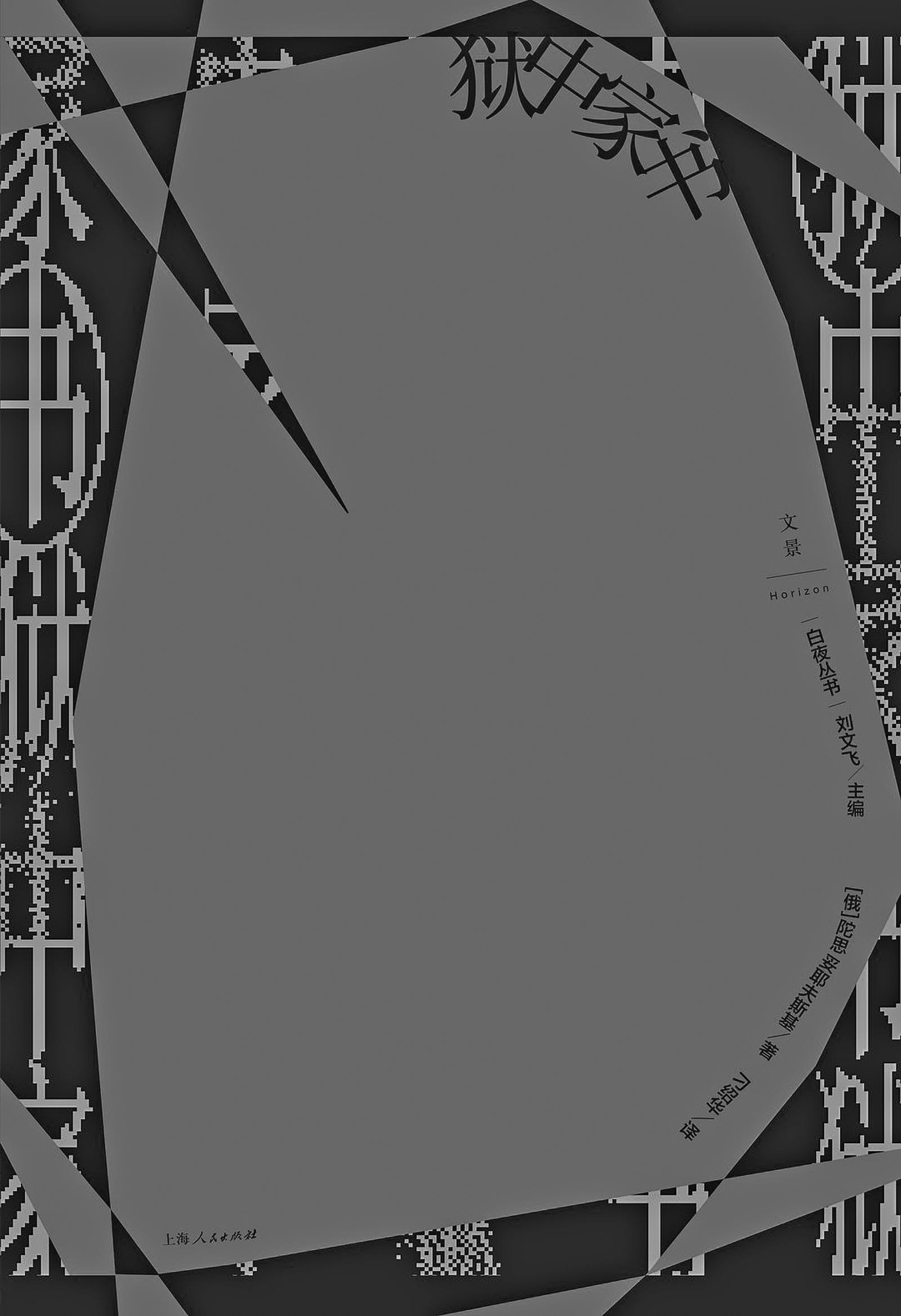□石琢玉
1849年4月,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逮捕,同年12月被判处死刑,临刑时改判为四年苦役,然后充军。他给哥哥和弟弟写的信描绘了在狱中的生活,特别是最后一封,书写了他处在死亡边缘时的心理状态,这些书信记录了他对人类心灵极限的最初探测。即使身处最为严酷的绝境,他也没有失去写作的强大意志,几乎是凭借写作支撑着全部的生存。
小说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和他的小说一样,在散文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呈现为不可替代的精神现象。它们不仅是我们理解这位文学巨匠的钥匙,也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生活和意识的许多根本特征。
《狱中家书》精选了这些书信和随笔。其中,《彼得堡纪事》《狱中家书》两篇集中提供了相对典型的陀氏文学世界观。《彼得堡纪事》中,通过再现彼得改革后处于时代剧烈变动中的俄国现状、复杂细微的人间百态,凸显出一种病态的、奇怪而阴郁,却充满生活气息的彼得堡都市形象,在这种城市力量的整合下,所有阶层的人民得以“开始”生活。陀氏零散、离散的叙述中始终维系着不变的主线——都市人民,生动而深刻地追踪着于时代激烈碰撞间,那些掩盖在表象下的人们时代心理症候。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可是研究城市却是并非无益的事”。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审视并阅读城市的历史,亦是从文化建筑中读取、了解整个时代,作者敏锐地把握住了疾驰生活背景下当代思想的困顿与迷惘。人们被讲述、被描写,同时也在世人面前分析自己,常常是怀着痛苦的心情。陀氏饱含着对人民的同情,注视人们复杂变幻的心理世界,以巨大热情谈及美德、创造、当代思想,强调生命本身不受苦难摧毁的美丽内核——即使是在病态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生活平庸贫乏,萎靡不振,因此人们力图用幻想及其一切辅助手段来填补他的空虚”)。透过富含意象的塑造,“幻想家”这一极具特点的形象和概念在本文被提及,不久后也成为他创作全新小说人物的灵感原型。我们能够看出,正是这样对万事万物充满探究心、不断叩问内心灵魂并将其付诸笔墨的坚持,才能使得一部部伟大作品于灵感迸发的一瞬间被捕获、凝固于纸面,最终得以成型。
《狱中家书》更直观地展现了一个生活困顿、深受苦刑折磨,却仍用文字传达不受禁锢的饱满情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较于其他随笔中透析人间的求索者、政论文中用语夸张怪诞却直击重大问题的思想家,他在这篇里,更像是一位挣扎于穷困、向往着美好生活、与千千万万受压迫的人民有着同样美好不屈灵魂的普通人。遭到牢狱之灾,不知审判和死亡何时到来,在如此极端恶劣的处境中,他渴望并重视着亲情,将书籍与思想融入血肉。尽管死亡与刑罚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他仍旧顽强地与病痛斗争,化生命为文学信念,在绝境中找寻他眼中的“救赎”。
1849年9月14日的信中,他写道,“也就是说,我只靠着头脑而生,别无其他”——这一天是他与死神擦身而过的日子,他以为自己即将被处死,被拉去行刑前的最后一分钟里,他饱含对亲人的爱,想念着他们。经历临刑前获赦免的劫后余生,他又写道,“生活就在我们自身,而不在外界……如今,我的生活变了,我要以另一种形式再生”。
这些家书也可窥见陀氏文学观念的一斑,他详尽描述了自己苦役期间严酷的生活条件与病魔的侵扰,这一切身感受也使得他将对人民的热爱与理解融进写作中,他脑海中无数的形象都是血肉鲜活的人民苦难的缩影。陀氏眼中的文学写作也是摧毁与再造生命的轮回历程,在不断写作中,这些灵魂将获得生命的载体,变得愈加完整,就如文中说的,“有多少个形象受过重伤之后活了下来,经过我重新创造之后,又要死去,在我的头脑中消失,或者变成毒汁融入血液里!可是假如不准写作,我就宁肯死去……只要是手里能握着笔,那也是好的”。《百岁老妇》一篇就是这样一个写作背后的故事,一段见闻、一些不连贯的印象,却能霎时间勾起作家的灵感,转化成为文学世界里的一个小小场景,对生死的体悟、对人民深刻的爱使得故事丰满而连贯。
本书的其他几篇,或回忆、或特写、或对话,打破了人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章风格固有的印象,其内容分别以乔治·桑、女性运动、民族历史、人口与土地问题、普希金的文学地位等话题,较为全面地展现了陀氏的文学、政治、人类观念。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陀氏也广博地探讨了女性力量、城市体制扩张与土地不合理分配所埋下的隐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在矿泉区什么东西最有用 矿泉水还是风度?》等多篇文章采用对话体,借“奇谈怪论者”的对话这一怪诞夸张的形式,揭露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重申应对人类抱有的热爱。
尽管陀氏因其所处时代的桎梏,其思想仍带有一些理性化、宗教化的色彩,但其始终有着对精神世界执着的探求与思辨。他坚信俄国人的使命是全欧洲性和全世界性的,并在文学界发出呼吁,以朴素的目标要求实现最迫切的大联合以及全人类的统一。通过对普希金文学精神的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蕴含着反映全世界的能力——天才的全世界性和全人类性,超越时代窥见了这种“世界性”实现的可能。
对文学、对世界包含痛苦与爱的思索,是从陀氏充满诗性与情感的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回观今日,陀氏之书仍然以其复杂而真切的思想,给予我们这个同样充满时代症候性的社会以超越表象、直击灵魂的启示。在如今这个媒介信息空前爆炸的电子时代,我们处于一个似乎冷漠的离散化、原子化社会中,重读百年前陀氏的文学,汲取其带给我们的超越时空的思考,找回我们弥散在电子空间中的主体性,将人与人之间脆弱、断裂的关系,通过炽热的文字重新维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