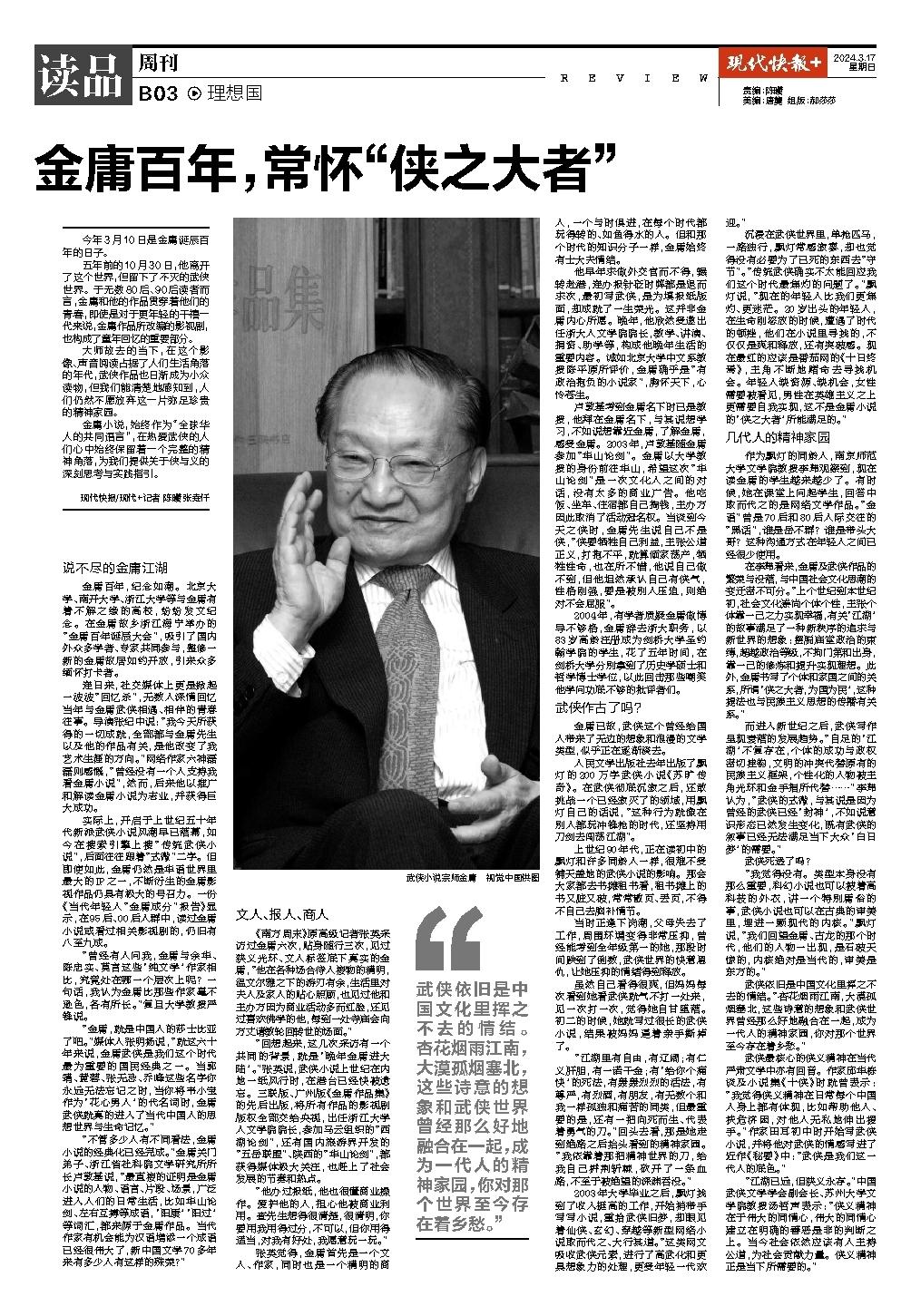今年3月10日是金庸诞辰百年的日子。
五年前的10月30日,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留下了不灭的武侠世界。于无数80后、90后读者而言,金庸和他的作品贯穿着他们的青春,即使是对于更年轻的千禧一代来说,金庸作品所改编的影视剧,也构成了童年回忆的重要部分。
大师故去的当下,在这个影像、声音阅读占据了人们生活角落的年代,武侠作品也日渐成为小众读物,但我们能清楚地感知到,人们仍然不愿放弃这一片弥足珍贵的精神家园。
金庸小说,始终作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在热爱武侠的人们心中始终保留着一个完整的精神角落,为我们提供关于侠与义的深刻思考与实践指引。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张垚仟
说不尽的金庸江湖
金庸百年,纪念如潮。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等与金庸有着不解之缘的高校,纷纷发文纪念。在金庸故乡浙江海宁举办的“金庸百年诞辰大会”,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专家共同参与,整修一新的金庸故居如约开放,引来众多缅怀打卡者。
连日来,社交媒体上更是掀起一波波“回忆杀”,无数人深情回忆当年与金庸武侠相遇、相伴的青春往事。导演张纪中说:“我今天所获得的一切成就,全部都与金庸先生以及他的作品有关,是他改变了我艺术生涯的方向。”网络作家六神磊磊则感慨,“曾经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看金庸小说”,然而,后来他以推广和解读金庸小说为志业,并获得巨大成功。
实际上,开启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新派武侠小说风潮早已落幕,如今在搜索引擎上搜“传统武侠小说”,后面往往跟着“式微”二字。但即使如此,金庸仍然是华语世界里最大的IP之一,不断衍生的金庸影视作品仍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一份《当代年轻人“金庸成分”报告》显示,在95后、00后人群中,读过金庸小说或看过相关影视剧的,仍旧有八至九成。
“曾经有人问我,金庸与余华、陈忠实、莫言这些‘纯文学’作家相比,究竟处在哪一个层次上呢?一句话,我认为金庸比那些作家毫不逊色,各有所长。”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说。
“金庸,就是中国人的莎士比亚了吧。”媒体人张明扬说,“就这六十年来说,金庸武侠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国民经典之一。当郭靖、黄蓉、张无忌、乔峰这些名字你永远无法忘记之时,当你将韦小宝作为‘花心男人’的代名词时,金庸武侠就真的进入了当代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与生命记忆。”
“不管多少人有不同看法,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已经完成。”金庸关门弟子、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卢敦基说,“最直接的证明是金庸小说的人物、语言、片段、场景,广泛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华山论剑、左右互搏等成语,‘阳康’‘阳过’等词汇,都来源于金庸作品。当代作家有机会能为汉语增添一个成语已经很伟大了,新中国文学70多年来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殊荣?”
文人、报人、商人
《南方周末》原高级记者张英采访过金庸六次,贴身随行三次,见过狭义光环、文人标签底下真实的金庸,“他在各种场合待人接物的精明,温文尔雅之下的游刃有余,生活里对夫人及家人的贴心照顾,也见过他和主办方因为商业活动多而红脸,还见过喜欢佛学的他,每到一处寺庙会向方丈请教轮回转世的场面。”
“回想起来,这几次采访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晚年金庸进大陆’。”张英说,武侠小说上世纪在内地一纸风行时,在港台已经快被遗忘。三联版、广州版《金庸作品集》的先后出版,将所有作品的影视剧版权全部交给央视,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参加马云组织的“西湖论剑”,还有国内旅游界开发的“五岳联盟”、陕西的“华山论剑”,都获得媒体极大关注,也赶上了社会发展的节奏和热点。
“他办过报纸,他也很懂商业操作。爱护他的人,担心他被商业利用。查先生想得很清楚,很清明,你要用我用得过分,不可以,但你用得适当,对我有好处,我愿意玩一玩。”
张英觉得,金庸首先是一个文人、作家,同时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一个与时俱进,在每个时代都玩得转的、如鱼得水的人。但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始终有士大夫情结。
他早年求做外交官而不得,辗转赴港,连办报针砭时弊都是退而求次,最初写武侠,是为填报纸版面,却成就了一生荣光。这并非金庸内心所愿。晚年,他欣然受邀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教学、讲演、捐资、助学等,构成他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所评价,金庸确乎是“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胸怀天下,心怜苍生。
卢敦基考到金庸名下时已是教授,他拜在金庸名下,与其说想学习,不如说想靠近金庸,了解金庸,感受金庸。2003年,卢敦基随金庸参加“华山论剑”。金庸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前往华山,希望这次“华山论剑”是一次文化人之间的对话,没有太多的商业广告。他吃饭、坐车、住宿都自己掏钱,主办方因此取消了活动冠名权。当谈到今天之侠时,金庸先生说自己不是侠,“侠要牺牲自己利益,主张公道正义,打抱不平,就算倾家荡产,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他说自己做不到,但他坦然承认自己有侠气,性格刚强,要是被别人压迫,则绝对不会屈服”。
2004年,有学者质疑金庸做博导不够格,金庸辞去浙大职务,以83岁高龄注册成为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学生,花了五年时间,在剑桥大学分别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以此回击那些嘲笑他学问功底不够的批评者们。
武侠作古了吗?
金庸已故,武侠这个曾经给国人带来了无边的想象和浪漫的文学类型,似乎正在逐渐淡去。
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年出版了飘灯的200万字武侠小说《苏旷传奇》。在武侠彻底沉寂之后,还敢挑战一个已经寂灭了的领域,用飘灯自己的话说,“这种行为就像在别人都玩冲锋枪的时代,还坚持用刀剑去闯荡江湖”。
上世纪90年代,正在读初中的飘灯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很难不受铺天盖地的武侠小说的影响。那会大家都去书摊租书看,租书摊上的书又脏又破,常常散页、丢页,不得不自己去脑补情节。
当时正逢下岗潮,父母失去了工作,周围环境变得非常压抑,曾经能考到全年级第一的她,那段时间跌到了倒数,武侠世界的快意恩仇,让她压抑的情绪得到释放。
虽然自己看得很爽,但妈妈每次看到她看武侠就气不打一处来,见一次打一次,觉得她自甘堕落。初二的时候,她就写过很长的武侠小说,结果被妈妈逼着亲手撕掉了。
“江湖里有自由,有辽阔;有仁义肝胆,有一诺千金;有‘给你个痛快’的死法,有轰轰烈烈的活法,有尊严,有烈酒,有朋友,有无数个和我一样孤独和痛苦的同类,但最重要的是,还有一把向死而生、代表着勇气的刀。”回头去看,那是她走到绝路之后抬头看到的精神家园。“我依靠着那把精神世界的刀,给我自己拼荆斩棘,砍开了一条血路,不至于被绝望的深渊吞没。”
2003年大学毕业之后,飘灯找到了收入挺高的工作,开始捎带手写写小说,重拾武侠旧梦,却眼见着仙侠、玄幻、穿越等新型网络小说取而代之、大行其道。“这类网文吸收武侠元素,进行了高武化和更具想象力的处理,更受年轻一代欢迎。”
沉浸在武侠世界里,单枪匹马,一路独行,飘灯常感寂寥,却也觉得没有必要为了已死的东西去“守节”。“传统武侠确实不太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最焦灼的问题了。”飘灯说,“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更焦灼、更迷茫。20岁出头的年轻人,在生命刚怒放的时候,遭遇了时代的顿挫,他们在小说里寻找的,不仅仅是爽和释放,还有突破感。现在最红的应该是番茄网的《十日终焉》,主角不断地赌命去寻找机会。年轻人缺资源、缺机会,女性需要被看见,男性在英雄主义之上更需要自我实现,这不是金庸小说的‘侠之大者’所能满足的。”
几代人的精神家园
作为飘灯的同龄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玮观察到,现在读金庸的学生越来越少了。有时候,她在课堂上问起学生,回答中取而代之的是网络文学作品。“金语”曾是70后和80后人际交往的“黑话”,谁是岳不群?谁是带头大哥?这种沟通方式在年轻人之间已经很少使用。
在李玮看来,金庸及武侠作品的繁荣与没落,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密不可分。“上个世纪到本世纪初,社会文化崇尚个体个性,主张个体靠一己之力实现幸福,有关‘江湖’的故事满足了一种新秩序的追求与新世界的想象:摆脱庙堂政治的束缚,超越政治等级,不拘门第和出身,靠一己的修炼和提升实现理想。此外,金庸书写了个体和家国之间的关系,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种提法也与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有关系。”
而进入新世纪之后,武侠写作呈现衰落的发展趋势。“自足的‘江湖’不复存在,个体的成功与政权密切挂钩,文明的冲突代替原有的民族主义框架,个性化的人物被主角光环和金手指所代替……”李玮认为,“武侠的式微,与其说是因为曾经的武侠已经‘封神’,不如说意识形态已然发生变化,既有武侠的叙事已经无法满足当下大众‘白日梦’的需要。”
武侠死透了吗?
“我觉得没有。类型本身没有那么重要,科幻小说也可以披着高科技的外衣,讲一个特别庸俗的事,武侠小说也可以在古典的审美里,埋进一颗现代的内核。”飘灯说,“我们回望金庸、古龙的那个时代,他们的人物一出现,是石破天惊的,内核绝对是当代的,审美是东方的。”
武侠依旧是中国文化里挥之不去的情结。“杏花烟雨江南,大漠孤烟塞北,这些诗意的想象和武侠世界曾经那么好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家园,你对那个世界至今存在着乡愁。”
武侠最核心的侠义精神在当代严肃文学中亦有回音。作家邱华栋谈及小说集《十侠》时就曾表示:“我觉得侠义精神在日常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体现,比如帮助他人、扶危济困,对他人无私地伸出援手。”作家田耳初中时开始写武侠小说,并将他对武侠的情感写进了近作《秘要》中:“武侠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底色。”
“江湖已远,但狭义永存。”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汤哲声表示:“侠义精神在于伟大的同情心,伟大的同情心建立在明确的善恶是非的判断之上。当今社会依然应该有人主持公道,为社会贡献力量。侠义精神正是当下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