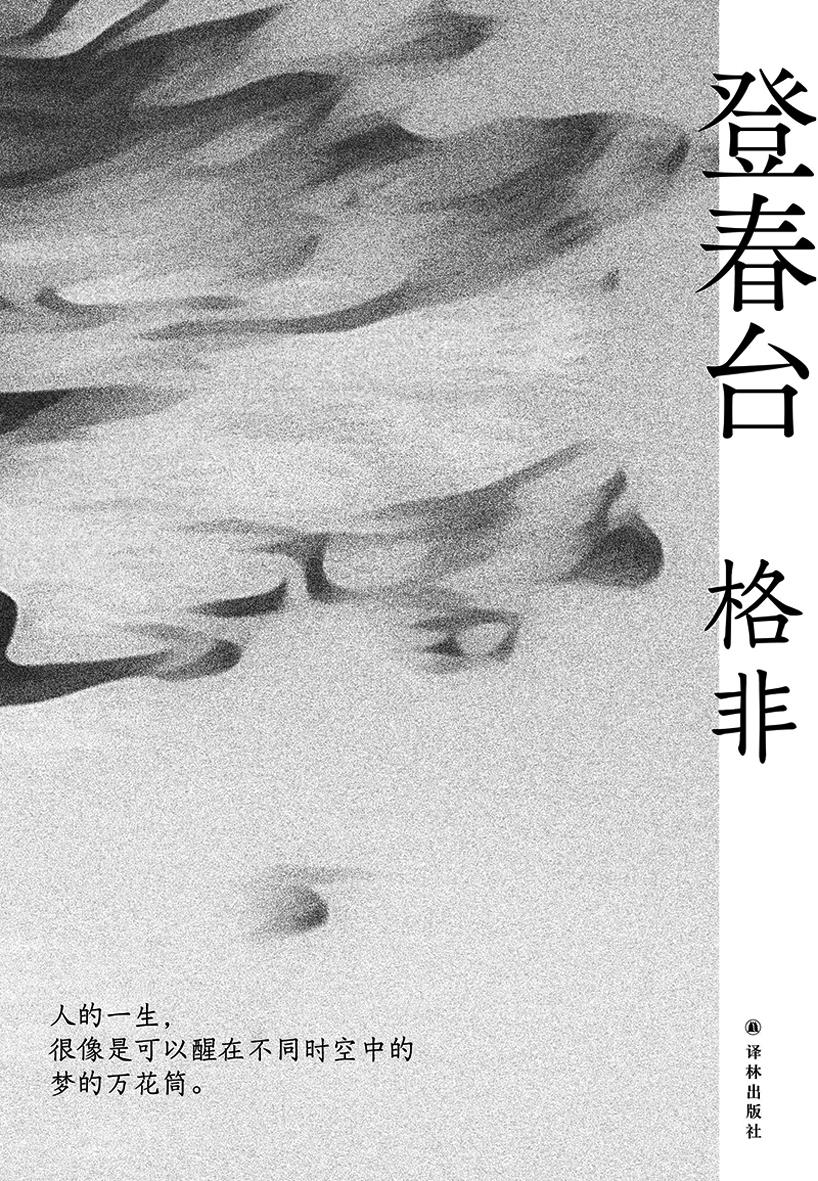3月20日,时值春分,茅盾文学奖得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的最新长篇小说《登春台》正式面世。
故事以1980年代至今的四十余年为背景,聚焦四个人物的命运流转。他们之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来自江南的笤溪村、北京的小羊坊村、甘肃的地坑院洞穴、里下河平原的小村庄,并在北京春台路67号有了命运的交集。书中延续了格非创作脉络中对现代文明的关切,以小说的形式,进行广泛精微的中国社会考察,对人类和自我等命题做出哲思性探讨。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希望把四个不同的故事写成同一个故事
小说故事是从1980年代开始讲起。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分别从江南的笤溪村、北京的小羊坊村、甘肃云峰镇、天津城来到北京春台路67号,他们供职于同一家物联网公司,又在若即若离中,展演着自己的故事。处于江南乡村家庭漩涡中的沈辛夷,在逃离与顺应中进退维谷;深爱妻子的陈克明,却不可避免地陷入出轨的危险之中;阴郁的野人窦宝庆,始终握着自己的秘密,在人群中独行;业已退休、烹茶养花的企业家周振遐十分确认自己正处于幸福之中,对死亡的恐惧却依旧与他如影随形……
小说以四个人物的姓名为题分为四章,讲述各自的故事,并在头尾接续序章与附记两个部分。四个人物的故事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结。随着四人的讲述,故事渐渐拼凑成全貌,带读者离开地面,回望时代。
格非在接受访谈时表示,作品最困难的部分首先在于结构,而不是故事情节。他不愿意把一个故事从头到尾地讲一遍,当然也不愿意将它写成“系列小说”。他希望把四个不同的故事写成同一个故事,让各部分彼此镶嵌在一起,同时不去破坏每个故事自身的明晰性。
《登春台》问市后,受到文学界、评论界和读者广泛好评,目前已迅速加印,并成功入选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荣登2023《收获》文学榜长篇小说榜、《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等多种重要媒体榜单。作品还被《当代》《作家》等权威期刊转载。
在持续的困境中辨认自我与世界关系
《登春台》的书名取自老子《道德经》第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喻指一种盛世气象,又暗合了小说开篇俯瞰众生、凝神沉思的视角。全书延续了格非创作脉络中对现代文明之下的个体的关切。作品中的人物都身处现代文明进程中,面对着时代的巨大变幻。人流如潮水般漫上街面,列车极速狂飙突进,巨量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填满生活的缝隙。
格非希望在小说结构背后传达出有关当代人的欲望、情感、彼此关联、时间危机、生存困境等方面的思考。
他说,从198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正在以比较特殊的方式迈向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与城市的因素叠加起来,与整个世界的进程缠绕在一起,构成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人心和欲望的变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过去,就像在莫言小说中得到充分表现的那样,欲望意味着摆脱饥饿和匮乏,而在今天,欲望更多地被形形色色的流行文化所界定。举例来说,在乡村,几代人可以同穿一件大衣,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旧”的。旧物中包含着特殊的记忆和情感。但今天,我们的衣物远未变旧,新的款式就已经要求取而代之了。当然,我们今天的欲望也已经被符号化了。驱动欲望的不仅仅是匮乏,更多的是过剩性的文化想象。
评论家陈培浩称:“《登春台》最令我触动的是不放弃现实、也不放弃对现实的反思,在持续的困境中辨认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想姿态。”
别样的哲学意蕴和文体的创新可能
《登春台》以小说的形式,进行广泛精微的中国社会考察。在故事的叙写中,格非凝视现代人的情感变迁,探索了亲子关系、两性关系、今我与故我的关系等多种情感命题,以一位作家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浩渺哲思,为现代文明进程留下了可资参考的精神文本。而小说在故事层之余,还存在另一层与以往文本不同的哲学蕴藉。如评论家毛尖所说:“他更自由,更哲学。”这种自由与哲学,散布在小说的各个角落。
小说的核心地点春台路67号是一个带有深层寓意的物联网公司,而小说的结构是一个层层嵌套、可以形成闭环的圆;故事里有一个专门讨论哲学的读书会明夷社,对哲学兴趣浓厚的创业者蒋承泽,充满行动力的植物,更不用说行文中多处出现的关于存在与时间的省思。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民安认为:“《登春台》有尼采意义上的永恒轮回式的时间结构,也有拉图尔意义上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空间结构。连植物都是行动者!如今,物联网不仅是一个公司,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法则。”这一层哲学意蕴,也正是格非不断对现实进行反思,在持续的困境中辨认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想姿态的体现。
但这一层哲学蕴藉却丝毫没有影响小说的流畅与可读性,许多读者反馈,这是一个可以“一口气读完的”精彩故事。这也是格非在反复修改中希望呈现的效果:使人物故事与哲学意蕴圆融为一体。如同书评人俞耕耘所说:“《登春台》承载格非对人生况味,生活境遇的深沉涵咏。抒情风致,田野乡间,废窑花院,古寺深宅,大有梭罗、爱默生自然文学的质感肌理。其用散文笔法写故事,并不依赖戏剧性事件,而是有‘过生活’的纪实节奏。这种匀速的原样主义,给小说带来切己体感。”这样一种尝试,为小说这个体裁带来了一种新的文体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