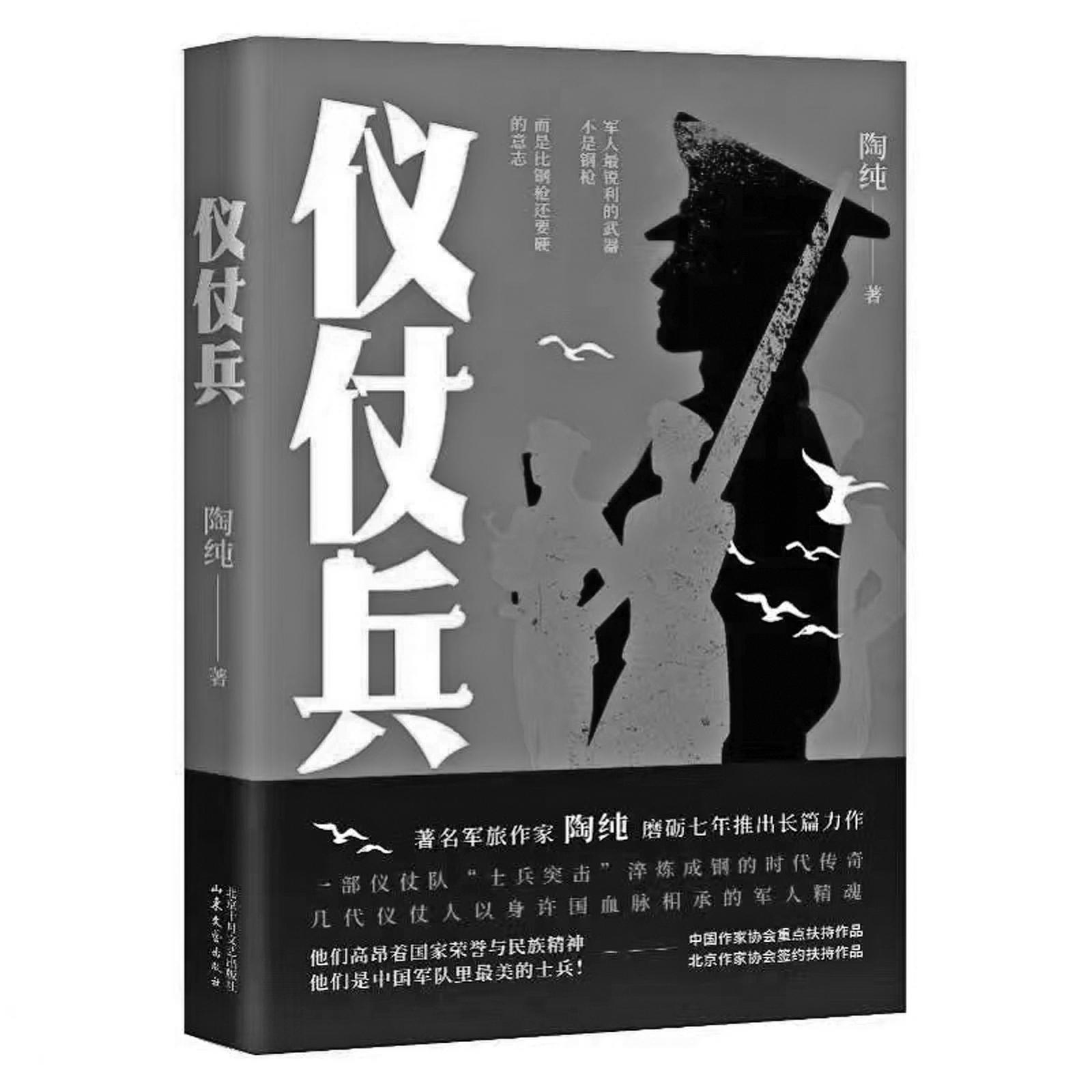□左怡然
军人用军刀雕琢军魂,作家则用笔雕琢人物由内而外的形象气质,而陶纯似乎给自己布置了更为艰巨的任务——雕刻一座属于仪仗兵的群像浮雕,编制一部振奋人心的仪仗兵群体成长史。正如书封上的那幅剪影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跨越代际、无谓性别、个性迥异的仪仗人于血汗交织中一脉相承的军人精魂。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仪仗队的组建可以追溯到1946年,为迎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上将,展现解放区人民军队的力量,党中央从解放军驻南泥湾部队中挑选500名战士,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支仪仗队。自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就成为了中国军队的门面乃至中华民族的名片。
“如果说解放军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大书,那么,三军仪仗队就是这部大书的精美扉页,在这张扉页上镌刻着共和国的风采和中华民族的尊严”,这是作者陶纯对三军仪仗队存在之意义的注解,也昭示了他选择这一独特的群体作为书写对象的原因。军队能够最直接地体现一个国家的实力,仪仗队则让内部的人民与外部的敌友最直观地感受到这股力量,对内振我民心,对外扬我国威。
与中国军队的其他兵种相比,三军仪仗队的历史不算悠久,作者在叙述视角上采用全知视角以便于从不同人物的心路历程中寻找刻画这一群体面貌的突破口,进而展开对这一群体发展史的书写。在具体时间段的选择上,作者以主人公李振杰从对仪仗兵产生敬仰之情,到应征入伍,再到逐渐被磨炼为一名成熟的仪仗兵的成长历程为主线,串联起香港回归、一九九九年世纪大阅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阅兵、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应邀参加莫斯科红场阅兵等重大事件,展现了迄今中国仪仗队最光彩的一段历史。同时作者借助叙述时间上的顺叙与回溯交错追忆了仪仗兵先辈们的历史,塑造了以吴登义为代表的老一辈仪仗人形象;而对卢天祥、吴青江、成敬捷等仪仗人偶像“前史”的书写,则与李振杰的成长形成了补充与映衬。
李振杰的成熟离不开师友们的帮助。同为师长和引路人,班长耿长明给了振杰最初的自信和勇气,并成为振杰数次想要退缩时支撑其继续走下去的力量,而振杰的成功似乎是以另一种方式弥补了班长军旅生活的遗憾;同样温暖着振杰军旅历程的还有不断为其争取机会的吴青江,爱才识才、循循善诱是这位教导员留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手持指挥刀的卢天祥则扮演着另一种角色:威严而峻厉,用最粗糙的毛边磨去振杰性格中的顽劣与怯弱,又以最坚挺的身姿成为振杰永远的标杆。李振杰、耿长明、吴青江、卢天祥……这些个性鲜明的仪仗人各自书写了仪仗兵不同阶段的历史,又汇聚到一起共谋仪仗军之大业,他们的性格和经历相互映照,映出了同中之异,更照出了异中之同——这是军人于血汗中淬炼出的军魂,亦是作家无数次打磨素材、情节和语言后提炼出的小说精神内核。
文学中的历史由人物书写而成,人物则在日常与细节中逐渐呈现出清晰而丰富的面貌。如何拉近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如何使文学作品在传递主流价值的同时不被架空为宣传标语和口号,作者做到了从仪仗兵日常的生活与训练出发,挖掘触动其心理震颤、引发其思想转变的人、事、物之细节,展示了不同于常人刻板印象的军营生活的另一面,以及仪仗兵所经受的不同于其他兵种的锻造与考验。军人是象征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的符号,但军人作为人又不应只是符号,作者将他们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在情感书写的过程中关注亲情、爱情、师生情、战友情等多种类型的情感对仪仗兵个体成长与群体发展的影响。在小说中,作者为我们展示了处理个体“小情”与军人“大义”之纠葛的多种方式,揭示了军人为国增光的背后离不开诸多家庭的奉献与牺牲。由此看来,军人的“小情”实乃人民的“大义”,“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本质小说的情感书写中得到了别样的升华。
“他们的舞台,那么小,就一个操场;他们的舞台,又是那么大,从天安门广场这个祖国的心脏,辐射到世界各地”。打造青春偶像不是娱乐行业和造星公司的专利,用文字打造偶像以传播正能量,文学和作家同样肩负使命。陶纯在《仪仗兵》中塑造的这一特殊的军人群体,枪里不用装子弹,刀刃不必染鲜血,却能释放出同样强大的力量。《仪仗兵》与仪仗兵们,必然会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之路上的一道耀眼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