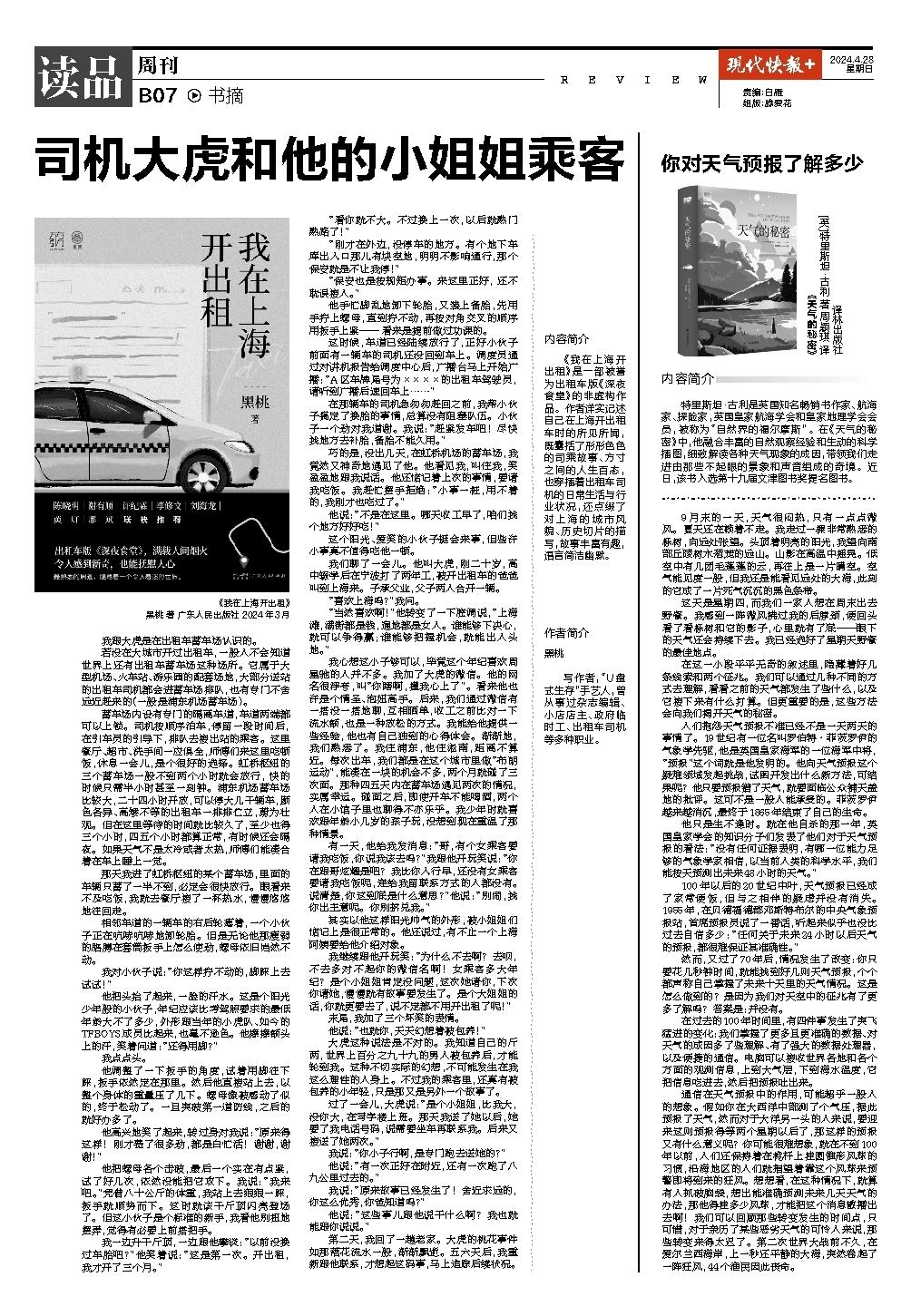特里斯坦·古利是英国知名畅销书作家、航海家、探险家,英国皇家航海学会和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被称为“自然界的福尔摩斯”。在《天气的秘密》中,他融合丰富的自然观察经验和生动的科学插图,细致解读各种天气现象的成因,带领我们走进由那些不起眼的景象和声音组成的奇境。近日,该书入选第十九届文津图书奖提名图书。
9月末的一天,天气很闷热,只有一点点微风。夏天还在赖着不走。我走过一棵非常熟悉的栎树,向远处张望。头顶着明亮的阳光,我望向南部丘陵树木葱茏的远山。山影在高温中摇晃。低空中有几团毛蓬蓬的云,再往上是一片晴空。空气能见度一般,但我还是能看见远处的大海,此刻的它成了一片死气沉沉的黑色条带。
这天是星期四,而我们一家人想在周末出去野餐。我感到一阵微风拂过我的后脖颈,便回头看了看栎树和它的影子,心里就有了底——眼下的天气还会持续下去。我已经选好了星期天野餐的最佳地点。
在这一小段平平无奇的叙述里,隐藏着好几条线索和两个征兆。我们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去理解,看看之前的天气都发生了些什么,以及它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方法会向我们揭开天气的秘密。
人们抱怨天气预报不准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19世纪有一位名叫罗伯特 · 菲茨罗伊的气象学先驱,他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位海军中将,“预报”这个词就是他发明的。他向天气预报这个疑难领域发起挑战,试图开发出什么新方法,可结果呢?他只要预报错了天气,就要面临公众铺天盖地的批评。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菲茨罗伊越来越消沉,最终于1865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只是生不逢时。就在他自杀的那一年,英国皇家学会的知识分子们发表了他们对于天气预报的看法:“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哪一位能力足够的气象学家相信,以当前人类的科学水平,我们能按天预测出未来48小时的天气。”
100年以后的20世纪中叶,天气预报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但与之相伴的疑虑并没有消失。1955年,在贝德福德郡邓斯特布尔的中央气象预报站,首席预报员说了一番话,听起来似乎也没比过去自信多少:“任何关于未来24小时以后天气的预报,都很难保证其准确性。”
然而,又过了70年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你只要花几秒钟时间,就能找到好几则天气预报,个个都声称自己掌握了未来十天里的天气情况。这是怎么做到的?是因为我们对天空中的征兆有了更多了解吗?答案是:并没有。
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有四件事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我们掌握了更多且更准确的数据、对天气的成因多了些理解、有了强大的数据处理器,以及便捷的通信。电脑可以接收世界各地和各个方面的观测信息,上到大气层,下到海水温度,它把信息吃进去,然后把预报吐出来。
通信在天气预报中的作用,可能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假如你在大西洋中部测了个气压,据此预报了天气,然而对于大洋另一头的人来说,要迎来这则预报得等两个星期以后了,那这样的预报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可能很难想象,就在不到100年以前,人们还保持着在桅杆上挂圆锥形风球的习惯,沿海地区的人们就指望着靠这个风球来预警即将到来的狂风。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有人抓破脑袋,想出能准确预测未来几天天气的办法,那他得挂多少风球,才能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啊!我们可以回顾那些转变发生的时间点,只可惜,对于亲历了某些恶劣天气的可怜人来说,那些转变来得太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在爱尔兰西海岸,上一秒还平静的大海,突然卷起了一阵狂风,44个渔民因此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