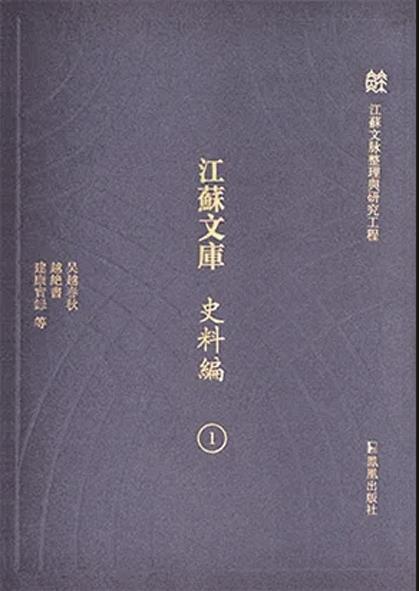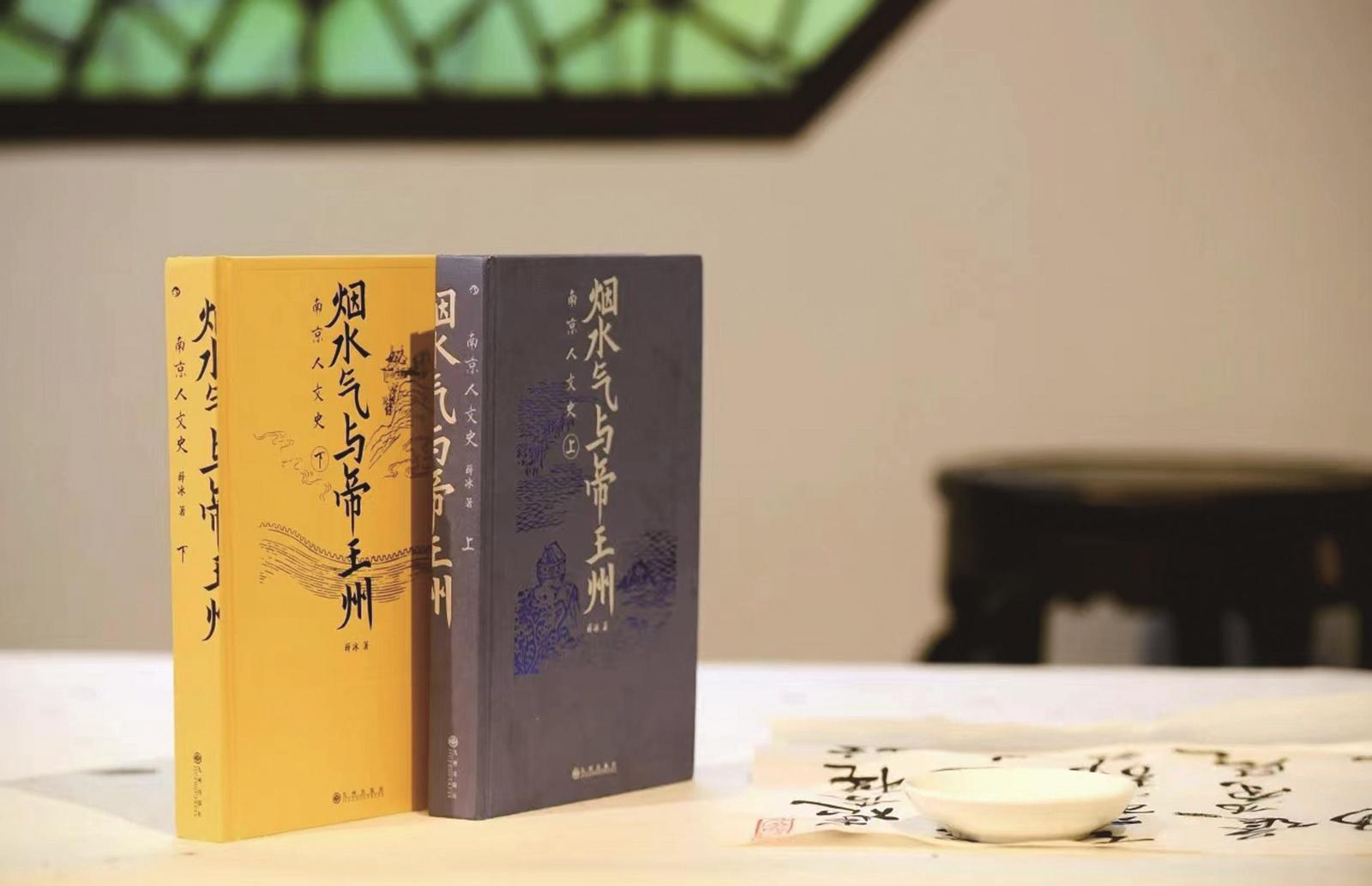我们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开篇就是“永和九年”,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年份背后,有一位贤明女性的身影。这就是在南京主持东晋朝政前后长达四十年、扶持六位皇帝、支撑陈郡谢氏崛起,却鲜为人知的女人——皇太后褚蒜子。
在著名学者薛冰新近出版的《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中,特意为褚蒜子书写了一个篇章,文脉君看后忍不住感叹:“这个女人不简单!”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凡 整理自《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
第一回
先来看看褚蒜子的出身。
褚蒜子可谓含着金汤匙出生。父亲是太傅褚裒(póu),母亲谢真石是陈郡谢氏后人,外祖父谢鲲先后追随王衍、王敦,也是一时名士,曾任豫章太守。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褚蒜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她嫁给了东晋第四位皇帝晋康帝司马岳,二十岁时被立为皇后。但好景不长,晋康帝仅在位两年就病故。
褚蒜子的人生由此转折,也由此“开挂”。
那时,褚蒜子的儿子司马聃才2岁。在群臣的恳请下,永和元年(345),二十一岁的皇太后褚蒜子临朝称制,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垂帘听政”——皇太后褚蒜子设白纱帷帐于太极殿,抱着两岁的小皇帝(晋穆帝)登上朝堂。
初登朝堂,褚蒜子的父亲褚裒成为女儿的有力支持,而且他不因皇亲身份把持朝政,这一点受到了群臣的敬重。褚裒任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京口(今镇江),拱卫京都,也守护着自己的女儿。
谢氏一族也因为褚蒜子而崛起。她的舅舅谢尚成为朝廷重臣,任豫州刺史。谢尚去世后,谢奕、谢万接替了谢尚的职务。陈郡谢氏由此成为一方诸侯。
褚蒜子从前朝重臣何充那里学会了平衡皇室与权臣。当时朝中还没有形成一家独大的士族,总理朝政的是会稽王司马昱(晋元帝司马睿之子,后来的简文帝),外戚褚氏没有政治野心,北方强敌后赵因内乱衰败无力南顾,所以永和年间是东晋南渡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兰亭集序》的一段文坛佳话或许是安定的一个印证。
桓温专权威逼建康
第二回
不过,安定之中也蕴藏危机,危机的中心是荆州刺史桓温。
桓温也是“皇亲”,他是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婿,娶了南康公主,拜驸马都尉,由此跻身士族。
那时候东晋国土几乎有一半被桓温掌握,看着桓温不断扩大地盘,渐渐干预朝政,褚蒜子出手了。在她的支持下,司马昱引扬州刺史殷浩,共同对抗桓温。王导堂侄王彪之任吏部尚书,有智谋有决断,成为司马昱的有力帮手。同时褚蒜子的父亲褚裒镇守京口,褚蒜子的舅舅谢尚掌控豫州,使桓温势力暂时只局限在长江上、中游。
桓温屡次请战北伐,收复失地,但朝廷始终顾虑桓温势力扩张而不允。桓温率军自江陵顺流而下,进驻武昌(今鄂州),威逼建康。
不过,当朝中再没有足以用来抵制桓温的将领时,还是只得让桓温总揽北伐大权。永和十二年(356),桓温任征讨大都督,八月大破姚襄,收复洛阳,修西晋诸陵,留兵守戍,自率大军退回江南,倡言晋廷还都洛阳。
恢复中原是东晋君臣的心结,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此起彼伏,这成了朝廷的软肋,桓温借此胁迫公卿,回军后长驻姑孰(今当涂),近逼建康,遥制朝廷。
褚蒜子屈从桓温之谋
第三回
升平元年(357)正月,晋穆帝年满十五岁,皇太后褚蒜子下诏,还政于穆帝,退居崇德宫。当时主政的是丞相司马昱,陆续进入朝廷中枢的还有王坦之、王珣、郗超、谢安等人。
但是,四年后,晋穆帝去世,尚未立太子。这怎么办?
褚蒜子有诏,当年成帝去世,因诸子年幼,由康帝、穆帝父子继位,现成帝之子已成年,应由成帝长子、琅琊王司马丕继位。
晋哀帝司马丕登基,改元隆和(362)。这是褚蒜子继自己的丈夫、儿子之后,扶持的第三位皇帝。
而此时桓温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但他顾忌朝中士族力量,不敢轻易入都。
晋哀帝迷信方士,沉湎丹药,不问朝政。不过,他建造了瓦官寺,大画家顾恺之还为瓦官寺绘维摩诘像壁画。
兴宁二年(364),晋哀帝服长生药中毒,不省人事,朝臣只得再请褚蒜子摄政。第二年晋哀帝去世,无后嗣,仍由皇太后褚蒜子主政,她扶立成帝次子司马奕继位,改元太和,改封会稽王司马昱为琅琊王。这是褚蒜子扶持的第四位皇帝。
再看桓温。他在这十几年间,以北伐为旗帜,战功显赫,掌握军事指挥权,逐步控制长江下游各州郡,他的根本目的是篡夺政权。
他从皇帝司马奕下手,听从谋士之计,诬称司马奕不能生育,三个儿子是后妃与他人私通所生,在民间广为传播。事关皇室血统,这可是大事。太和六年(371)冬,桓温领兵入建康,以宫廷秽乱为由,上书皇太后褚蒜子,要废司马奕,改立司马昱。
《晋书·后妃传》中对桓温觐见皇太后有生动描写,这也是史料中有关褚蒜子少有的细节记载——
太后方在佛屋烧香,内侍启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户前,视奏数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笔答奏云:“未亡人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温始呈诏草,虑太后意异,悚动流汗,见于颜色。及诏出,温大喜。
司马奕就这样被废为东海王,又降为海西公,成了东晋唯一被废黜的皇帝。琅琊王司马昱登基,史称简文帝,改元咸安。褚蒜子退居崇德宫。司马昱是褚蒜子扶立的第五位皇帝。
褚蒜子退居崇德宫
第四回
不过,桓温的如意算盘还是失算了。他本想以简文帝司马昱作为过渡,找机会逼迫他禅位给自己,但遭到了朝中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士族的有力抵抗。
咸安二年(372),司马昱去世,皇太子司马曜继位,史称孝武帝,改元宁康。这是褚蒜子扶持的第六位皇帝。
此时,褚蒜子不得不再次向权倾当朝的桓温屈服。因为皇帝年幼,又在居丧期间,褚蒜子命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暂代皇帝执政。诏令已在朝中公布,幸而被王彪之劝阻,将诏令封还。
她最终站在了士族一边,桓温到死也没有如愿“自立为王”。
桓温死后,群臣再一次请褚蒜子临朝称制。按辈分,褚蒜子只是司马曜的堂嫂,而且司马曜母亲还健在。但朝臣仍请褚蒜子辅政,足见对她执政能力的认可。太元元年(376)孝武帝司马曜成年亲政,褚蒜子退居崇德宫。
这一次她是真的退居了。
《建康实录》中说:“晋十一帝,有十陵,元、明、成、哀四陵在鸡笼山之阳,阴葬不起坟。康、简文、武、安、恭五陵在钟山之阳,亦不起坟。惟孝宗一陵在幕府山,起坟也。”
士族与皇室共治局面终结
尾声
谢安率子侄大败前秦的淝水大战,是太元八年(383)的事。这一战建功,奠定了陈郡谢氏的门阀地位。
就在淝水之战第二年,太元九年(384)六月,六十岁的褚蒜子去世。她三度临朝称制,先后扶持六位皇帝,在东晋十一帝中超过一半,在位约四十年,占东晋百年历史五分之二,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这期间,政局错综复杂,谯国桓氏以屡建军功而崛起,桓温死前将军权交给弟弟桓冲、南郡公爵位传给儿子桓玄,留下了后世变乱的隐患。同时,陈郡谢氏的地位得以确立,谢安成为与王导齐名的辅国重臣,淝水大捷为东晋王朝续命数十年。褚蒜子最后扶持的孝武帝在位二十四年,是东晋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正是在他手中,终结了士族与皇室共治的局面。
在学者薛冰看来,褚蒜子是南京人文史上值得书写的女性,遗憾的是,直到当代仍被遮蔽。东晋名臣,人人知道王导、谢安,但褚蒜子却鲜为人知。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史家往往忽略女性的历史功绩,所以关于褚蒜子的记载极为简略,几乎没有具体事件与细节。但是,在《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中,薛冰通过爬梳史料,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见证并参与东晋王朝兴衰、智慧与坚毅并举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