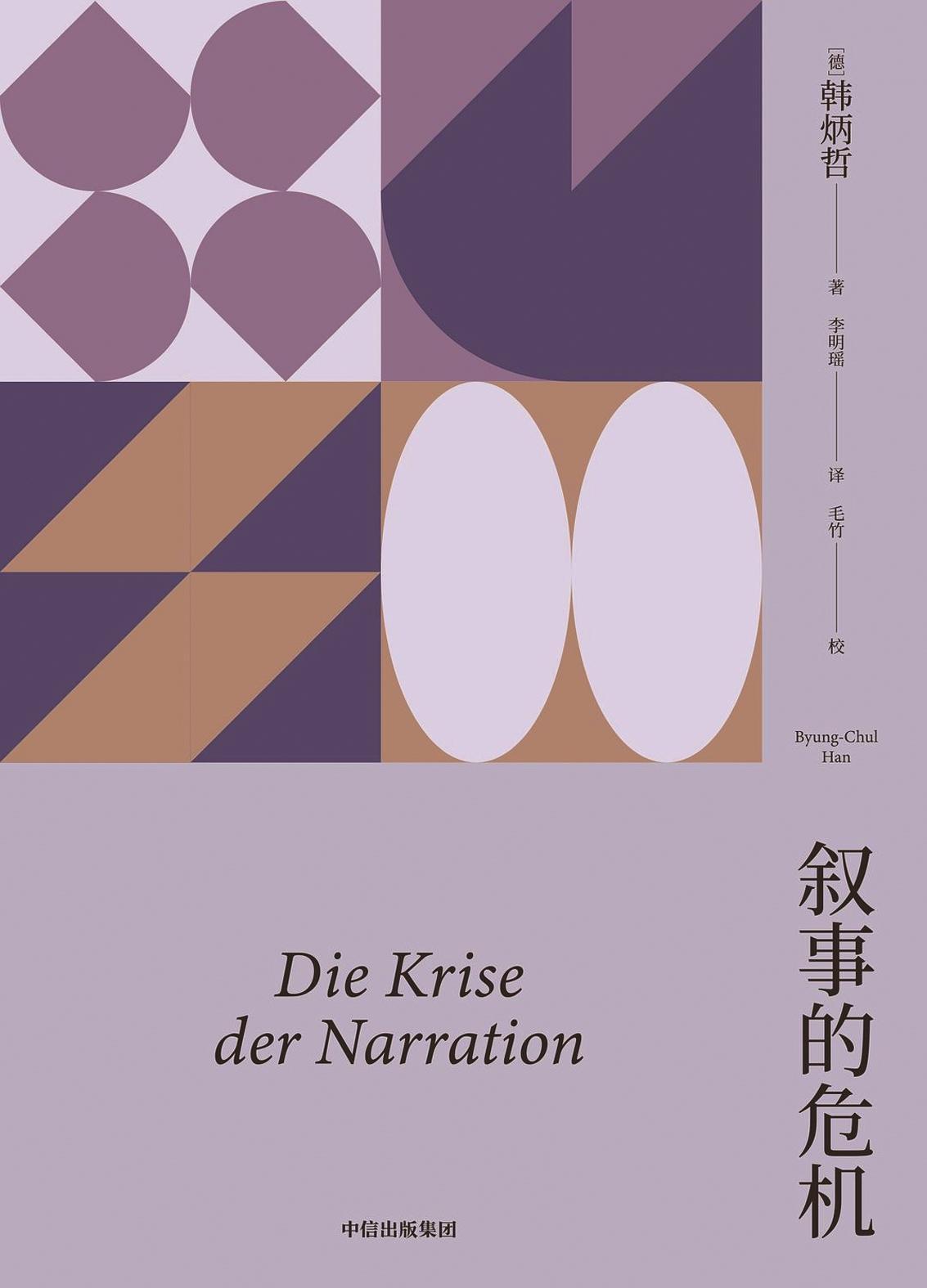□思郁
现在谈论韩炳哲有种疲软的状态。自从2019年开始,这位当红德国哲学家的著作被陆续引进中国,他已经出版的31种著作当中,截至目前,加上刚出版的《叙事的危机》等新三种,中文版已经出了22种。韩炳哲的著作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都是小册子,每本不过百页,涉及的话题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话题。他的著作简短、尖锐、紧迫,直指当下,他讨论大数据时代、手机智人、自拍、深陷点赞与分享中年轻人的虚妄的生活,他讨论我们关心的那些问题。在康德、福柯、德里达、海德格尔等等这些大名鼎鼎的名字背后,总有一点点属于他的思想的闪光碎片,他从来不担心暴露自己的浅薄,也不担心从无数人名那里借来的观念和概念,从某种意义上,他复活了这些概念和观念。
韩炳哲的写作毫无疑问是碎片化的,是不符合传统哲学的。韩炳哲的争议与其说他是一个哲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文体家更确切一些。
我当然并不是夸大其词。理论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理解的,不能让人理解的理论是一种思想上的伪善。在众多韩炳哲的著作中,我想推荐这本《叙事的危机》也是源于这个原因。相对于韩炳哲的其他著作,这本书涉猎的主题正好跟韩炳哲的写作有很大的关系。在这本书中,韩炳哲谈到了现代的危机,归根结底来说,是一种叙事的危机。
社交媒体上,看起来,人人都在讲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的泛滥反而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不会讲故事了。因为这些故事的讲述者并不能让自己的故事催生出更多的东西,所有的故事到了最后都指向了一种东西,那就是商品,讲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打造各种奇特的人设积攒流量,最后的目的就是进行一种消费主义的狂欢,进行直播带货,割韭菜。
而韩炳哲所说的叙事危机就在于,能开启和改变世界的讲述不是由某一个个体随意创造出来的,而是由时代的精神推动之下产生的,加上不同人的合力才能逐渐完成的。比如宗教的形成就是一种叙事,时间本身也具有叙事性,还有各种节日也是一种叙事。比如端午节,小朋友都知道这是纪念屈原的节日。这就是韩炳哲所说“没有故事,就没有节日和节日时间,也没有节日感,即程度更深的存在感”。而在后叙事时代,“节日被商业化,沦为事件和景观”。像“双十一”“618”这种节日没有任何内涵,只是购物的狂欢。
在韩炳哲看来,信息的漫溢是现代社会叙事危机的罪魁祸首。在《叙事的危机》当中,韩炳哲从报纸的消亡,手机智人的崛起,世界的祛魅、理论的衰落等方面分析了叙事危机产生的原因。尤其《理论即讲述》这一章节,非常值得关注。理论就是叙事的一种,叙事的危机即理论的危机。大数据时代,理论丧失了自己的领地。
比如提到笛卡尔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思故我在”,提到康德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康德的星空理论,想到尼采的时候会想到重估一切价值,这些理论并不能真正全面代表他们的思想,但却是最容易让普通读者理解和记忆的方式。我们需要借助各种媒介进行传播理论,哪怕这种理论在不断的传播过程当中被误读,被曲解。传播过程就是一个试错和纠正的过程,只有能传播开来的理论,才能产生影响力。那种只被小圈子里讨论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炳哲写作的文体就是一种传播学的尝试。你可以称他为思想的二道贩子,可以鄙视他没有任何原创的观念,但是你却不能忽略他的影响力。
韩炳哲告诫说,一旦哲学理论以科学自居的时候,它的衰败就开始了。这种衰败就是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开始的,因为哲学发明了太多自以为是的概念,自动将自己与大众理解的语言隔绝了起来;其次,哲学变成了学院里的一门学科,我们只能从哲学史中学习哲学,这就意味着哲学丧失了大众的生命力。他不无担忧地说,面对当下的这场叙事危机,哲学正面临着终结的威胁。
但是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韩炳哲的写作,正尝试着复活我们对哲学的兴趣,引导我们对抗这个只会用数据说话、不会讲故事的时代。
■好书试读
本杰明·拉斯克具备几乎所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却也因此被剥夺了一项特权:他没有一种英雄般崛起的经历。他的成长故事中缺乏砥砺和不屈不挠,也没有依靠坚不可摧的意志从近乎废墟之上为自己打造一个黄金铺路的命运。根据拉斯克家族《圣经》背面的记载,1662年,他父亲的祖先从哥本哈根迁往格拉斯哥,开始在北美殖民地贩卖烟草。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生意蒸蒸日上,随着业务不断扩展,家族中的一些成员移民到美国,以便就近监督供应商,并掌控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历经三代之后,本杰明的父亲所罗门买断了所有亲戚和外部投资者的股份。在他独自领导下,公司继续蓬勃发展,不久之后,他成为东海岸最显赫的烟草贸易商之一。
——《信任》
[美] 埃尔南·迪亚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那是我在皮村度过的头一夜。
往后我和工友之家及文学小组的人们渐渐熟了起来。我拜访了那天留下微信名片的史鱼琴、王成秀,以后又认识了同样做育儿嫂的林巧珍。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小海的店里逛逛,和万华山、小静逐渐熟了起来,也成了给文学小组讲课的老师的一员。在小付的邀请下,我开始参加每年度的新工人文学奖的最终评选,一般负责非虚构类。很难忘记头两年文学奖颁发的场景:破旧的平房会议室里没有暖气或空调,桌面下方冰冷的水泥地让穿着运动鞋的我脚冻僵了,只能不停地跺脚。桌面上却是热气腾腾,拥挤的人群哈出的热气汇成了笼罩的雾霭,人们的面容和声音都在这层雾霭里浮现,带着掩藏不住的兴奋和喜悦。平日纵横的沟壑被抹平,不管是领奖者、颁奖人还是等待者,每个人都似乎在一团理想的光影里浮动,脱离了寒冷坚硬的日常生活地面。这一刻大约就是文学小组存在的意义。
——《我的皮村兄妹》
袁凌 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