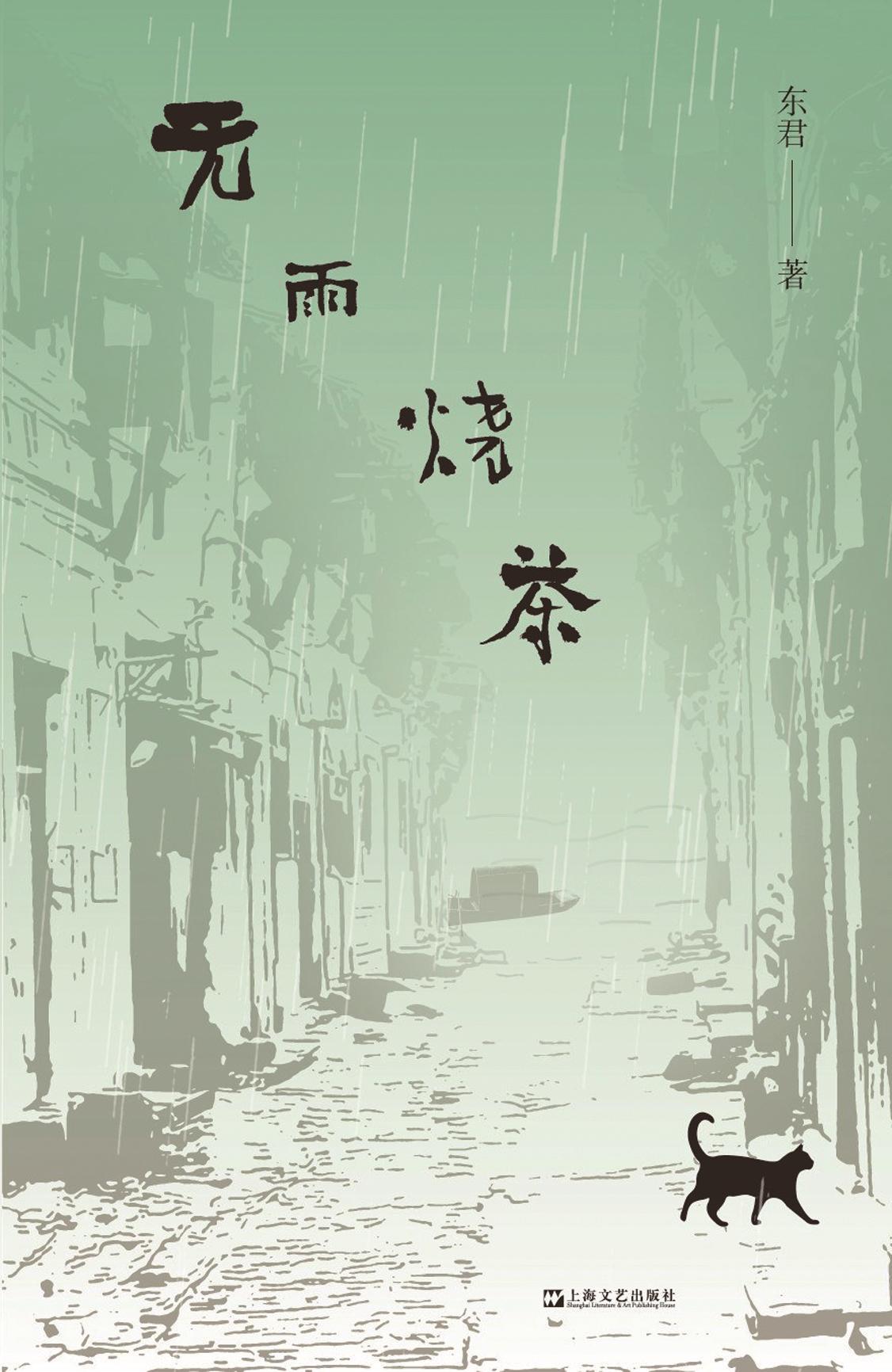写作者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在故乡的异乡者,一类是在异乡的怀乡者。一直以来,作家东君都生活在老家温州,“有些事因为空间距离太近,反倒不好写,因此我就在小说叙述中有意拉远了时间的距离”。有了距离,就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东君喜欢写故人、旧事、老房子,在他看来,这些都或多或少地承载着一些人的记忆,小而言之,一个字也承载着记忆。就像他新近出版的中短篇集《无雨烧茶》,“‘雨’字一经写出,就给人一种淅淅沥沥的感觉,这里面有视觉的记忆,也有听觉的记忆。‘茶’字拆开来,是艹、人、木,我们可以想象,人在草木丛中,清气浮动。一个茶字跟另一些文字组合在一起,足以唤起每个人不同的记忆。”
烟雨、新茶、悠长的老巷,勾勒出浙南老城的往日时光。“三官爷”、唱词先生、陶庵三老……没有主动跟上时代步伐的人们隐没于烟火日常。问他写这些旧事有什么用?东君会慢悠悠地回答:“一个城市需要一些跑得快的人,但也需要一些‘落伍’的人。”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
带出一种“说书情境”
读品:关于新书《无雨烧茶》,您曾提到两个关键词:“记忆”和“欲望”。十篇小说中的故人、旧事、老房子,都是围绕这两个关键词次第铺排开的。
东君:这本集子如果仅仅是写故人、旧事、老房子,那么我触及的只能是一个时代的表象,但我还是要把笔触伸到更为幽深的地方,触及那些人物的记忆与欲望。记忆总是与过去的生活有关,而欲望则与未来的生活有关。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那些人物何去何从、如何安放自我是我要关注和探询的。我曾在一次分享会上引用艾略特《荒原》的开头诗句:“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这一节诗里就有两个重要的词:回忆和欲望。
读品:《无雨烧茶》中每个短篇几乎都有一个故事引子,人物一般在你问我答中引出陈年旧事,这似乎是一种更接近民间故事的传统叙事方式,这种叙事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东君:我禀承的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比较常见的手法,但注入了自己的想法和写法,这样就可以带出一种“说书情境”来。儿时耳濡目染的民间文化较多,比如温州鼓词就是其中一种。温州鼓词就像说书,只不过是唱出来的。鼓词先生在我印象中大都戴着墨镜,坐在院子里的一张八仙桌或者戏台上,有板有眼地唱念。当时在乡间逢年过节或碰上红白喜事,都会请鼓词先生来唱。他们多用一种略带腔款的方言,要竖起耳朵仔细听才能听得懂。我哥哥经常晚上跑去听鼓词,很晚才回来,由我负责开门。第二天有空闲时间,他就跟我复述昨晚的故事。鼓词一般唱的是《三侠五义》《水浒》《红楼》《西游》这些。大概1980年初,已经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引进内陆。《射雕英雄传》还没播放,鼓词先生已经开唱《书剑恩仇录》。80年代中后期,我几乎读遍了金庸所有可以读到的武侠小说,最喜欢的还是《射雕英雄传》,开头就是写临安牛家村两株大松树下围着一堆村民,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瘦削的老者右手打着两片梨花木板,左手中竹棒敲打着一面小羯鼓,现在想来,这就是小说的引子,后面写到郭、杨两家,有点像《水浒传》里面的一种“弄引法”,也就是先用一段小文字徐徐导出大事件。我后来曾以现代小说的独白体戏仿金庸小说写了一个中篇小说《空山》,也是暗用过“弄引法”。
读品:《为张晚风点灯》一篇,柳先生教徒弟温州鼓词,除了“一琴二鼓三唱四白”,还要去闹市里跟牙郎学地道的方言土语,去桥头樟树下听路人讲闲话。这个学习的过程很有意思,其实磨炼写作跟学鼓词也有相通之处?
东君:我写《为张晚风点灯》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些,但这篇小说的叙述腔调的确是有意模仿鼓词先生讲故事的调调。有些方言俗语掺入温州当地的鼓词、斗歌等曲艺里面,念出来别有一番情味。鼓词偏俗,斗歌近雅;前者相当于我们坊间流行的通俗小说,后者则相当于诗词文赋。这些地方曲艺最大的特点就是汲取了一部分古老的方言土语。
在标准普通话普及的今天,方言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一些地方性的小传统,更好地保存某个族群的记忆。遗憾的是,大量方言词汇因为无法转换成对应的普通话,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就慢慢地从日常生活里淡出。如果脱离小说文本设置的具体情境,外人未必能领会某些方言词汇的意思,但把它们还原到小说人物之间的对话和对地方风情的描述中去,就大致可以揣摩。有些方言词汇跟我们的生活习俗相连,化到小说里面去,用得好,的确能让某个句子或片段变得鲜活起来,营造出一种浓重的烟火气。同样一个东西,用书面语还是方言俗语来称呼,不仅会影响作者观看世俗的角度,还会影响他言说的腔调。我生活在方言中,我的小说中即便很少掺和方言,但方言所带来的那种思维方式、言说氛围依旧可以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我的文字里,因此我想,那些鼓词先生在这方面应该跟我会有大致相同的感受。
“本地”意识也是“平民”意识
读品:全书,尤其是开篇《美人姓董,先生姓杨》集中体现了温州人的“本地”意识,长期浸泡其中,您认为这种强烈的“本地”意识从何而来?
东君:在我生活的小地方,“本地人”是一种身份认同,连类而及,就有了本地鸡、本地卵、本地杨梅、本地柑橘等说法,细究起来,这大概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吧。前阵子端午节,我吃的就是本地的灰汤粽。在我们这里,端午节如果拿“五芳斋”粽子送人就好比拿“肯德基”汉堡请客,总嫌情意不够厚重。毕竟,本地粽是手工粽,是带着一份浓浓乡情的。按照本地习俗,从初一到除夕,从一个人出生到死亡,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讲究的。小说家了解这些,认同这些,自然也就有了一种“本地”意识,说到底,这也是小说家必须具备的一种“平民”意识。
读品:您的小说中,不时有带着神性的器物、文物穿插其间,在您看来,收藏某种器物反映了人怎样的心态?您小说中的旧色是否跟那些旧时的器物散发的气息有关?
东君:我写过西乡(乐清县西)旧事,平常也喜欢观赏旧物,但我没有收藏的癖好。我在多年前见过一位民国藏书家的藏书印章:曾在倪悟真处。但他收藏的那些书后来被人一把火烧掉了。因此,无论是什么器物还是文物,在我看来,都是过眼、过手而已。
我写这些系列小说时,有意给它铺上了一层旧色。我有一个观点:思想如果是旧的,文字再新,也会过时;思想如果是新的,文字不怕旧。清代画家石涛说过这么一句话:“笔墨当随时代”。这个“随”,是跟随的意思?显然不是,笔墨如果紧紧跟随时代,未必是好事。这句话应是随时代的变化有自己的变与不变。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找到切合自己的笔墨。
“植物记忆”比“矿物记忆”更长久
读品:《在陶庵》写到一家像世外桃源一样的书店,其中“陶庵三老”等爱书人的日常闲谈与他们贯穿一生的友情都令人动容。对于他们、对于您来说,阅读和写作意味着什么?您是否担心纸质书有一天会消失?
东君:我至今仍然保持着纸质阅读的老习惯。我的写作进度很慢,阅读也慢,慢一点,我才会记住更多一点。艾柯把记忆分为“植物记忆”与“矿物记忆”。所谓矿物记忆,在今天看来,它的载体就是电脑或手机,而植物记忆的载体就是植物造的纸。我总觉得植物记忆更长久,更可信赖。比如一些文学类作品,我如果只是在手机上浏览,很难谈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也许,这只是一个阅读习惯问题。
人工智能的不断升级可能会颠覆我们的传统写作,使我们今天所认可的写作标准丧失意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停止写作?当然不是。在我们还能对抗这一切的时候,仍然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为后来者保持一部分鲜活而持久的矿物记忆或植物记忆。
读品:十篇小说的内容情节,既在日常之中,又似乎超脱于世俗之外。我在阅读时,总会产生类似佛教“一切皆空”“诸行无常”的领悟。这是您的创作所要表达的初衷吗?怎样的生活经历和写作经验造就了这样的观念与领会?
东君: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中国的四大名著虽然称为“小说”,其实是“大说”。四大名著都有一种“天下观”。《三国演义》开头便是:“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红楼梦》从女娲炼石补天说到青埂峰下的石头;《水浒传》先讲七十二天罡,三十六地煞的传说;《西游记》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从天道的眼光看人物,而非人道。我写的是短篇小说,虽然没有采用这种“天下观”,但还是有意无意地借用了一种“天道的眼光”,那些笔下的人物有的在滚滚红尘里依旧执迷不悟,有的渡尽劫波之后,能勘破无常,回归日常。现在回想起来,早年读《红楼梦》中的《好了歌》、郑板桥《道情十道》、金圣叹托名施耐庵作的《水浒传》序文,我就有一种类似你说的“一切皆空”“诸行无常”的感觉。什么“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什么“劝君更尽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头”,什么“有时风寒,有时泥雨,有时卧病,有时不值,如是等时,真住牢狱矣”……这些诗句里面潜藏着多少人世间循环往复的悲辛。
读品:2017年,您和几位友人联合创办了白鹭书院。在书院里办了青少年写作营、“道坦讲座”和新书分享会。“道坦讲座”这个名字起得有趣,您能就此谈谈吗?
东君:我和几位同道选择可楼创办白鹭书院,纯属巧合。有一天下午,我带着好奇心第二次走进刚刚修复的可楼时,发现这里已经没有之前的荒芜景象了。我登上那架曲折幽暗的木质楼梯时,忽然看到二楼的墙上有一个镂空的“东”字,就情不自禁地掏出手机,给这里的新主人虞海泽打了一个电话。当他听说我要借此办一座书院,就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回复。进驻可楼之后,请大家为书院取名。为什么最后认定“白鹭书院”这个名称?一是乐清水泊海滨多白鹭,二是白鹭的意象入诗也美,它是自由、优雅的象征。白鹭书院的LOGO底下有一行细字“静静地向高处飞翔”,正是取自沃尔科特的一首长诗《白鹭》。书院的活动分两个板块:公益文化平台和创意写作中心。“道坦讲座”曾邀请过小说家张翎、评论家黄德海和张定浩、诗人郑愁予、学者川岛郁夫、文史专家张炳勋等。创办白鹭书院,寄托着一份以文会友、以文会师、以文会学的愿景。
东君
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及诗与随笔。结集作品有《东瓯小史》《某年某月某先生》《徒然先生穿过北冰洋》《面孔》《无雨烧茶》等。另著有长篇小说《浮世三记》、评论集《隐秘的回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