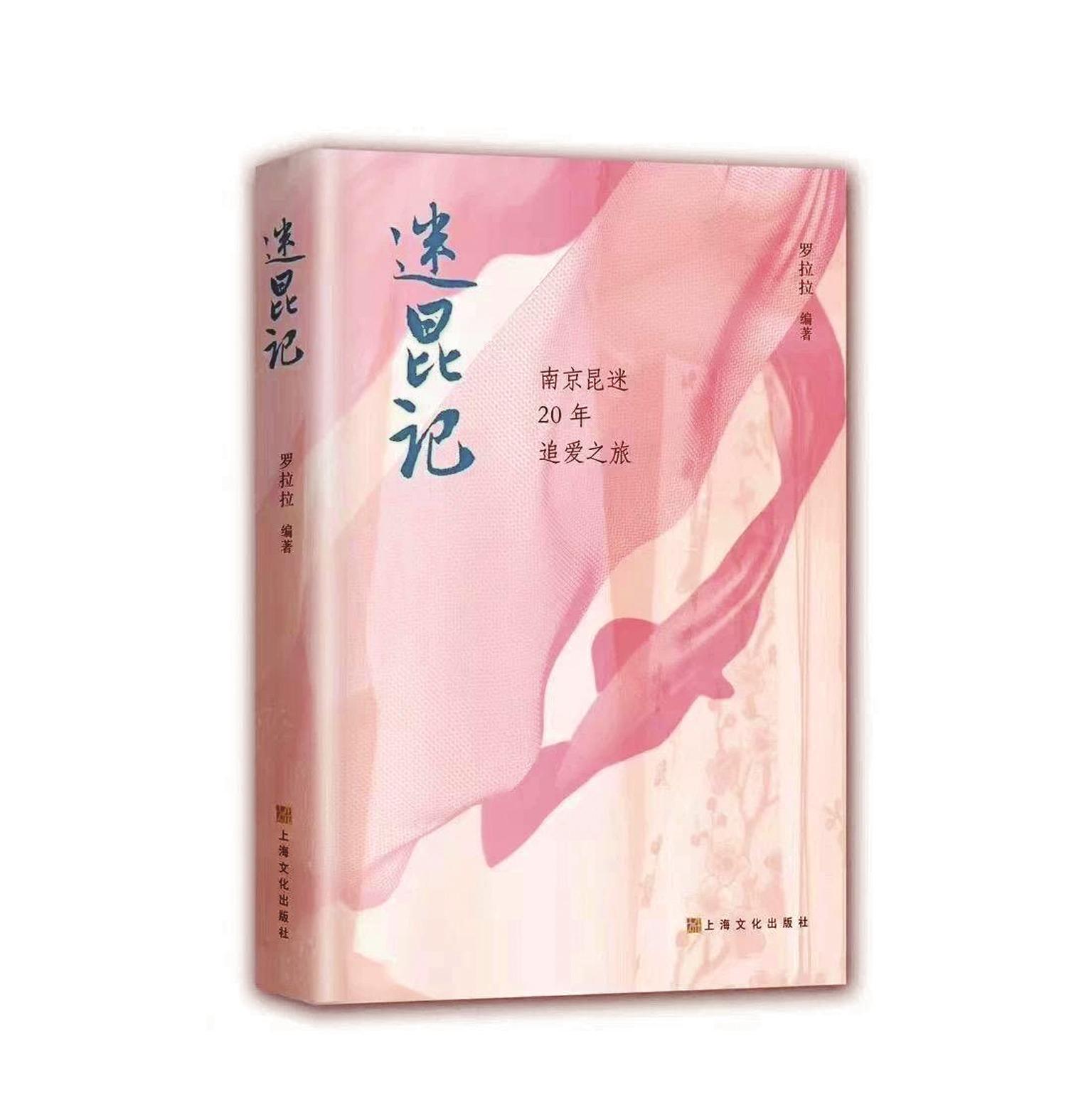2024年初夏的一天,南京紫金山北麓一处院落里,一声声婉转的昆腔随着欢声笑语荡漾开来。
律师、教师、编辑、作家、科研工作者、高校学生、艺术家、设计师……还有著名昆剧演员单雯、著名京剧演员彭林刚等,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因昆曲而结缘聚会。
一聚就是20年。月牙湖、秦淮河、古林公园、灵谷寺、美术馆……先后23次的昆剧迷追爱之旅,在南京城的角角落落,钤上了昆曲的印记。
紫金山北麓的这场聚会,便是第23场。在聚会上,活动发起人、作家罗拉拉,带来了她编著的新书《迷昆记》,这本书是对之前22场聚会的记录,更是映照昆剧精华与风雅南京的一面镜子。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白雁
再续旧缘,28年后与昆剧“贴身重逢”
罗拉拉与昆曲的情缘,可以追溯到近50年前。1976年,作为宝应县小红花宣传队的一名小演员,她随团来南京参加省里的文艺汇演,被招待看了一场昆剧《十五贯》。跌宕起伏的剧情、活灵活现的表演,让她觉得有趣,娄阿鼠两手交叉、拇指转动的动作,让她印象格外深刻。
与昆曲的情缘,似乎就定格在了1976年。时隔多年后,罗拉拉才知道当年所看的《十五贯》是传字辈艺人周传瑛、王传淞主演。而直到28年后,那一帧画面才又活泼泼地动了起来。
2004年5月,罗拉拉受师妹徐蔚邀请去参加一个校友聚会,地点在南京东郊的阳山碑材。徐蔚和罗拉拉同为苏州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徐蔚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她是苏州大学唯一一届昆曲艺术专业班的毕业生。
苏州大学昆曲艺术专业班开设于1989年,由苏大中文系与昆剧传习所合办,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拥有正规本科学历的昆曲艺术专业班。开设这个班的目的在于,培养一批既懂学术又懂舞台的昆剧人才,建立一个既能从事学术研究又能粉墨登场的昆曲研究中心。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一初衷最终未能达成,毕业班的同学后来去了各种工作岗位,唯有一人从事昆曲事业。
此次聚会,罗拉拉不仅见到了当年苏州大学昆曲艺术专业班的学弟学妹们,还见到了当年昆曲班的班主任周秦。大家在一个茶楼上坐定,寒暄之后,周秦取出一枚竹笛,以悠扬的笛声正式开启了这场聚会。在周秦的伴奏下,已经毕业十年的学生们唱起了根据李后主《浪淘沙》谱写的昆歌: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十年间,岁月和不同的人生境遇改变了昔日同窗的容颜,一曲昆歌却忽然将他们化入同一意境。惆怅的惋叹的,审美的远古的,此时的彼时的,在那一刻深深地打动了罗拉拉。她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28年后才与昆曲贴身重逢的我,无意之间撞到‘半堂度曲课’。”
聚会次日,罗拉拉在网上以《半堂度曲课》为题发帖,引发了一波网络热评。看到帖子的朋友们,纷纷怂恿罗拉拉“试水”,操办一堂“度曲课”,让更多人领略昆曲的魅力。罗拉拉有些心虚,因为她既不会唱昆曲,也不会吹昆笛,甚至并不认识太多唱昆曲的朋友。
短暂的犹豫之后,罗拉拉决定试试,天性热情开朗的她开始呼朋唤友、穿针引线地张罗“度曲课”。2004年10月,各种机缘巧合之下,罗拉拉张罗的第一场曲会在南京顺利举办。巧的是,这一年,也是青春版《牡丹亭》诞生的年份。
二十年追爱,为南京钤上昆曲印记
从2004年到2022年,由罗拉拉牵头,先后在南京举行了22届昆曲曲会。2017年开始,罗拉拉有意识开始收集过往资料,除了自己攒下的,她还向所有参加过曲会且尚有联系的朋友一一征集照片和文字。
历时七年,《迷昆记》成书。全书以时间为线索,分22个单篇呈现22届昆曲曲会,又依照时间顺序用《欸乃初起》《蓬勃生机》《魔力磁铁》《学而时习》《花繁浓艳》五个章节归纳各篇。五个章节的名称用心别具,恰如其分地展示了曲会从无到有、从单薄到繁茂的发展历程,也展示着罗拉拉和她的同道朋友们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2004年10月30日的第一届曲会,地点选在南京城东月牙湖畔的明湖山庄,一个旁侧有水有芦苇的亭子里。当天晴好,有阳光有微风。一曲《牡丹亭·惊梦》【皂罗袍】响起,眼前情景正与曲中“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呼应。曲会吸引了小区里的居民,大家纷纷围拢过来,有的还搬来椅子坐下同听,最小的“听众”仅有七个月大,在妈妈怀里咿呀应和。参加活动的闫安后来总结当日情形:“杨柳湖畔,惠风和畅,昆腔咿呀,佳人妩媚。”而在罗拉拉的提议下,《皂罗袍》则成了以后每次曲会的开场曲。
2016年3月27日第十三届曲会,对罗拉拉而言有着特别的记忆。曲会的地点别出心裁地选在了户外,南京紫金山南麓、灵谷寺东北的临瀑阁,这里亭台楼阁层层叠叠,与周围幽静清雅的自然环境相映成趣。
在户外办曲会,其实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有名的虎丘曲会,是苏州历史上规模宏大的民间自发的昆曲集会,文人雅士、曲词名家、专业艺人、百姓群众都会自发地在中秋之夜,聚集虎丘,吟咏较艺、竞技演唱。南京的莫愁湖,明清时期也盛行户外曲会。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就写到了莫愁湖曲会,“诸名士看这湖亭时,轩窗四起,一转都是湖水围绕,微微有点熏风,吹得波纹如縠。亭子外一条板桥,戏子装扮了进来,都从这桥上过。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门,让戏子走过桥来,一路从回廊内转去,进东边的格子,一直从亭子中间走出西边的格子去,好细细看他们袅娜形容……”
临瀑阁曲会,丝毫不输古时。更为奇妙的是,那天临瀑阁附近从正午阳光灿烂到黄昏余晖满天,光线的变化也极富诗意。而在罗拉拉的记忆里,最为神奇的是,开场大合唱《皂罗袍》响起时,山间众蝉齐鸣,自然界的昆虫和自称“昆虫”的昆剧迷,共同奏响和谐天籁。
单雯穿着日常服装参加了临瀑阁曲会,当她站上舞台、亮开嗓子“变身”《南柯梦·瑶台》里的琼芳公主,所有现场的人都跟着她瞬间穿越。参加当天曲会的周晓阳后来回忆:“我真的想掐自己大腿一下,想看看到底是不是在做梦。后来一看,我四岁的娃娃好像也有同感,他一反常态坐在小桥边,看着台上,变得痴痴的。”
“小众”也会扩展,“精英”也会繁衍
与青春版《牡丹亭》同龄的昆曲曲会,见证了二十年来昆曲从式微到复兴、从小众到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过程。而就在2004年,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私人化的曲会竟然成就了一场长达20年的昆剧迷追爱之旅,并且规模、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丰富和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
从《迷昆记》的记载来看,曲会涉及的人士有罗拉拉、彭林刚、孙芸、陈薇亦等昆剧业余爱好者,也有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龚隐雷、王斌,昆曲新生力量单雯、施夏明、张争耀、曹志威,笛师王建农、迟凌云、曾明、姚琦等名家和名演员;还有不断加入的昆曲爱好者,他们是作家、编辑、律师、艺术家、设计师、教师、工程师等,涵盖了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正如南大青年学者、群学书院联合创始人陆远所言:“这些民间的昆曲爱好者,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化素养,对曲律、音韵的精致追求,助力推动了一个非常古老又曲高和寡的剧种一直流传到今天。”
曾执教于苏州大学的徐斯年先生,则从专业的角度出发,对这二十多届曲会予以高度赞誉,“我认为,昆曲在民间的传播过程不是由雅变俗,而是升俗入雅,所以这种活动是‘小众性’的。数百年的历史积累,完善了、也固化了昆曲的品性,它的诗性、音乐性和文人性是无与伦比的,也是不可取代的。品曲的人,要有一点书卷气,要有一点乐感;拍曲,需懂些乐理,至少要会辨别板眼。否则难以‘登堂’。若要‘入室’,则更要审音析律,追求清工本色。所以,一个好的曲社,一定要有一位好的‘拍先’,即拍曲先生,和一位好的笛师。这些,都决定着民间昆曲活动的小众性和精英性。不过,‘小众’也会扩展,‘精英’也会繁衍,喜欢昆曲的年轻朋友越来越多就是明证。这对提升我们民族的文化品性,无异也是一个好消息。”
●曲中人语
鲁敏(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由曲会起,我特别喜欢上了昆笛,可能也跟女儿习笛有一定关系。昆笛之沉静、悠远,哀而不伤,尤其在曲会这样“简约丰美”的形式中,大有“主脑”之感。尤其喜欢笛师的表情与身姿,其不表之情、不动之舞,有时比舞台上那些正在演戏的妙人们更加吸引我。
孙芸(资深律师、曲友,苏州大学中文系昆曲艺术专业毕业生):最初的曲会很小,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喜欢,不是走向大众,而是走向了许多有着精神需求的人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和曲会一起成长完善,这是一个可以坦坦荡荡表达自己所爱的地方,始终不讳言爱昆曲,坚持爱昆曲,这世界能坚持爱一件事而不失望很不易,这过程给予我们力量。
陈卫新(设计师、作家、书画家):这样的民间曲会意义很大。我认为任何“文化的传承”都必须在生活之中,曲会对于昆曲的影响也未可知,但对于昆曲以外的人是个福音,他们可以通过曲会更加靠近昆曲了解昆曲。我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昆曲演员或是昆曲研究者参加到了这种曲会中。这应该是最好的意义。
张争耀(昆曲演员,获“中国戏曲红梅金花”):艺术传播不能只是曲高和寡地在殿堂剧场里浮于半空中,而需要实实在在地在民间,相信戏曲文化能发展、传承至今,也是因为这一点。对于我们昆曲专业工作者,也要秉承这一点,踏踏实实地学好每一出戏、唱好每一出戏,为喜爱它的人们演出、也让更多的人可以爱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