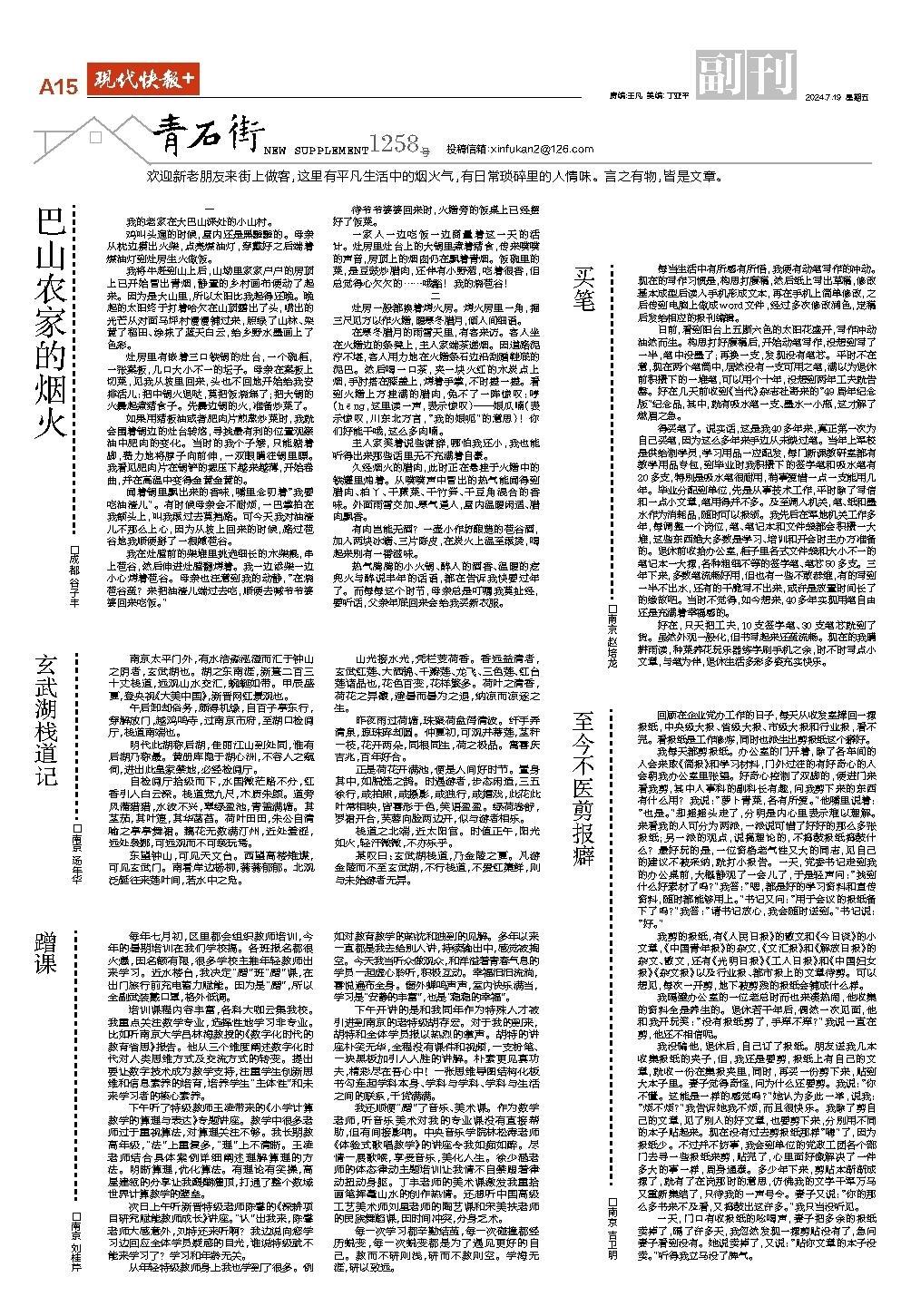□成都 谷子丰
一
我的老家在大巴山深处的小山村。
鸡叫头遍的时候,屋内还是黑黢黢的。母亲从枕边摸出火柴,点亮煤油灯,穿戴好之后端着煤油灯到灶房生火做饭。
我将牛赶到山上后,山坳里家家户户的房顶上已开始冒出青烟,静置的乡村画布便动了起来。因为是大山里,所以太阳比我起得还晚。晚起的太阳终于打着哈欠在山顶露出了头,喷出的光芒从对面马坪村慢慢铺过来,照绿了山林、染黄了稻田、涂抹了蓝天白云,给乡野水墨画上了色彩。
灶房里有嵌着三口铁锅的灶台,一个碗柜,一张案板,几口大小不一的坛子。母亲在案板上切菜,见我从坡里回来,头也不回地开始给我安排活儿:把中锅火退哒,莫把饭烧焦了;把大锅的火爨起煮猪食子。先爨边锅的火,准备炒菜了。
如果用猪板油或者肥肉片煎熬炒菜时,我就会围着锅边的灶台转悠,寻找最有利的位置观察油中肥肉的变化。当时的我个子矮,只能踮着脚,费力地将脖子向前伸,一双眼睛往锅里瞟。我看见肥肉片在锅铲的摁压下越来越薄,开始卷曲,并在高温中变得金黄金黄的。
闻着锅里飘出来的香味,嘴里念叨着“我要吃油渣儿”。有时候母亲会不耐烦,一巴掌拍在我额头上,叫我滚过去莫挡路。可今天我对油渣儿不那么上心,因为从坡上回来的时候,路过苞谷地我顺便掰了一根嫩苞谷。
我在灶膛前的柴堆里挑选细长的木柴棍,串上苞谷,然后伸进灶膛翻烤着。我一边添柴一边小心烤着苞谷。母亲也注意到我的动静,“在烧苞谷蛮?来把油渣儿端过去吃,顺便去喊爷爷婆婆回来吃饭。”
待爷爷婆婆回来时,火塘旁的饭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
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商量着这一天的活计。灶房里灶台上的大锅里煮着猪食,传来噗噗的声音,房顶上的烟囱仍在飘着青烟。饭碗里的菜,是豆豉炒腊肉,还伴有小野葱,吃着很香,但总觉得心欠欠的……哦豁!我的烧苞谷!
二
灶房一般都挨着烤火房。烤火房里一角,掘三尺见方以作火塘,暖寒冬腊月,倾人间细语。
在寒冬腊月的雨雪天里,有客来访。客人坐在火塘边的条凳上,主人家端茶递烟。因道路泥泞不堪,客人用力地在火塘条石边沿刮蹭鞋底的泥巴。然后喝一口茶,夹一块火红的木炭点上烟,手肘搭在膝盖上,烤着手掌,不时搓一搓。看到火塘上方挂满的腊肉,免不了一阵惊叹:哼(hēng,这里读一声,表示惊叹)——娘瓜喃(表示惊叹,川东北方言,“我的娘呃”的意思)!你们好能干哦,这么多肉喃。
主人家笑着说些谦辞,哪怕我还小,我也能听得出来那些话里无不充满着自豪。
久经烟火的腊肉,此时正在悬挂于火塘中的铁罐里炖着。从噗噗声中冒出的热气能闻得到腊肉、柏丫、干蕨菜、干竹笋、干豆角混合的香味。外面雨雪交加、寒气逼人,屋内温暖闲适、腊肉飘香。
有肉岂能无酒?一壶小作坊酿造的苞谷酒,加入两块冰糖、三片陈皮,在炭火上温至滚烫,喝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热气腾腾的小火锅、醉人的酒香、温暖的疙兜火与醉说丰年的话语,都在告诉我快要过年了。而每每这个时节,母亲总是叮嘱我莫扯经,要听话,父亲年底回来会给我买新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