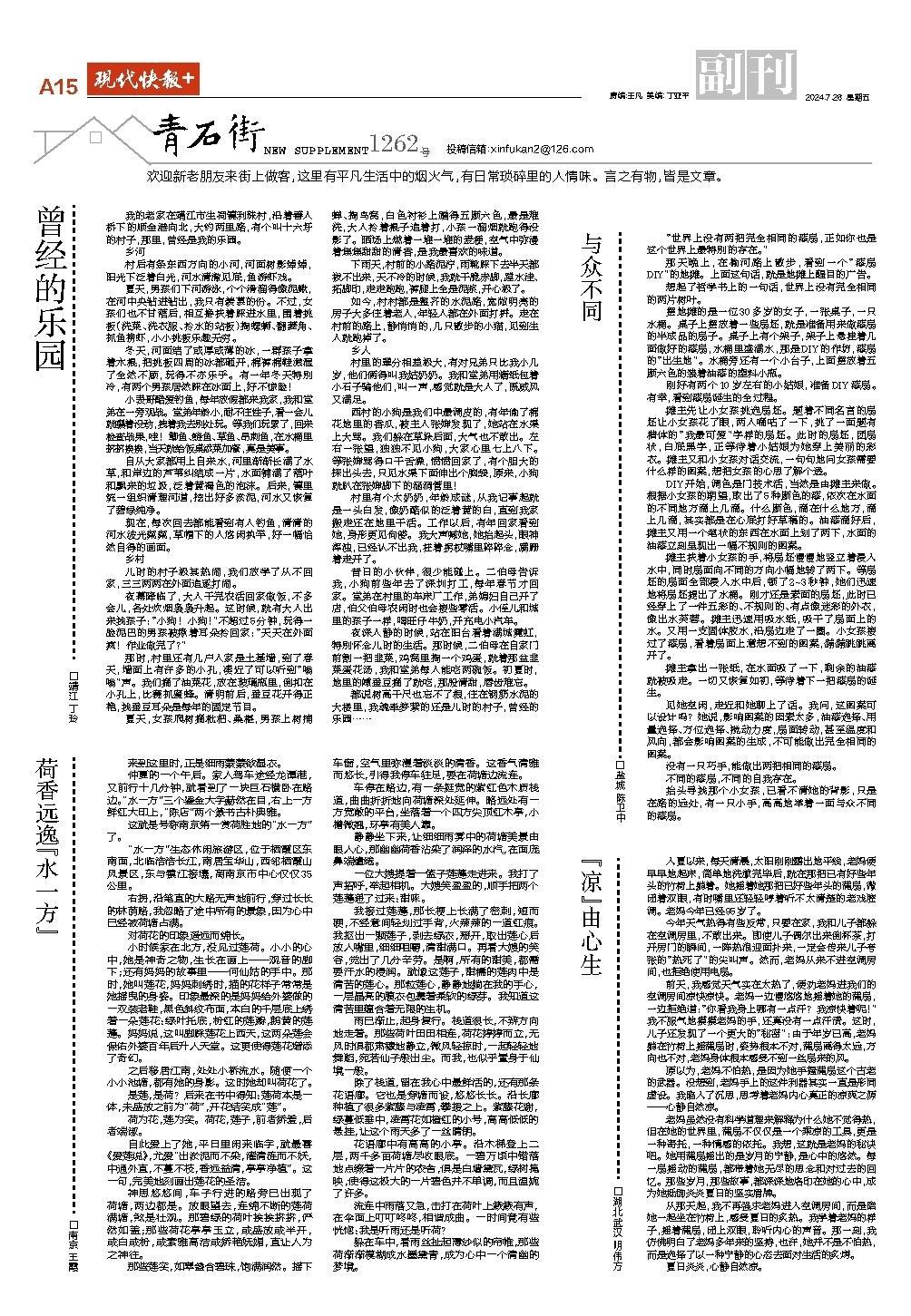□靖江 丁玲
我的老家在靖江市生祠镇利珠村,沿着善人桥下的顺金港向北,大约两里路,有个叫十六圩的村子,那里,曾经是我的乐园。
乡河
村后有条东西方向的小河,河面树影绰绰,阳光下泛着白光,河水清澈见底,鱼游虾戏。
夏天,男孩们下河游泳,个个滑溜得像泥鳅,在河中央钻进钻出,我只有羡慕的份。不过,女孩们也不甘落后,相互搀扶着踩进水里,围着挑板(洗菜、洗衣服、拎水的站板)掏螺蛳、翻菱角、抓鱼捞虾,小小挑板乐趣无穷。
冬天,河面结了或厚或薄的冰,一群孩子拿着木棍,把挑板四周的冰都砸开,棉裤棉鞋溅湿了全然不顾,玩得不亦乐乎。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有两个男孩居然踩在冰面上,好不惊险!
小表哥酷爱钓鱼,每年放假都来我家,我和堂弟在一旁观战。堂弟年龄小,耐不住性子,看一会儿就嚷着没劲,拽着我去别处玩。等我们玩累了,回来检查战果,哇!鲫鱼、鲢鱼、草鱼、昂刺鱼,在水桶里挤挤挨挨,当天就给饭桌添菜加餐,真是美事。
自从大家都用上自来水,河里渐渐长满了水草,和岸边的芦苇纠结成一片,水面铺满了落叶和飘来的垃圾,泛着黄褐色的泡沫。后来,镇里统一组织清理河道,挖出好多淤泥,河水又恢复了碧绿纯净。
现在,每次回去都能看到有人钓鱼,清清的河水波光粼粼,草帽下的人悠闲执竿,好一幅怡然自得的画面。
乡村
儿时的村子极其热闹,我们放学了从不回家,三三两两在外面追逐打闹。
夜幕降临了,大人干完农活回家做饭,不多会儿,各处炊烟袅袅升起。这时候,就有大人出来找孩子:“小狗!小狗!”不超过5分钟,玩得一脸泥巴的男孩被揪着耳朵拎回家:“天天在外面疯!作业做完了?”
那时,村里还有几户人家是土基墙,到了春天,墙面上有许多的小孔,凑近了可以听到“嗡嗡”声。我们摘了油菜花,放在玻璃瓶里,倒扣在小孔上,比赛抓蜜蜂。清明前后,蚕豆花开得正艳,找蚕豆耳朵是每年的固定节目。
夏天,女孩爬树摘枇杷、桑椹,男孩上树捕蝉、掏鸟窝,白色衬衫上蹭得五颜六色,最是难洗,大人拎着棍子追着打,小孩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晒场上燃着一堆一堆的麦梗,空气中弥漫着焦焦甜甜的清香,是我最喜欢的味道。
下雨天,村前的小路泥泞,雨靴踩下去半天都拔不出来,天不冷的时候,我就干脆赤脚,蹚水洼、拓脚印,走走跑跑,裤腿上全是泥浆,开心极了。
如今,村村都是整齐的水泥路,宽敞明亮的房子大多住着老人,年轻人都在外面打拼。走在村前的路上,静悄悄的,几只散步的小猫,见到生人就跑掉了。
乡人
村里的辈分相差极大,有对兄弟只比我小几岁,他们俩得叫我姑奶奶。我和堂弟用糖纸包着小石子骗他们,叫一声,感觉就是大人了,既威风又满足。
西村的小狗是我们中最调皮的,有年偷了棉花地里的香瓜,被主人张婶发现了,她站在水渠上大骂。我们躲在草垛后面,大气也不敢出。左右一张望,独独不见小狗,大家心里七上八下。等张婶骂得口干舌燥,愤愤回家了,有个胆大的探出头去,只见水渠下面伸出个脑袋,原来,小狗就趴在张婶脚下的涵洞管里!
村里有个太奶奶,年龄成谜,从我记事起就是一头白发,像奶酪似的泛着黄的白,直到我家搬走还在地里干活。工作以后,有年回家看到她,身形更见佝偻。我大声喊她,她抬起头,眼神浑浊,已经认不出我,拄着拐杖嘴里碎碎念,蹒跚着走开了。
昔日的小伙伴,很少能碰上。二伯母告诉我,小狗前些年去了深圳打工,每年春节才回家。堂弟在村里的车床厂工作,弟媳妇自己开了店,伯父伯母农闲时也会接些零活。小侄儿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喝旺仔牛奶,开充电小汽车。
夜深人静的时候,站在阳台看着满城霓虹,特别怀念儿时的生活。那时候,二伯母在自家门前割一把韭菜,鸡窝里掏一个鸡蛋,就着那盆韭菜蛋花汤,我和堂弟每人能吃两碗饭。初夏时,地里的嫩蚕豆摘了就吃,那股清甜,唇齿难忘。
都说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住在钢筋水泥的大楼里,我魂牵梦萦的还是儿时的村子,曾经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