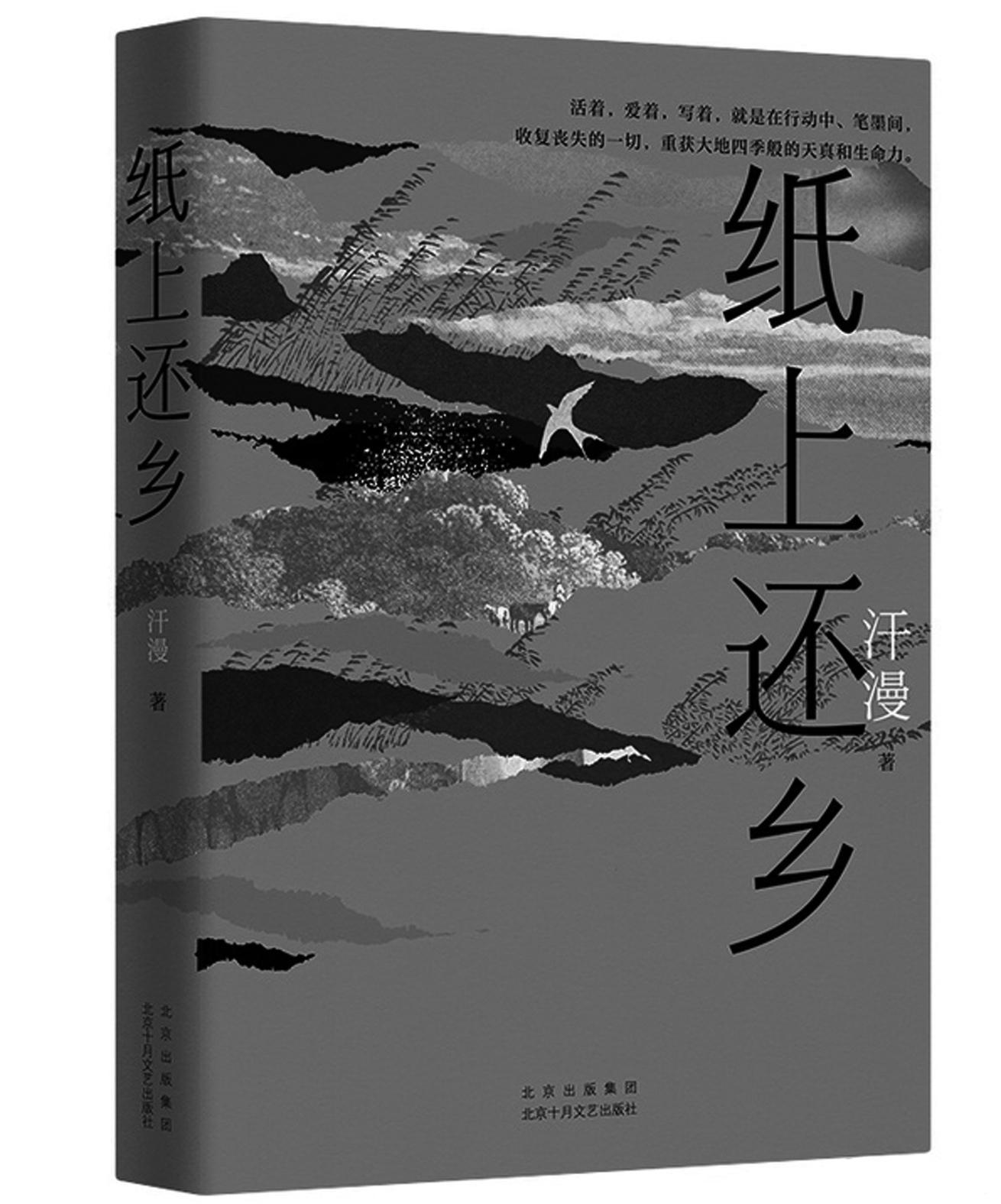□王若水
汗漫的新作《纸上还乡》是一部故乡之书,献给这世上所有的异乡人。
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曾把笔端朝向故乡。在汗漫既往的诗歌、散文中,关于故乡的歌谣早已经连绵不绝地唱起,只是他需要一次集中、专注、盛大的返乡之旅,不仅是返回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南阳盆地,更是回到浩荡苍茫的民族历史,辽阔永恒的自然天地。而这返乡的途径尤为重要,纸墨之上,方寸之间,以语言重建丧失的一切。纸上还乡,亦是回到语言的故乡,以写作重新辨认自我,为故乡赋形,抵达诗性的存在。这一返乡之旅完成后,对于作者而言,即便“我”不在故乡,而故乡在“我”。
与常见的怀人忆旧、触物抒情的故乡类主题散文不同,汗漫的书写背后始终浮现着对于“故乡”这一母题深沉的思索追问:我们为何需要返乡?故乡带给了我们什么?异乡之人如何在纸上重建故乡?在文中,类似的表达反复回响着:“在异地,一个人才能获得故乡”“一个人离开出生地,在远方,才能获得乡愁和诗意”“所谓故乡,就是亡故了的家乡,就是消失了的旧人物、旧时光、旧景象。”。可见,若想读懂“还乡”,首先要洞悉“丧失”。
在巨变的时代里,在漫长的一生中,丧失不断发生着,人们远走他乡,快步向前,又向着自己的来处频频回望,“从前的山水城阙、世故人情,被崭新的建筑学、经济学、政治社会学,雨打风吹去”,作者意识到,对于任何人而言,地理意义上的故乡都难以返回。许多人有着强烈的异乡感、过客感,因而“纸上”的返乡,即通过语言唤起对故乡旧时风物的感知、记忆,将漂泊的灵魂与安然宽厚的故土相连接,是迫切而必要的。
那么,纸上返乡,故乡赐予了我们什么?作者用诗性思维书写故乡的散文,缓步前行在南阳盆地的山川草木间,从烟火人家、花朵翕张处,重新感受语言的质地和生命。“宛然、宛如”,是南阳大碗巨阔的盆地在头顶浮动;“针对”是女人们对衣衫、纽扣、棉被的细腻缝合,精心补缀;“走红”是公鸡在树枝上走出的一缕晨曦,“亮丽的风景线”是鸡鸣声中盆地群山峰顶渐次明媚的轮廓线。僵化干瘪、乏味泛滥的词语在故乡灵秀的山河中重获生命,作者在语言中重建纸上故乡,同时也在山野乡风的吹拂下抵达了语言的家园。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是我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
回到故乡不只是肉身的在场,更应该蜕去习惯和成见,俯身贴近大地,像最初认识这个世界一样,重新确立自己的言说方式。以写作者的敏锐穿越南阳盆地,汗漫得到了来自故乡的丰富启示。古朴的城门,像小说的开篇和定场诗;汉代石刻的简单稚拙,力透石背,寓意着写作应大度硬朗,以至简抵达真理;对玉石的探幽显微,意味着艺术品的创造是对被遮蔽事物的揭示。当所有说出口的语言都和大地上的万物相牵系连结,感知被唤醒,言辞确立了来处,那么人就可以在写作中确认自己,不再是漂泊无根的浮萍。
在广袤的历史时空中,故乡这片土地还有许多这样的言说者,曾用语言还乡,在故乡的土地上创造语言,作者有意寻访他们,跨越时空,延续故土语汇的浩荡星河。张衡的“愿言不获,终然永思”如星辰高悬在南阳的上空,指引后辈追寻自由的言辞,向着理想穷究不辍;诸葛亮为南阳卧龙岗留下了“三顾茅庐”“鞠躬尽瘁”的注脚;台湾诗人痖弦的诗歌,回荡着南阳灯歌、民间谣曲的咿呀长调;何南丁的作品中有小水村的沉静悲悯,乔典运的小说散发着中原草木的葳蕤光线。作者思接千载,沿着故乡的文明漫溯,从个人还乡思考民族的还乡,一代代文人墨客在纸上重建故乡,汇集成汉语文明,古人曾在空无中创造新言辞,而今人却使用着庸俗泛滥的只言片语,丧失了敏锐的感知力。可见作者的返乡不是背对当下,而饱含着现实忧思,从言语的匮乏、机械,揭示当下人感受力的丧失和与故乡大地的隔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丧失田园、远离草木,在纷繁空洞语词包裹下的当代人,无论身居何处,都是面目混沌的“异乡人”。
因而作者反复重申写作对于“重建”的意义,在纸上还乡,即是采撷故乡大地上的灯火缔造诗性灵动的新语言,在语言中游走历史的苍茫,传诵麦浪的低语,画下河川细腻的波纹,回溯家族的生死绵延。故乡与写作双向赋能,对故乡的言说恢复了语言的质地,而语言像灯盏,照亮沉默的故乡。
汗漫的故乡书写不满足于游子对土地的深情告白,而以一个诗人的自觉,连通故乡之上历代写作者,在故乡历史与自我生命的交界处,创造言说故乡、确立自我的新言辞,收复生命的纯真与诗意,力图“让他乡异代的人,在阅读中遭逢自我和当下”。合上书卷,凝神谛听心中荡漾的故乡情思,我想,作者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