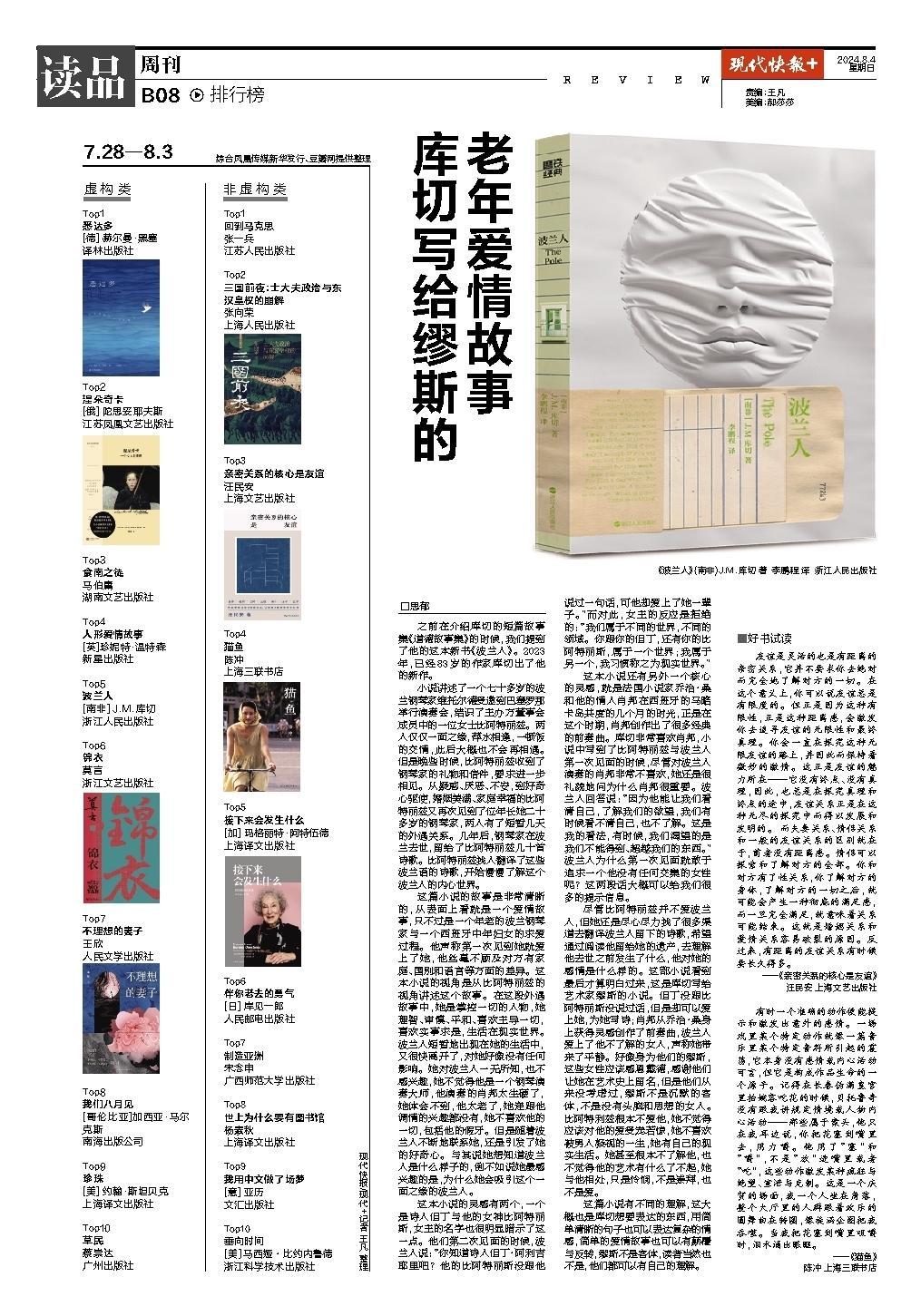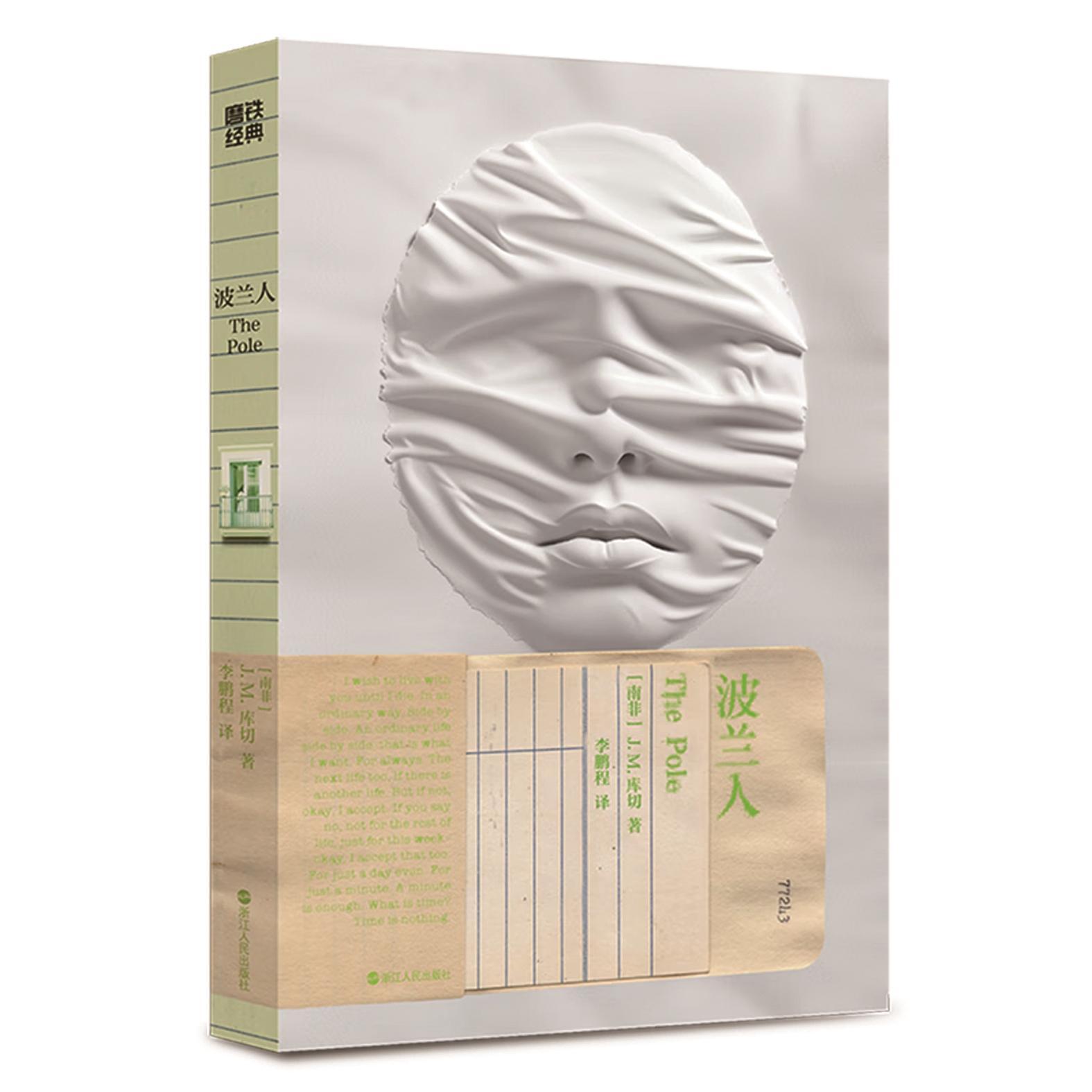□思郁
之前在介绍库切的短篇故事集《道德故事集》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他的这本新书《波兰人》。2023年,已经83岁的作家库切出了他的新作。
小说讲述了一个七十多岁的波兰钢琴家维托尔德受邀到巴塞罗那举行演奏会,结识了主办方董事会成员中的一位女士比阿特丽兹。两人仅仅一面之缘,萍水相逢,一顿饭的交情,此后大概也不会再相遇。但是晚些时候,比阿特丽兹收到了钢琴家的礼物和信件,要求进一步相见。从疑惑、厌恶、不安,到好奇心驱使,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的比阿特丽兹又再次见到了位年长她二十多岁的钢琴家,两人有了短暂几天的外遇关系。几年后,钢琴家在波兰去世,留给了比阿特丽兹几十首诗歌。比阿特丽兹找人翻译了这些波兰语的诗歌,开始慢慢了解这个波兰人的内心世界。
这篇小说的故事是非常清晰的,从表面上看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只不过是一个年老的波兰钢琴家与一个西班牙中年妇女的求爱过程。他声称第一次见到她就爱上了她,他丝毫不顾及对方有家庭、国别和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这本小说的视角是从比阿特丽兹的视角讲述这个故事。在这段外遇故事中,她是掌控一切的人物,她理智、审慎、平和、喜欢主导一切,喜欢实事求是,生活在现实世界。波兰人短暂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又很快离开了,对她好像没有任何影响。她对波兰人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她不觉得他是一个钢琴演奏大师,他演奏的肖邦太生硬了,她体会不到,他太老了,她连跟他调情的兴趣都没有,她不喜欢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假牙。但是随着波兰人不断地联系她,还是引发了她的好奇心。与其说她想知道波兰人是什么样子的,倒不如说她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她会吸引这个一面之缘的波兰人。
这本小说的灵感有两个,一个是诗人但丁与他的女神比阿特丽斯,女主的名字也很明显暗示了这一点。他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波兰人说:“你知道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吧?他的比阿特丽斯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可他却爱上了她一辈子。”而对此,女主的反应是拒绝的:“我们属于不同的世界,不同的领域。你跟你的但丁,还有你的比阿特丽斯,属于一个世界;我属于另一个,我习惯称之为现实世界。”
这本小说还有另外一个核心的灵感,就是法国小说家乔治·桑和他的情人肖邦在西班牙的马略卡岛共度的几个月的时光,正是在这个时期,肖邦创作出了很多经典的前奏曲。库切非常喜欢肖邦,小说中写到了比阿特丽兹与波兰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尽管对波兰人演奏的肖邦非常不喜欢,她还是很礼貌地问为什么肖邦很重要。波兰人回答说:“因为他能让我们看清自己,了解我们的欲望,我们有时候看不清自己,也不了解。这是我的看法,有时候,我们渴望的是我们不能得到、超越我们的东西。”波兰人为什么第一次见面就敢于追求一个他没有任何交集的女性呢?这两段话大概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示信息。
尽管比阿特丽兹并不爱波兰人,但她还是尽心尽力找了很多渠道去翻译波兰人留下的诗歌,希望通过阅读他留给她的遗产,去理解他去世之前发生了什么,他对她的感情是什么样的。这部小说看到最后才算明白过来,这是库切写给艺术家缪斯的小说。但丁没跟比阿特丽斯没说过话,但是却可以爱上她,为她写诗;肖邦从乔治·桑身上获得灵感创作了前奏曲,波兰人爱上了他不了解的女人,声称她带来了平静。好像身为他们的缪斯,这些女性应该感恩戴德,感谢他们让她在艺术史上留名,但是他们从来没考虑过,缪斯不是沉默的客体,不是没有头脑和思想的女人。比阿特利兹根本不爱他,她不觉得应该对他的爱受宠若惊,她不喜欢被男人凝视的一生,她有自己的现实生活。她甚至根本不了解他,也不觉得他的艺术有什么了不起,她与他相处,只是怜悯,不是崇拜,也不是爱。
这篇小说有不同的理解,这大概也是库切想要表达的东西,用简单清晰的句子也可以表达复杂的情感,简单的爱情故事也可以有颠覆与反转,缪斯不是客体,读者当然也不是,他们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好书试读
友谊是灵活的也是有距离的亲密关系,它并不要求你去绝对而完全地了解对方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友谊总是有限度的。但正是因为这种有限性,正是这种距离感,会激发你去追寻友谊的无限性和最终真理。你会一直在探究这种无限友谊的路上,并因此而保持着微妙的激情。这正是友谊的魅力所在——它没有终点、没有真理,因此,也总是在探究真理和终点的途中,友谊关系正是在这种无尽的探究中而得以发展和发明的。 而夫妻关系、情侣关系和一般的友谊关系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没有距离感。情侣可以探索和了解对方的全部。你和对方有了性关系,你了解对方的身体,了解对方的一切之后,就可能会产生一种彻底的满足感,而一旦完全满足,就意味着关系可能结束。这就是婚姻关系和爱情关系容易破裂的原因。反过来,有距离的友谊关系有时候要长久得多。
——《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
汪民安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有时一个准确的动作便能提示和激发出意外的感情。一场戏里某个特定动作就像一篇音乐里某个特定音符所引起的震荡,它本身没有感情或内心活动可言,但它是构成作品生命的一个原子。记得在长春伪满皇宫里拍婉容吃花的时候,贝托鲁奇没有跟我讲规定情境或人物内心活动——那些属于案头,他只在我耳边说,你把花塞到嘴里去,用力嚼。他用了“塞”和“嚼”,不是“放”进嘴里或者“吃”,这些动作激发某种疯狂与绝望、宣泄与克制。这是一个庆贺的场面,我一个人坐在角落,整个大厅里的人群跟着欢乐的圆舞曲在转圈,像旋涡企图把我吞噬。当我把花塞到嘴里咀嚼时,泪水涌出眼眶。
——《猫鱼》
陈冲 上海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