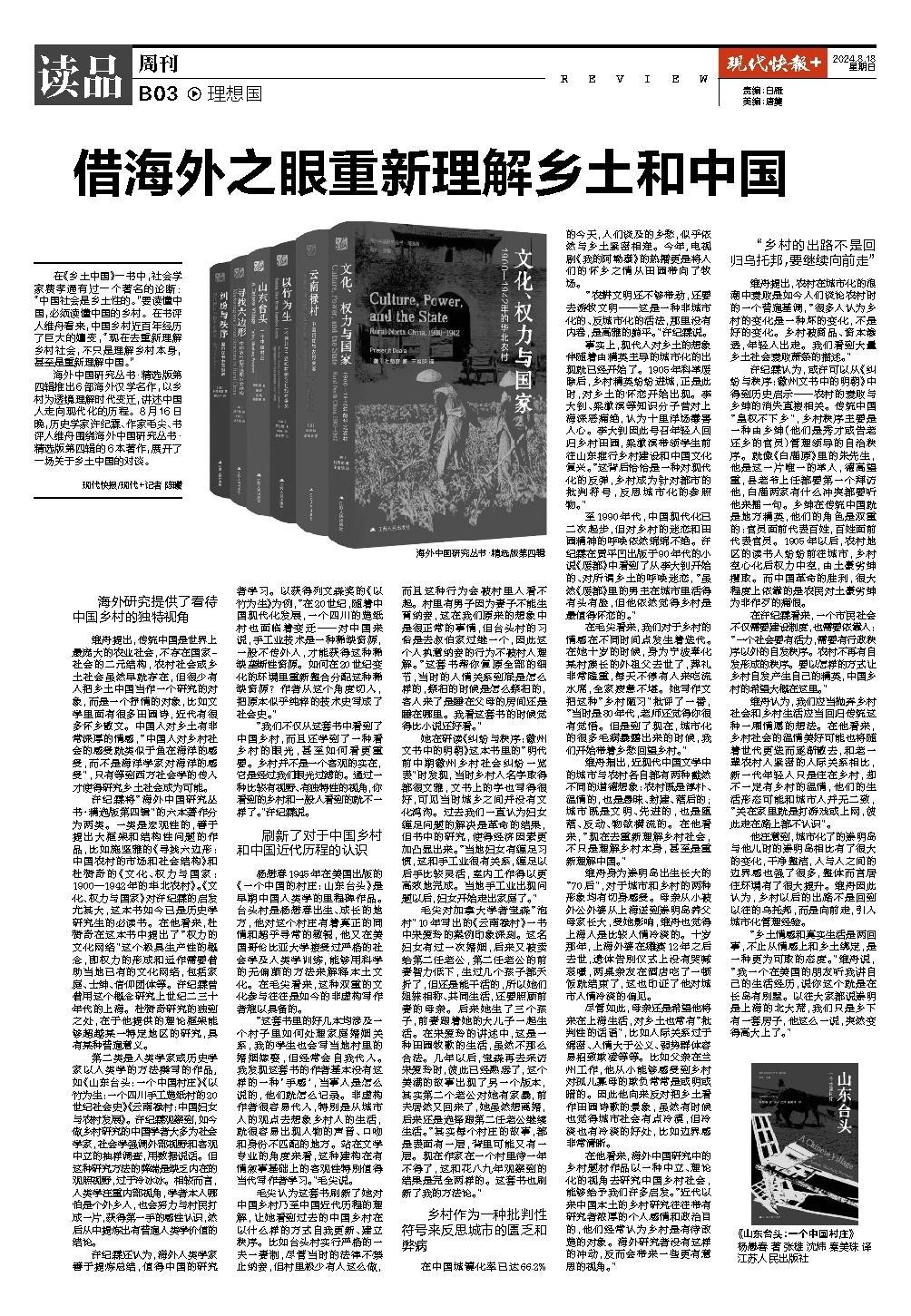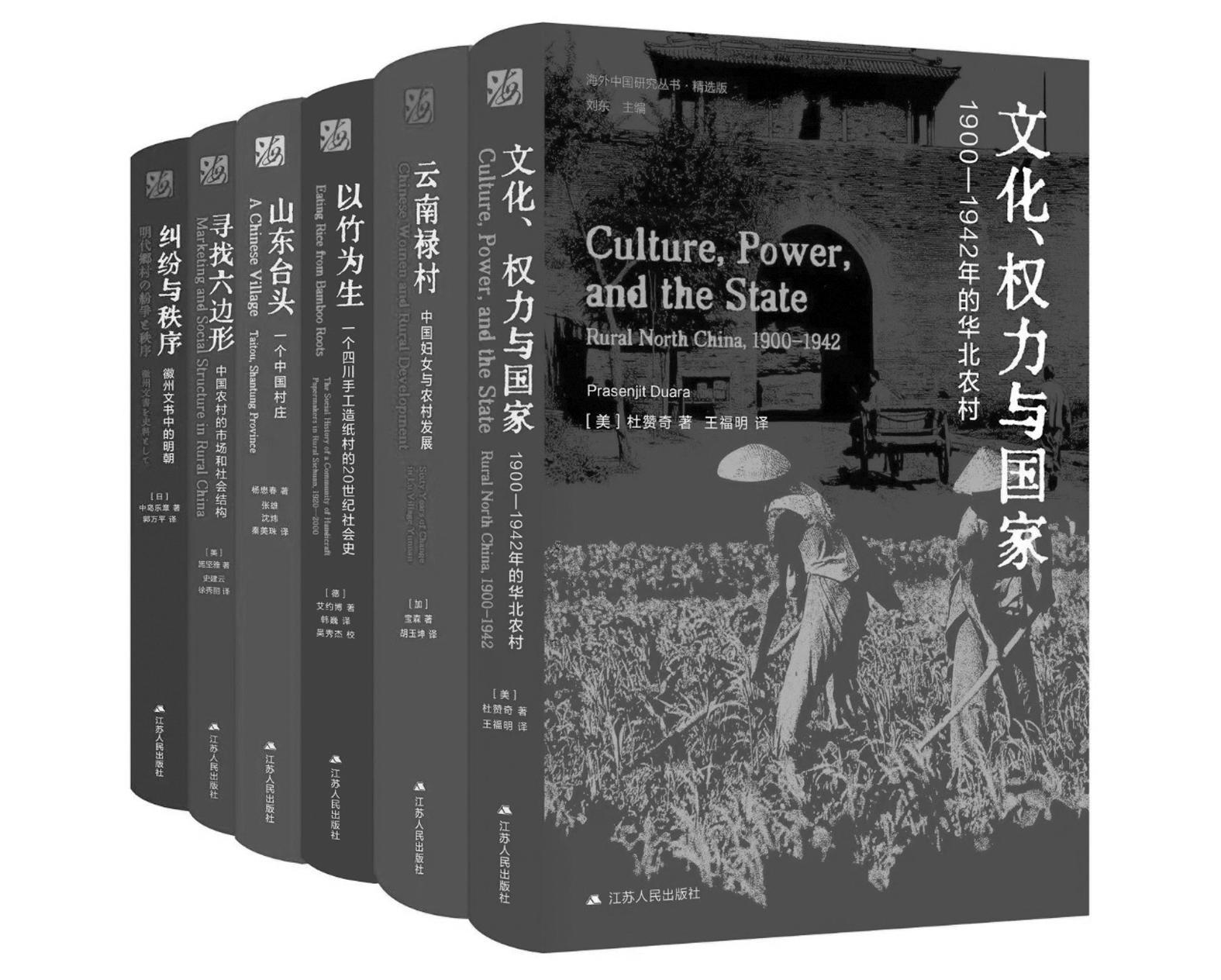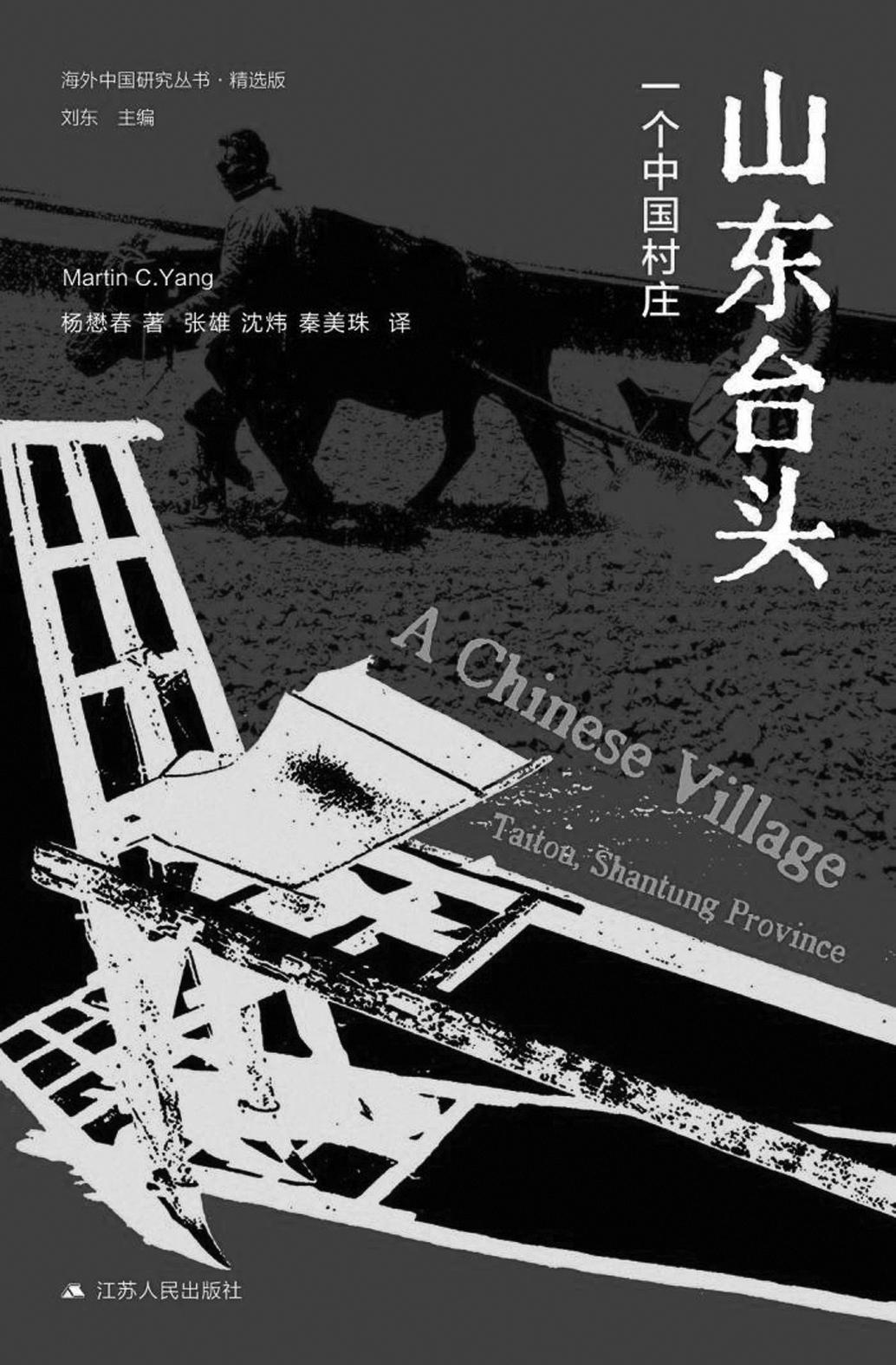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社会学家费孝通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要读懂中国,必须读懂中国的乡村。在书评人维舟看来,中国乡村近百年经历了巨大的嬗变,“现在去重新理解乡村社会,不只是理解乡村本身,甚至是重新理解中国。”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选版第四辑推出6部海外汉学名作,以乡村为透镜理解时代变迁,讲述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历程。8月16日晚,历史学家许纪霖、作家毛尖、书评人维舟围绕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选版第四辑的6本著作,展开了一场关于乡土中国的对谈。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海外研究提供了看待中国乡村的独特视角
维舟提出,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农业社会,不存在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农村社会或乡土社会虽然早就存在,但很少有人把乡土中国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而是一个抒情的对象,比如文学里面有很多田园诗,近代有很多怀乡散文。中国人对乡土有非常深厚的情感,“中国人对乡村社会的感受就类似于鱼在海洋的感受,而不是海洋学家对海洋的感受”,只有等到西方社会学的传入才使得研究乡土社会成为可能。
许纪霖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选版第四辑”的六本著作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性的,善于提出大框架和结构性问题的作品,比如施坚雅的《寻找六边形: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和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文化、权力与国家》对许纪霖的启发尤其大,这本书如今已是历史学研究生的必读书。在他看来,杜赞奇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极具生产性的概念,即权力的形成和运作需要借助当地已有的文化网络,包括家庭、士绅、信仰团体等。许纪霖曾借用这个概念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杜赞奇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提供的理论框架能够超越某一特定地区的研究,具有某种普遍意义。
第二类是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以人类学的方法撰写的作品,如《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云南禄村: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许纪霖观察到,如今做乡村研究的中国学者大多为社会学家,社会学强调外部视野和客观中立的抽样调查,用数据说话。但这种研究方法的弊端是缺乏内在的观照视野,过于冷冰冰。相较而言,人类学注重内部视角,学者本人哪怕是个外乡人,也会努力与村民打成一片,获得第一手的感性认识,然后从中提炼出有普遍人类学价值的结论。
许纪霖还认为,海外人类学家善于提炼总结,值得中国的研究者学习。以获得列文森奖的《以竹为生》为例,“在20世纪,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一个四川的造纸村也面临着变迁——对中国来说,手工业技术是一种稀缺资源,一般不传外人,才能获得这种稀缺垄断性资源。如何在20世纪变化的环境里重新整合分配这种稀缺资源?作者从这个角度切入,把原本似乎纯粹的技术史写成了社会史。”
“我们不仅从这套书中看到了中国乡村,而且还学到了一种看乡村的眼光,甚至如何看更重要。乡村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实在,它是经过我们眼光过滤的。通过一种比较有视野、有独特性的视角,你看到的乡村和一般人看到的就不一样了。”许纪霖说。
刷新了对于中国乡村和中国近代历程的认识
杨懋春1945年在美国出版的《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是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里程碑作品。台头村是杨懋春出生、成长的地方,他对这个村庄有着真正的同情和超乎寻常的敏锐,他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严格的社会学及人类学训练,能够用科学的无偏颇的方法来解释本土文化。在毛尖看来,这种双重的文化参与往往是如今的非虚构写作者难以具备的。
“这套书里的好几本均涉及一个村子里如何处理家庭婚姻关系,我的学生也会写当地村里的婚姻嫁娶,但经常会自我代入。我发现这套书的作者基本没有这样的一种‘手感’,当事人是怎么说的,他们就怎么记录。非虚构作者很容易代入,特别是从城市人的观点去想象乡村人的生活,就很容易出现人物的声音、口吻和身份不匹配的地方。站在文学专业的角度来看,这种建构在有情叙事基础上的客观性特别值得当代写作者学习。”毛尖说。
毛尖认为这套书刷新了她对中国乡村乃至中国近代历程的理解,让她看到过去的中国乡村在以什么样的方式自我更新、建立秩序。比如台头村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尽管当时的法律不禁止纳妾,但村里极少有人这么做,而且这种行为会被村里人看不起。村里有男子因为妻子不能生育纳妾,这在我们原来的想象中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台头村的习俗是去叔伯家过继一个,因此这个人执意纳妾的行为不被村人理解。“这套书帮你复原全部的细节,当时的人情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祭祀的时候是怎么祭祀的,客人来了是睡在父母的房间还是睡在哪里。我看这套书的时候觉得比小说还好看。”
她在研读《纠纷与秩序:徽州文书中的明朝》这本书里的“明代前中期徽州乡村社会纠纷一览表”时发现,当时乡村人名字取得都很文雅,文书上的字也写得很好,可见当时城乡之间并没有文化鸿沟。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妇女缠足问题的解决是革命的结果,但书中的研究,使得经济因素更加凸显出来。“当地妇女有缠足习惯,这和手工业很有关系,缠足以后手比较灵活,室内工作得以更高效地完成。当地手工业出现问题以后,妇女开始走出家庭了。”
毛尖对加拿大学者宝森“泡村”10年写出的《云南禄村》一书中宋爱玲的案例印象深刻。这名妇女有过一次婚姻,后来又被卖给第二任老公,第二任老公的前妻智力低下,生过几个孩子都夭折了,但还是能干活的,所以她们姐妹相称、共同生活,还要照顾前妻的母亲。后来她生了三个孩子,前妻跟着她的大儿子一起生活。在宋爱玲的讲述中,这是一种田园牧歌的生活,虽然不那么合法。几年以后,宝森再去采访宋爱玲时,彼此已经熟悉了,这个美满的故事出现了另一个版本,其实第二个老公对她有家暴,前夫居然又回来了,她虽然想离婚,后来还是选择跟第二任老公继续生活。“其实每个村庄的故事,都是表面有一层,背里可能又有一层。现在作家在一个村里待一年不得了,这和花八九年观察到的结果是完全两样的。这套书也刷新了我的方法论。”
乡村作为一种批判性符号来反思城市的匮乏和弊病
在中国城镇化率已达66.2%的今天,人们谈及的乡愁,似乎依然与乡土紧密相连。今年,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更是将人们的怀乡之情从田园带向了牧场。
“农耕文明还不够带劲,还要去游牧文明——这是一种非城市化的、反城市化的活法,那里没有内卷,是高雅的躺平。”许纪霖说。
事实上,现代人对乡土的想象伴随着由精英主导的城市化的出现就已经开始了。1905年科举废除后,乡村精英纷纷进城,正是此时,对乡土的怀恋开始出现。李大钊、梁漱溟等知识分子曾对上海深恶痛绝,认为十里洋场毒害人心。李大钊因此号召年轻人回归乡村田园,梁漱溟带领学生前往山东推行乡村建设和中国文化复兴。“这背后恰恰是一种对现代化的反弹,乡村成为针对都市的批判符号,反思城市化的参照物。”
至1990年代,中国现代化已二次起步,但对乡村的迷恋和田园精神的呼唤依然绵绵不绝。许纪霖在贾平凹出版于90年代的小说《废都》中看到了从李大钊开始的、对所谓乡土的呼唤迷恋,“虽然《废都》里的男主在城市里活得有头有脸,但他依然觉得乡村是最值得怀恋的。”
在毛尖看来,我们对于乡村的情感在不同时间点发生着迭代。在她十岁的时候,身为宁波奉化某村族长的外祖父去世了,葬礼非常隆重,每天不停有人来吃流水席,全家疲惫不堪。她写作文把这种“乡村陋习”批评了一番,“当时是80年代,老师还觉得你很有觉悟。但是到了现在,城市化的很多毛病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开始带着乡愁回望乡村。”
维舟指出,近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城市与农村各自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想象:农村既是淳朴、温情的,也是愚昧、封建、落后的;城市既是文明、先进的,也是堕落、反动、物欲横流的。在他看来,“现在去重新理解乡村社会,不只是理解乡村本身,甚至是重新理解中国。”
维舟身为崇明岛出生长大的“70后”,对于城市和乡村的两种形象均有切身感受。母亲从小被外公外婆从上海送到崇明岛养父母家长大,受她影响,维舟也觉得上海人是比较人情冷淡的。十岁那年,上海外婆在瘫痪12年之后去世,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哭喊哀嚎,两桌亲友在酒店吃了一顿饭就结束了,这也印证了他对城市人情冷淡的偏见。
尽管如此,母亲还是希望他将来在上海生活,对乡土也常有“批判性的话语”,比如人际关系过于绵密、人情大于公义、弱势群体容易招致欺凌等等。比如父亲在兰州工作,他从小能够感受到乡村对孤儿寡母的欺负常常是或明或暗的。因此他向来反对把乡土看作田园诗歌的景象,虽然有时候也觉得城市社会有点冷漠,但冷淡也有冷淡的好处,比如边界感非常清晰。
在他看来,海外中国研究中的乡村题材作品以一种中立、理论化的视角去研究中国乡村社会,能够给予我们许多启发。“近代以来中国本土的乡村研究往往带有研究者浓厚的个人感情和政治目的,他们经常认为乡村是有待改造的对象。海外研究者没有这样的冲动,反而会带来一些更有意思的视角。”
“乡村的出路不是回归乌托邦,要继续向前走”
维舟提出,农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衰败是如今人们谈论农村时的一个普遍基调,“很多人认为乡村的变化是一种坏的变化,不是好的变化。乡村被商品、资本渗透,年轻人出走。我们看到大量乡土社会衰败萧条的描述。”
许纪霖认为,或许可以从《纠纷与秩序:徽州文书中的明朝》中得到历史启示——农村的衰败与乡绅的消失直接相关。传统中国“皇权不下乡”,乡村秩序主要是一种由乡绅(他们是秀才或告老还乡的官员)管理领导的自治秩序。就像《白鹿原》里的朱先生,他是这一片唯一的举人,德高望重,县老爷上任都要第一个拜访他,白鹿两家有什么冲突都要听他来插一句。乡绅在传统中国就是地方精英,他们的角色是双重的:官员面前代表百姓,百姓面前代表官员。1905年以后,农村地区的读书人纷纷前往城市,乡村空心化后权力中空,由土豪劣绅攫取。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农民对土豪劣绅为非作歹的痛恨。
在许纪霖看来,一个市民社会不仅需要建设制度,也需要依靠人:“一个社会要有活力,需要有行政秩序以外的自发秩序。农村不再有自发形成的秩序。要以怎样的方式让乡村自发产生自己的精英,中国乡村的希望大概在这里。”
维舟认为,我们应当抛弃乡村社会和乡村生活应当回归传统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他看来,乡村社会的温情美好可能也将随着世代更迭而逐渐散去,和老一辈农村人紧密的人际关系相比,新一代年轻人只是住在乡村,却不一定有乡村的温情,他们的生活形态可能和城市人并无二致,“关在家里就是打游戏或上网,彼此走在路上都不认识”。
他注意到,城市化了的崇明岛与他儿时的崇明岛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干净整洁,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也强了很多,整体而言居住环境有了很大提升。维舟因此认为,乡村以后的出路不是回到以往的乌托邦,而是向前走,引入城市化管理经验。
“乡土情感和真实生活是两回事,不止从情感上和乡土绑定,是一种更为可取的态度。”维舟说,“我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听我讲自己的生活经历,说你这个就是在长岛有别墅。以往大家都说崇明是上海的北大荒,我们只是乡下有一套房子,他这么一说,突然变得高大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