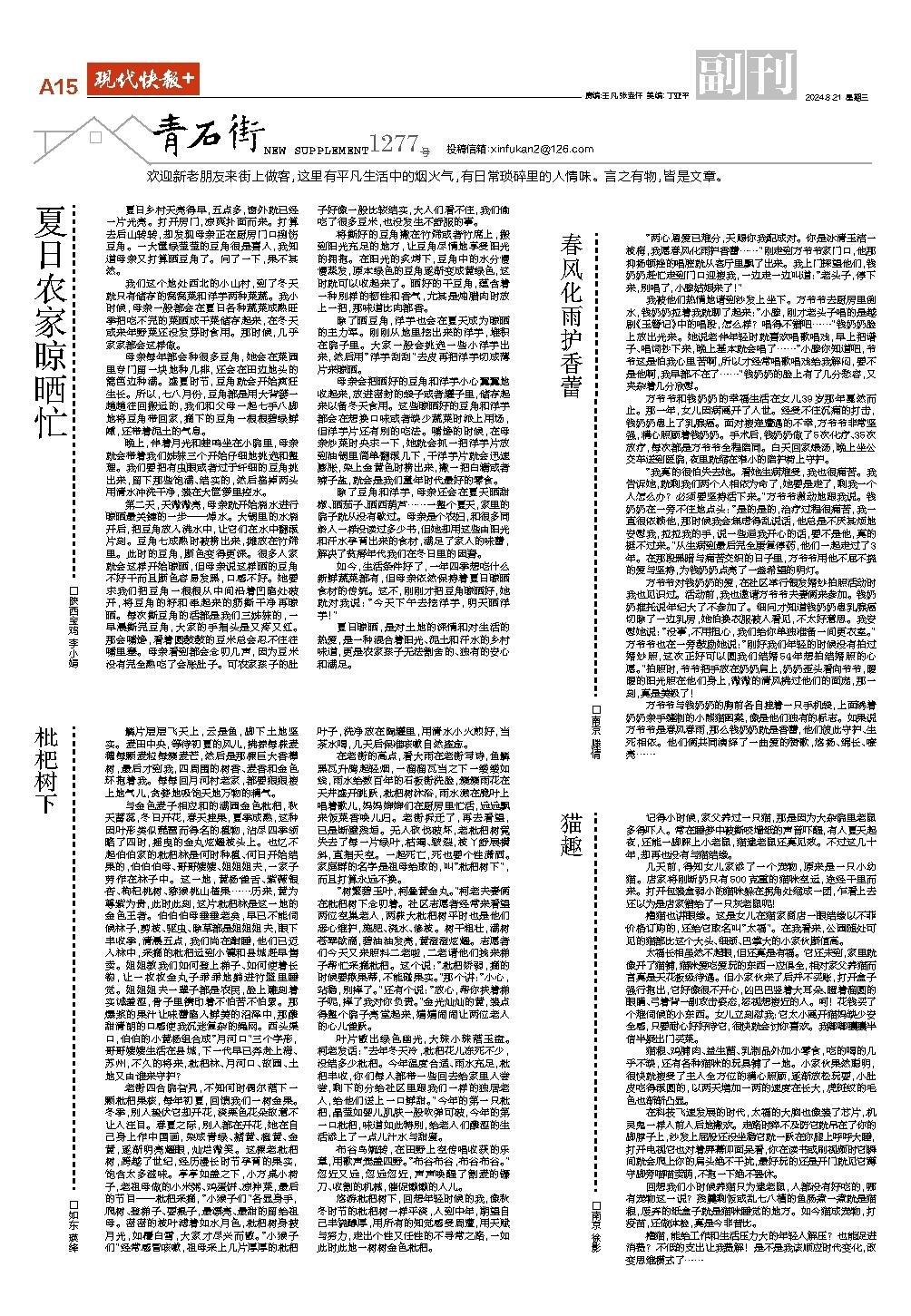□如东 瑛绛
鳞片层层飞天上,云是鱼,脚下土地坚实。麦田中央,等待初夏的风儿,拂掠每株麦穗每颗麦粒每簇麦芒,然后是那棵巨大香樟树,最后才到我,四周围的树香、麦香和金色环抱着我。每每回月河村老家,都要狠狠接上地气儿,贪婪地吸饱天地万物的精气。
与金色麦子相应和的满园金色枇杷,秋天蓄蕊,冬日开花,春天挂果,夏季成熟,这种因叶形类似琵琶而得名的植物,沾尽四季领略了四时,摇曳的金丸炫耀枝头上。也忆不起伯伯家的枇杷林是何时种植、何日开始结果的,伯伯伯母、哥哥嫂嫂、姐姐姐夫,一家子劳作在林子中。这一地,黄杨雀舌、紫薇银杏、枸杞桃树、猕猴桃山楂果……历来,黄为尊紫为贵,此时此刻,这片枇杷林是这一地的金色王者。伯伯伯母垂垂老矣,早已不能伺候林子,剪枝、驱虫、除草都是姐姐姐夫,眼下丰收季,清晨五点,我们尚在酣睡,他们已迈入林中,采摘的枇杷运到小镇和县城赶早售卖。姐姐教我们如何登上梯子、如何使着长钩,让一枚枚金丸子乖乖地躺进竹篮里睡觉。姐姐姐夫一辈子都是农民,脸上雕刻着实诚羞涩,骨子里镌印着不怕苦不怕累。那爆浆的果汁让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那酸甜清朗的口感使我沉迷复杂的绳网。西头渠口,伯伯的小黄杨组合成“月河口”三个字形,哥哥嫂嫂生活在县城,下一代早已奔赴上海、苏州,不久的将来,枇杷林、月河口、故园、土地又由谁来守护?
老街四合院旮旯,不知何时偶尔落下一颗枇杷果核,每年初夏,回馈我们一树金果。冬季,别人蛰伏它却开花,淡栗色花朵故意不让人注目。春夏之际,别人都在开花,她在自己身上作中国画,染成青绿、赭黄、橙黄、金黄,逐渐明亮耀眼,灿烂微笑。这棵老枇杷树,跨越了世纪,经历漫长时节孕育的果实,饱含太多滋味。亭亭如盖之下,小方桌小椅子,老祖母做的小米粥、鸡蛋饼、凉拌菜,最后的节目——枇杷采摘,“小猴子们”各显身手,爬树、登梯子、耍棍子,最漂亮、最甜的留给祖母。密密的枝叶滤着如水月色,枇杷树身披月光,如覆白雪,大家才尽兴而散。“小猴子们”经常感冒咳嗽,祖母采上几片厚厚的枇杷叶子,洗净放在陶罐里,用清水小火煎好,当茶水喝,几天后保准咳嗽自然痊愈。
在老街的高点,看大雨在老街写诗,鱼鳞黑瓦升腾起轻烟,一溜溜瓦当之下一缕缕如线,雨水给数百年的石板街洗脸,簇簇雨花在天井盛开跳跃,枇杷树沐浴,雨水溅在脆叶上唱着歌儿,妈妈婶婶们在厨房里忙活,远远飘来饭菜香唤儿归。老街拆迁了,再去看望,已是断壁残垣。无人砍伐破坏,老枇杷树竟失去了每一片绿叶,枯竭、皲裂,枝丫舒展横斜,直指天空。一起死亡,死也要个性潇洒。家庭群的名字是祖母给取的,叫“枇杷树下”,而且打算永远不换。
“树繁碧玉叶,柯叠黄金丸。”柯老夫妻俩在枇杷树下念叨着。社区志愿者经常来看望两位空巢老人,两株大枇杷树平时也是他们悉心维护,施肥、浇水、修枝。树干粗壮,满树苍翠欲滴,碧油油发亮,黄澄澄炫耀。志愿者们今天又来照料二老啦,二老请他们找来梯子帮忙采摘枇杷。这个说:“枇杷娇弱,摘的时候要揪果蒂,不能碰果实。”那个讲:“小心,站稳,别摔了。”还有个说:“放心,帮你扶着梯子呢,摔了我对你负责。”金光灿灿的黄,装点得整个院子亮堂起来,嬉嬉闹闹让两位老人的心儿雀跃。
叶片散出绿色幽光,大珠小珠落玉盘。柯老发话:“去年冬天冷,枇杷花儿冻死不少,没结多少枇杷。今年温度合适、雨水充足,枇杷丰收,你们每人都带一些回去给家里人尝尝,剩下的分给社区里跟我们一样的独居老人,给他们送上一口鲜甜。”今年的第一只枇杷,晶莹如婴儿肌肤一般吹弹可破,今年的第一口枇杷,味道如此特别,给老人们酸涩的生活添上了一点儿汁水与甜蜜。
布谷鸟婉转,在田野上空传唱收获的乐章,用歌声笼盖四野。“布谷布谷,布谷布谷。”忽近又远,忽远忽近,声声唤醒了割麦的镰刀、收割的机械,催促懒懒的人儿。
悠游枇杷树下,回想年轻时候的我,像秋冬时节的枇杷树一样平淡,人到中年,期望自己丰饶醇厚,用所有的知觉感受周遭,用天赋与努力,走出个性又任性的不寻常之路,一如此时此地一树树金色枇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