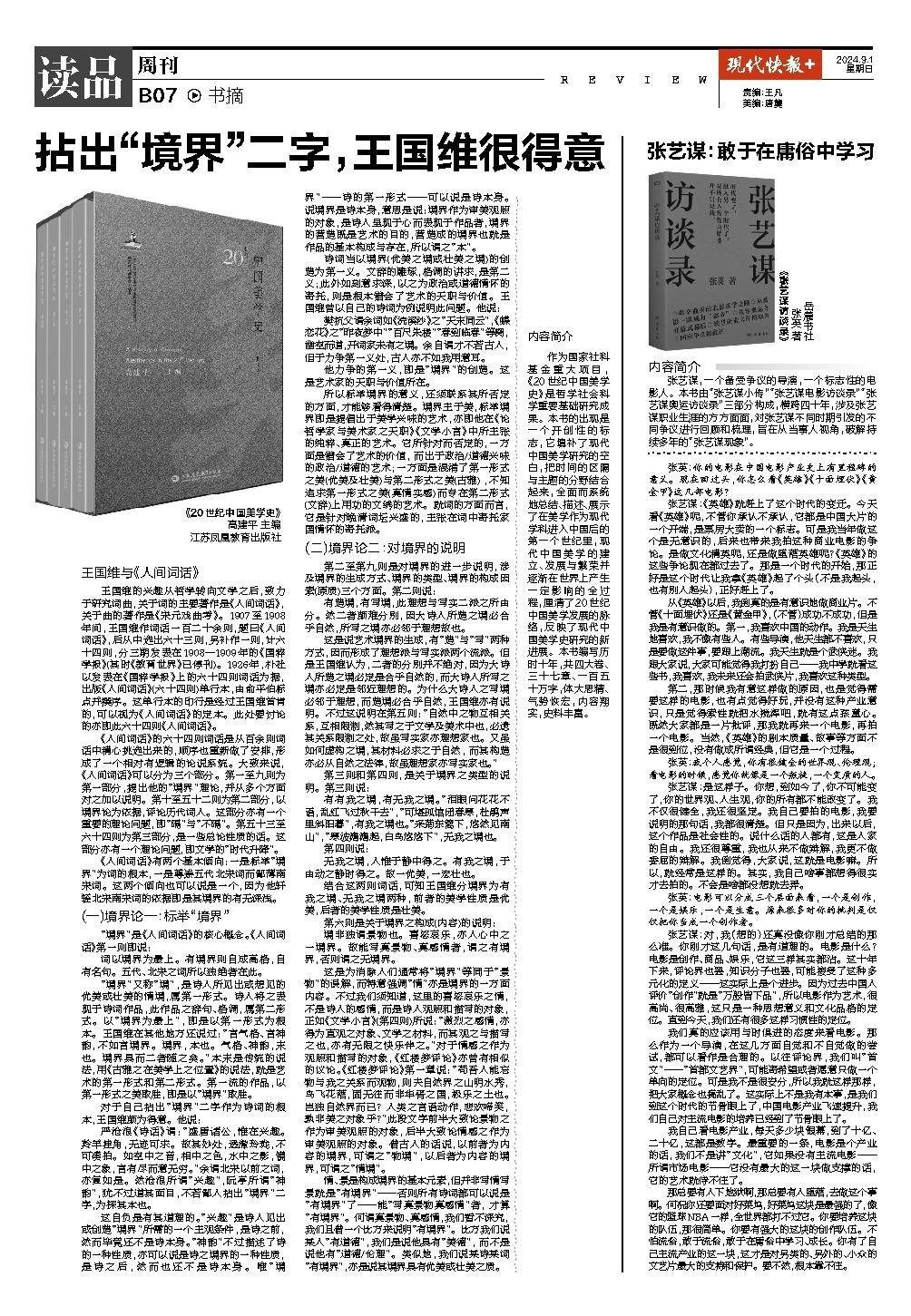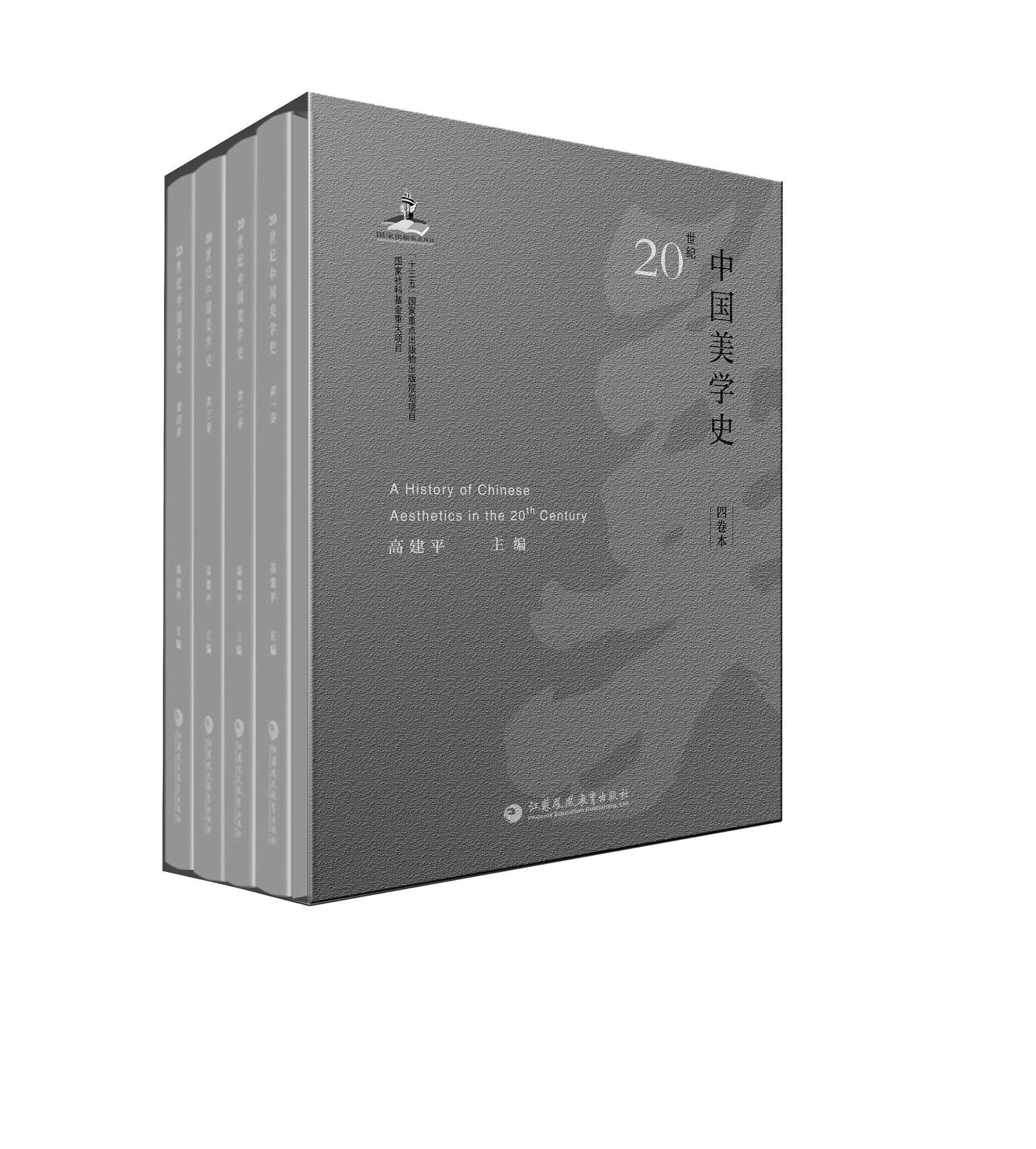王国维的兴趣从哲学转向文学之后,致力于研究词曲,关于词的主要著作是《人间词话》,关于曲的著作是《宋元戏曲考》。1907至1908年间,王国维作词话一百二十余则,题曰《人间词话》,后从中选出六十三则,另补作一则,计六十四则,分三期发表在1908—1909年的《国粹学报》(其时《教育世界》已停刊)。1926年,朴社以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六十四则词话为据,出版《人间词话》(六十四则)单行本,由俞平伯标点并撰序。这单行本的印行是经过王国维首肯的,可以视为《人间词话》的定本。此处要讨论的亦即此六十四则《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的六十四则词话是从百余则词话中精心挑选出来的,顺序也重新做了安排,形成了一个相对有逻辑的论说系统。大致来说,《人间词话》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至九则为第一部分,提出他的“境界”理论,并从多个方面对之加以说明。第十至五十二则为第二部分,以境界论为依据,评论历代词人。这部分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隔”与“不隔”。第五十三至六十四则为第三部分,是一些总论性质的话。这部分亦有一个理论问题,即文学的“时代升降”。
《人间词话》有两个基本倾向:一是标举“境界”为词的根本,一是尊崇五代北宋词而鄙薄南宋词。这两个倾向也可以说是一个,因为他轩轾北宋南宋词的依据即是其境界的有无深浅。
(一)境界论一:标举“境界”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概念。《人间词话》第一则即说: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境界”又称“境”,是诗人所见出或想见的优美或壮美的情境,属第一形式。诗人将之表现于诗词作品,此作品之辞句、格调,属第二形式。以“境界为最上”,即是以第一形式为根本。王国维在其他地方还说过:“言气格、言神韵,不如言境界。境界,本也。气格、神韵,末也。境界具而二者随之矣。”本末是传统的说法,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的说法,就是艺术的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第一流的作品,以第一形式之美取胜,即是以“境界”取胜。
对于自己拈出“境界”二字作为诗词的根本,王国维颇为得意。他说:
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这自负是有其道理的。“兴趣”是诗人见出或创造“境界”所需的一个主观条件,是诗之前,然而毕竟还不是诗本身。“神韵”不过描述了诗的一种性质,亦可以说是诗之境界的一种性质,是诗之后,然而也还不是诗本身。唯“境界”——诗的第一形式——可以说是诗本身。说境界是诗本身,意思是说:境界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是诗人呈现于心而表现于作品者,境界的营造既是艺术的目的,营造成的境界也就是作品的基本构成与存在,所以谓之“本”。
诗词当以境界(优美之境或壮美之境)的创造为第一义。文辞的雕琢,格调的讲求,是第二义;此外如刻意求深,以之为政治或道德情怀的寄托,则是根本错会了艺术的天职与价值。王国维曾以自己的诗词为例说明此问题。他说:
樊抗父谓余词如《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百尺朱楼”“春到临春”等阕,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
他力争的第一义,即是“境界”的创造。这是艺术家的天职与价值所在。
所以标举境界的意义,还须联系其所否定的方面,才能够看得清楚。境界主于美,标举境界即是提倡出于美学兴味的艺术,亦即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文学小言》中所主张的纯粹、真正的艺术。它所针对而否定的,一方面是错会了艺术的价值, 而出于政治/道德兴味的政治/道德的艺术;一方面是混淆了第一形式之美(优美及壮美)与第二形式之美(古雅) ,不知追求第一形式之美(真情实感)而专在第二形式(文辞)上用功的文绣的艺术。就词的方面而言,它是针对晚清词坛兴盛的,主张在词中寄托家国情怀的寄托派。
(二)境界论二:对境界的说明
第二至第九则是对境界的进一步说明,涉及境界的生成方式、境界的类型、境界的构成因素(原质)三个方面。第二则说: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这是说艺术境界的生成,有“造”与“写”两种方式,因而形成了理想派与写实派两个流派。但是王国维认为,二者的分别并不绝对,因为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定是合乎自然的,而大诗人所写之境亦必定是邻近理想的。为什么大诗人之写境必邻于理想,而造境必合乎自然,王国维亦有说明。不过这说明在第五则:“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 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第三则和第四则,是关于境界之类型的说明。第三则说: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
第四则说: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结合这两则词话,可知王国维分境界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两种,前者的美学性质是优美,后者的美学性质是壮美。
第六则是关于境界之构成(内容)的说明: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这是为消除人们通常将“境界”等同于“景物”的误解,而特意强调“情”亦是境界的一方面内容。不过我们须知道,这里的喜怒哀乐之情,不是诗人的感情,而是诗人观照和描写的对象,正如《文学小言》(第四则)所说:“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其观之与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对于情感之作为观照和描写的对象,《红楼梦评论》亦曾有相似的议论。《红楼梦评论》第一章说:“苟吾人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秀,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岂独自然界而已?人类之言语动作,悲欢啼笑,孰非美之对象乎?”此段文字前半大致论景物之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后半大致论情感之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借古人的话说,以前者为内容的境界,可谓之“物境”,以后者为内容的境界,可谓之“情境”。
情、景是构成境界的基本元素,但并非写情写景就是“有境界”——否则所有诗词都可以说是“有境界”了——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 才算“有境界”。何谓真景物、真感情,我们暂不深究,我们且借一个比方来说明“有境界”。比方我们说某人“有道德”,我们是说他具有“美德”, 而不是说他有“道德/伦理”。类似地,我们说某诗某词“有境界”,亦是说其境界具有优美或壮美之质。
内容简介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美学史》是哲学社会科学重要基础研究成果。本书的出现是一个开创性的标志,它填补了现代中国美学研究的空白,把时间的区隔与主题的分野结合起来,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描述、展示了在美学作为现代学科进入中国后的第一个世纪里,现代中国美学的建立、发展与繁荣并逐渐在世界上产生一定影响的全过程,厘清了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脉络,反映了现代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新进展。本书编写历时十年,共四大卷、三十七章、一百五十万字,体大思精、气势恢宏,内容翔实,史料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