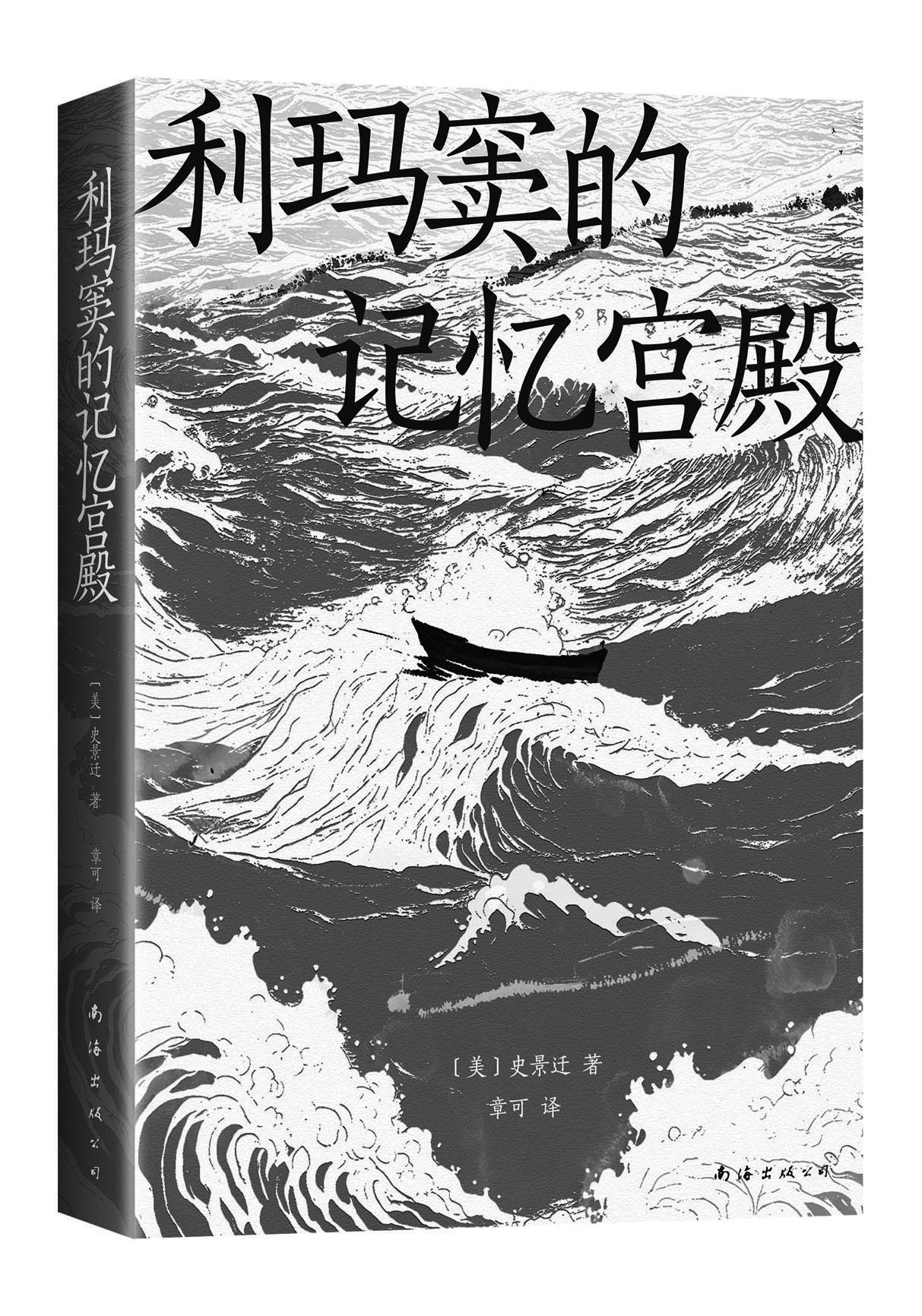1596年,利玛窦教中国人建造记忆宫殿之法。他告诉人们,这个宫殿的大小取决于他们希望记住多少东西:最宏大的构造将由几百个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建筑构成。利玛窦说,“多多益善”,但又补充道,一个人没必要上手就造一座宏伟的宫殿,他可以建一些朴实的宫室,或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建筑物,诸如一座寺观、公府、客栈,或是商人会馆。倘若此人希望从更小规模着手,则可建一个客堂、亭阁或书斋。要是他希望这个地方更私密,不妨设想为亭阁之一角、寺庙里的神龛,甚至是衣柜和座榻之类的家用物件。
利玛窦在总结这个记忆系统时说,这些宫殿、亭阁或座榻都是存留于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性建构,而非由真实的材料制成的实在物体。在脑海中构想出这些建筑的真正目的,是为数不胜数的概念提供安置之所,正是这些概念构成了人类知识的总和。利玛窦写道,对每一样我们希望记住的东西,都应给予它一个形象,并给每个形象分配一个位置,使它能安然存放,直到我们准备好“记起”它。只有这些形象都各得其所,并且我们能迅速地记起它们的位置,整个记忆体系才能运作。鉴于此,显然最简单的办法是依靠我们了熟于心的那些真实处所。然而,按利玛窦所想,这也会导致一个错误。因为我们正是通过不断增加形象以及存放形象之位置的数量,来增强我们的记忆。那么中国人将纠结于这项烦难的任务,即创造无数虚拟的场所,或者将实和虚的场所混合在一起,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复习将其永铸于记忆之中,最终使那些虚拟的场所“与实有者可无殊焉”。
中国人可能会问,这套记忆法是如何演变至今的?利玛窦早料到了这个问题,他将西方古典传统进行了总结,此传统将这种通过严格定位法来训练记忆的主张归于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
为获得向中国士人展现这种记忆法的机会,利玛窦不远万里跋涉而来。他是意大利人,1552 年出生在山城马切拉塔。1571年,利玛窦在罗马成为耶稣会的一名初学修士,随即接受了神学、人文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广泛训练。在印度和澳门度过了五年见习岁月之后,他于 1583 年进入中国,开展传教事业。到1595年,他已熟习汉语,住在东部省份江西繁华的行政和商业中心——南昌。那年年底,怀着驾驭新学语言的无比自信,利玛窦用汉字写成了《交友论》,这是一本关于友谊的格言集,采自一些西方古典作家和基督教神父。他将这本书的手抄本献给了明朝皇室的一位亲王——建安王。这位亲王居住在南昌,经常邀请利玛窦去其府邸参加酒宴。同时,利玛窦开始与当地士人讨论他的记忆理论,并传授记忆技巧。翌年,他又用汉语写成了一本探讨记忆法的小书《西国记法》,描述了他构想的“记忆宫殿”。他将这本书作为礼物赠予江西巡抚陆万陔及他的三个儿子。
对利玛窦自己而言,建造记忆宫殿并没有什么奇怪或者特别困难的地方。这套方法伴随着他成长,并和其他技巧一道,把他研习的各种学问都熔铸于记忆之中。而且,这些技能是他在罗马耶稣会学院所学的修辞和伦理课程的基本内容。
尽管有这样的说明,这套学说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仍然抽象而费解。但是,如果我们暂且离题,看一个现代的例子,或许就能拓宽视野,更好地理解利玛窦是如何通过建立这种形象和场所的联系,吸引中国人对他的记忆理论产生兴趣的。这套方法通过概念的组合或是特定的助记法则,可以在第一时间产生出人们需要的信息。
设想有一名现代大学里的医学生,她正面临着一场口试,考查的是骨骼、细胞和神经方面的知识。这名学生的头脑中有一整座记忆城市,放眼每片城区、每条大道与小巷、每幢房子,里面整齐地存放着她之前在学校习得的所有知识。然而,医科考试将至,她完全不理会那些历史、地质、诗学、化学和力学的知识区域,而把精力全部集中在“身体巷”(Body Lane)那栋三层的“生理楼”(Physiology House)。这栋楼里的各个房间存放着她每晚学习时所创造的形象,纷繁各异、生动鲜明、启人遐思,它们各居其位,分布在墙边、窗前或是桌椅床榻之上。这时摆在她面前的有三个问题:人体上肢各块骨骼的名称、细胞减数分裂的各个阶段,以及头骨的上眼窝组织的神经次序。
她的思绪首先飞到二楼楼梯口的“上身骨骼间”,那里进门的第三个位置有一名加拿大骑警,穿着亮闪闪的鲜红外套,骑着高头大马,马尾还拴着一个手戴镣铐、神情狂乱的犯人。而瞬时间,她的思绪又飘到了地下层的细胞室,壁炉边上站着一位身形魁梧、带有狰狞疤痕的非洲武士,尽管他硕大的双手紧紧抓住一位美丽非洲女郎的上臂,但他脸上却带着无可名状的厌倦表情。接着,这个女生的思绪又很快飞抵顶楼的头骨室,那里,一个艳丽的裸体女子正斜靠在床头,床罩上绘着法国国旗的条纹和色彩,女子小小的拳头里紧紧攥着一叠皱巴巴的美元钞票。
这个学生很快就有了前面三个问题的答案。皇家骑警和俘虏的形象让她想到一句话:“一些罪犯低估了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能力”(Some Criminals Have Underestimated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每个单词的首字母按次序表示人体上肢各骨骼的名称:肩胛骨(scapula)、锁骨(clavicle)、肱骨(humerus)、尺骨(ulna)、 桡 骨(radius)、 腕 骨(carpals)、 掌 骨(metacarpals)和指骨 (phalanges)。第二个形象,“倦怠的祖鲁人追捕黑人少女”(Lazy Zulu Pursuing Dark Damosels),则使她想起细胞减数分裂的各个 阶段:细线期(leptotene)、偶线期(zygotene)、粗线期(pachytene)、双线期(diplotene)和终变期(diakinesis)。最后一个形象,“慵懒的法国妓女已预先脱光衣服躺着”(Lazy French Tart Lying Naked In Anticipation),则代表着头骨的上眼窝组织的神经次序:泪腺神经(lacrimal)、前额神经(frontal)、滑车神经(trochlear)、侧面神经(lateral)、鼻睫神经(nasociliary)、内部神经(internal)和外展神经(abducens)。
一个人头脑中的记忆宫殿里已经存储了多少这样的图像?它到底总共能存储多少呢?利玛窦在1595年偶然写道,在纸上任意写下四百到五百个汉字,他只要读一遍,就能按顺序把这些汉字倒背出来,而他的中国朋友们则形容,他只要浏览一遍,就能把整卷的中国经典著作背诵出来。然而,这种特长其实并不那么令人吃惊。利玛窦同时代有一位长者帕尼加罗拉·弗朗切斯科,他可能在罗马或马切拉塔教过利玛窦记忆法,还写过一本讲记忆方法的小册子,手稿至今还保存在马切拉塔图书馆。据他在佛罗伦萨的熟人们说,帕尼加罗拉头脑中存有十万个记忆形象,每个都各就其位,任其择取。而利玛窦则根据他以前读过的记忆法的书跟陆万陔说,想让事物变得易记,最关键的是所想象的建筑物中存放形象诸场所的次序:
处所既定,爰自入门为始,循右而行,如临书然,通前达后,鱼贯鳞次,罗列胸中,以待记顿诸象也。用多,则广宇千百间,少,则一室可分方隅,要在临时斟酌,不可拘执一辙。
内容简介
明朝万历年间,也是世界史上的大航海时代,利玛窦从意大利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从介绍神秘的西方记忆法开始,传播西方文化。终其一生,他都在试图打入热衷科举考试、重视背诵诗书的士大夫群体,他披僧袍,又着儒衫,通过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来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世界。
史景迁从利玛窦留下的八个记忆碎片——四个汉字(武、要、利、好)和四幅圣经版画,搭建起这座记忆宫殿。穿梭于十六世纪晚期的世界图景中,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和史实在史景迁的笔下连缀汇集。一览两两相望的欧洲与中国,通过利玛窦的眼睛,儒家与古罗马这两个伟大的传统相互汇聚。
作者简介
史景迁(Jonathan Dermot Spence,1936年8月11日—2021年12月25日)
耶鲁大学历史系斯特林讲席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代表作:《王氏之死》《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康熙》以及《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等。曾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17)、古根海姆奖和麦克阿瑟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