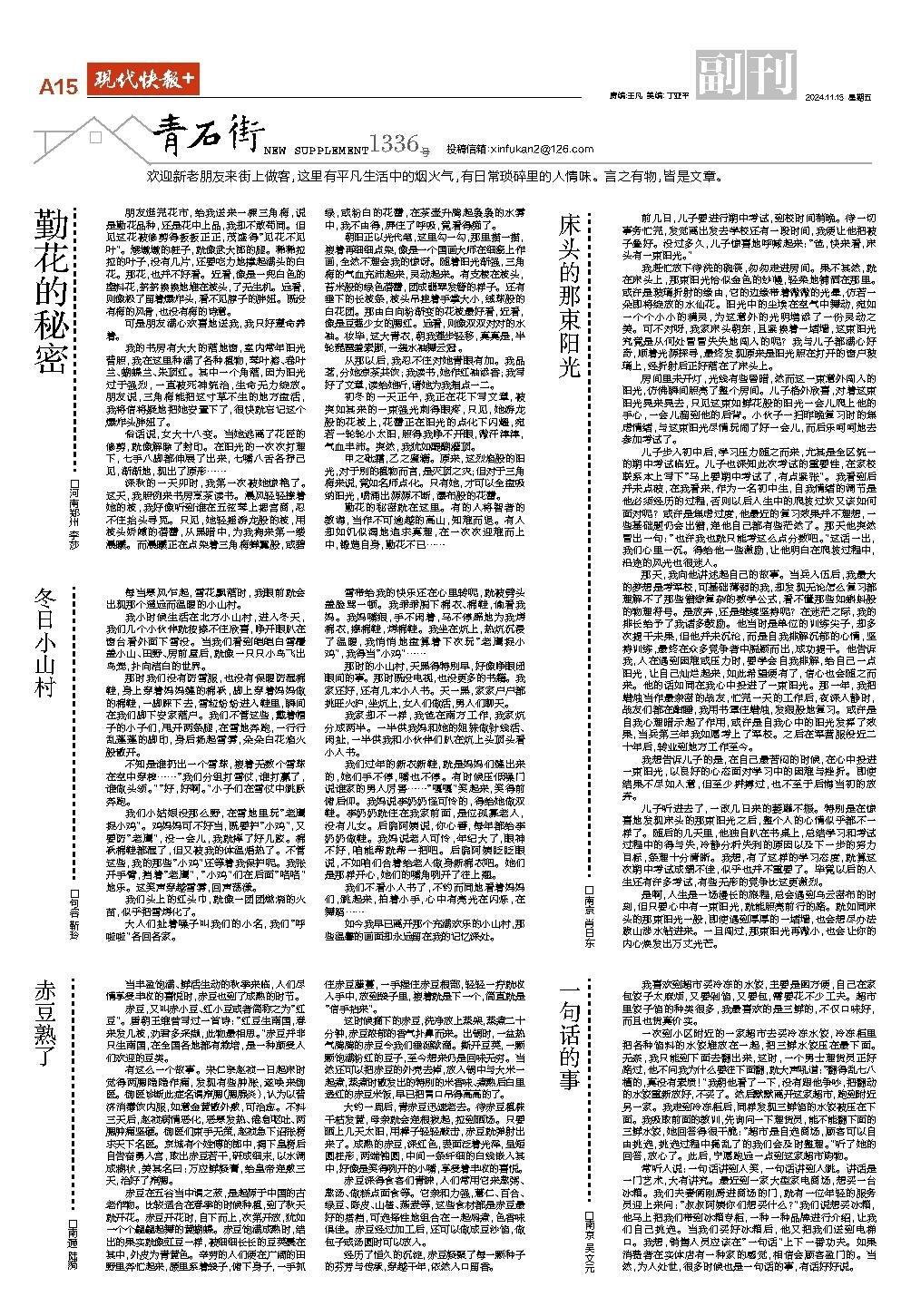□河南郑州 李莎
朋友逛完花市,给我送来一棵三角梅,说是勤花品种,还是花中上品,我却不敢苟同。但见这花被修剪得板板正正,茂盛得“见花不见叶”。矮墩墩的桩子,就像武大郎的腿。稀稀拉拉的叶子,没有几片,还要吃力地撑起满头的白花。那花,也并不好看。近看,像是一兜白色的塑料花,挤挤挨挨地堆在枝头,了无生机。远看,则像极了留着爆炸头,看不见脖子的胖妞。既没有梅的风骨,也没有梅的诗意。
可是朋友满心欢喜地送我,我只好遵命养着。
我的书房有大大的落地窗,室内常年阳光普照,我在这里种满了各种植物,琴叶榕、卷叶兰、蝴蝶兰、朱顶红。其中一个角落,因为阳光过于强烈,一直被死神统治,生命无力绽放。朋友说,三角梅能把这寸草不生的地方盘活,我将信将疑地把她安置下了,很快就忘记这个爆炸头胖妞了。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当她逃离了花匠的修剪,就像解除了封印。在阳光的一次次打理下,七手八脚都伸展了出来,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渐渐地,现出了原形……
深秋的一天卯时,我第一次被她惊艳了。这天,我照例来书房烹茶读书。晨风轻轻撩着她的枝,我好像听到谁在五弦琴上摁宫商,忍不住抬头寻觅。只见,她轻摇游龙般的枝,用枝头娇嫩的蓓蕾,从黑暗中,为我掬来第一缕晨曦。而晨曦正在点染着三角梅蝉翼般,或碧绿,或粉白的花蕾,在茶壶升腾起袅袅的水雾中,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竟看得痴了。
朝阳正以光代笔,这里勾一勾,那里描一描,接着再细细点染,像是一个国画大师在细瓷上作画,全然不理会我的惊讶。随着阳光渐强,三角梅的气血充沛起来,灵动起来。有支棱在枝头,苔米般的绿色蓓蕾,团成翡翠发簪的样子。还有垂下的长枝条,枝头吊挂着手掌大小,绒球般的白花团。那由白向粉渐变的花枝最好看,近看,像是豆蔻少女的腮红。远看,则像双双对对的水袖。妆毕,这大青衣,朝我莲步轻移,真真是,半轮琵琶羞素颜,一袭水袖舞云冠 。
从那以后,我忍不住对她青眼有加。我品茗,分她凉茶共饮;我读书,她作红袖添香;我写好了文章,读给她听,请她为我指点一二。
初冬的一天正午,我正在花下写文章,被突如其来的一束强光刺得眼疼,只见,她游龙般的花枝上,花蕾正在阳光的点化下闪耀,宛若一轮轮小太阳,照得我睁不开眼,微汗津津,气血丰沛。突然,我犹如醍醐灌顶。
甲之砒霜,乙之蜜糖。原来,这烈焰般的阳光,对于别的植物而言,是灭顶之灾;但对于三角梅来说,竟如名师点化。只有她,才可以全盘吸纳阳光,喷涌出源源不断,瀑布般的花蕾。
勤花的秘密就在这里。有的人将智者的教诲,当作不可逾越的高山,知难而退。有人却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理,在一次次迎难而上中,锻造自身,勤花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