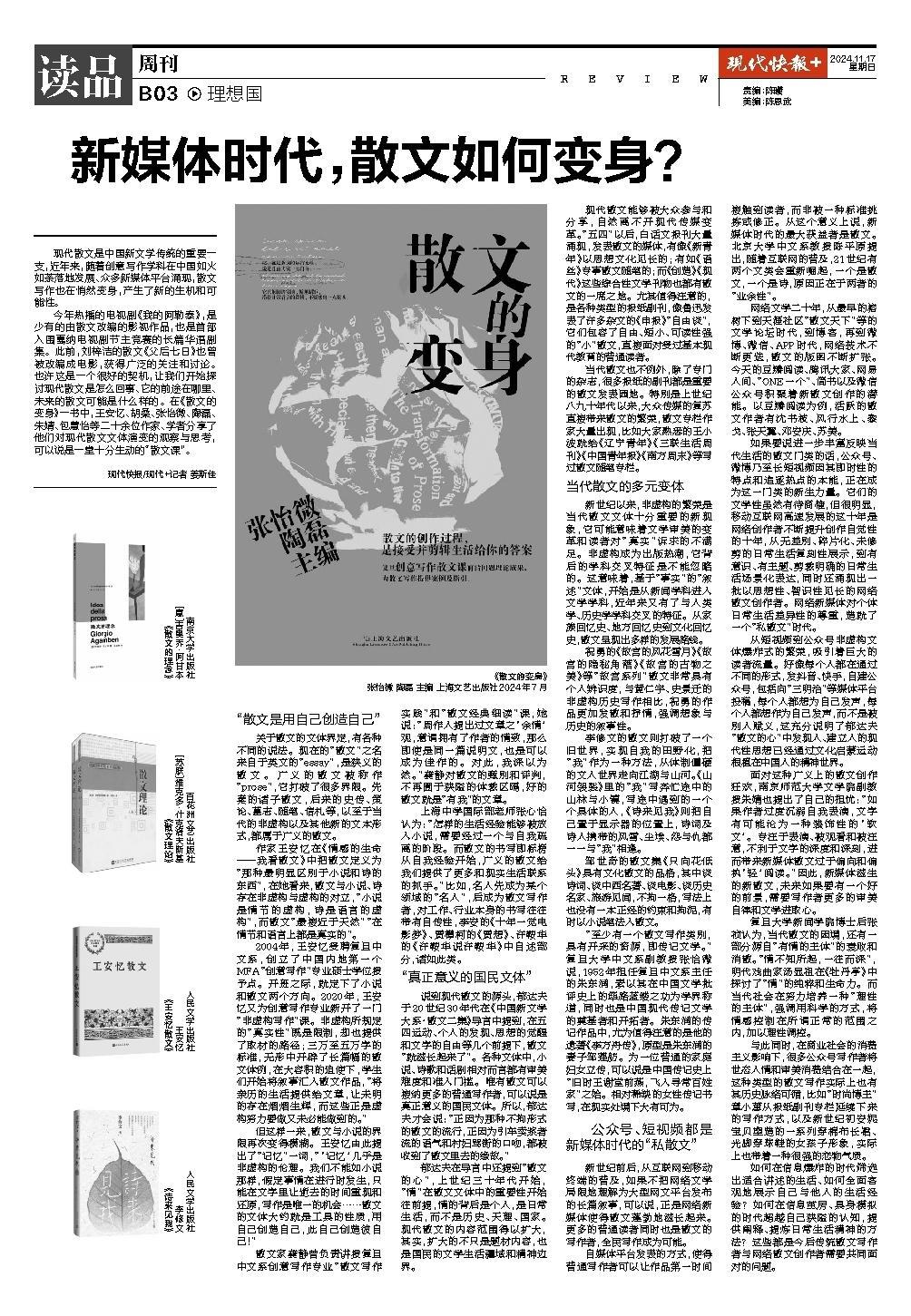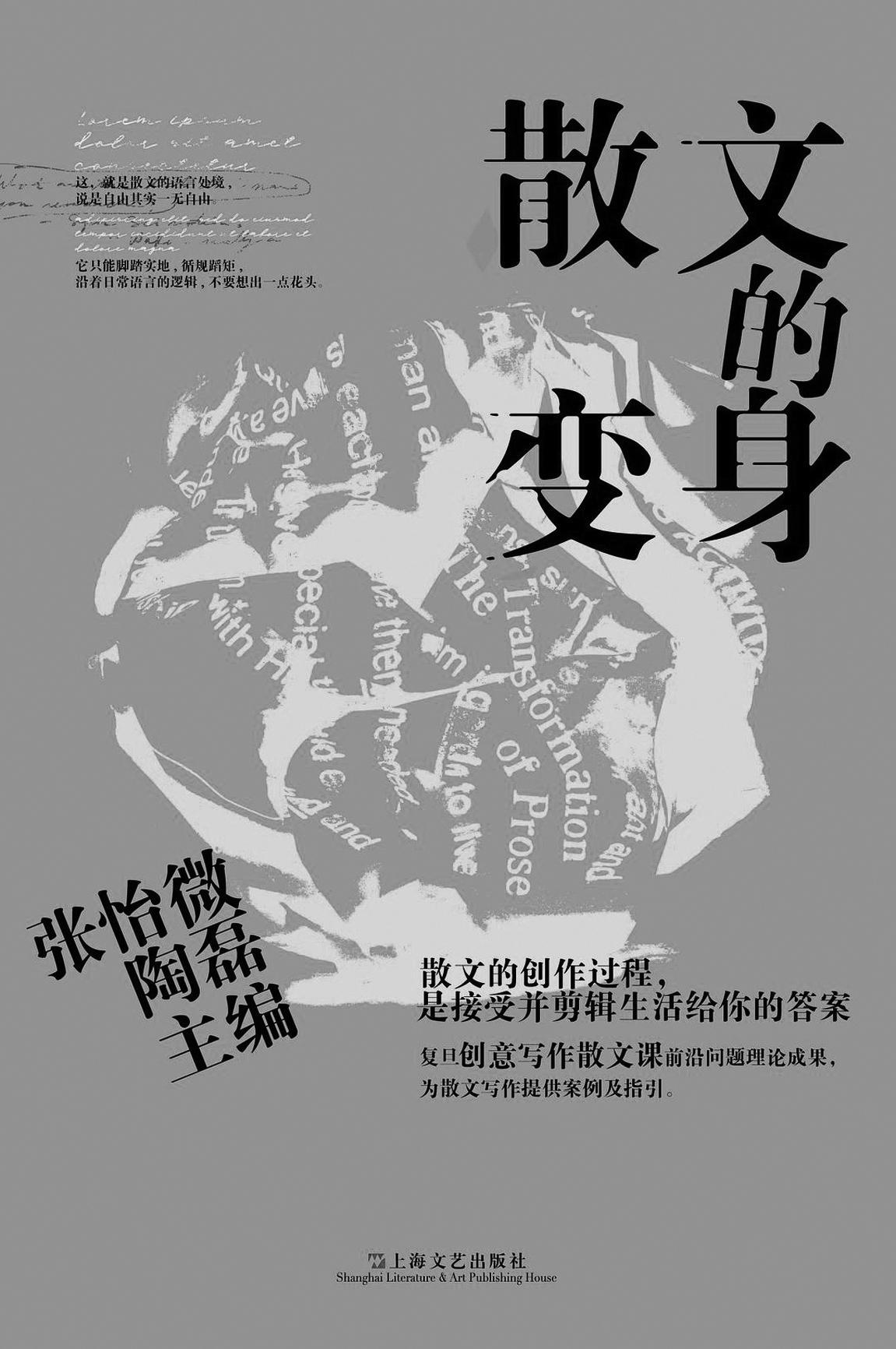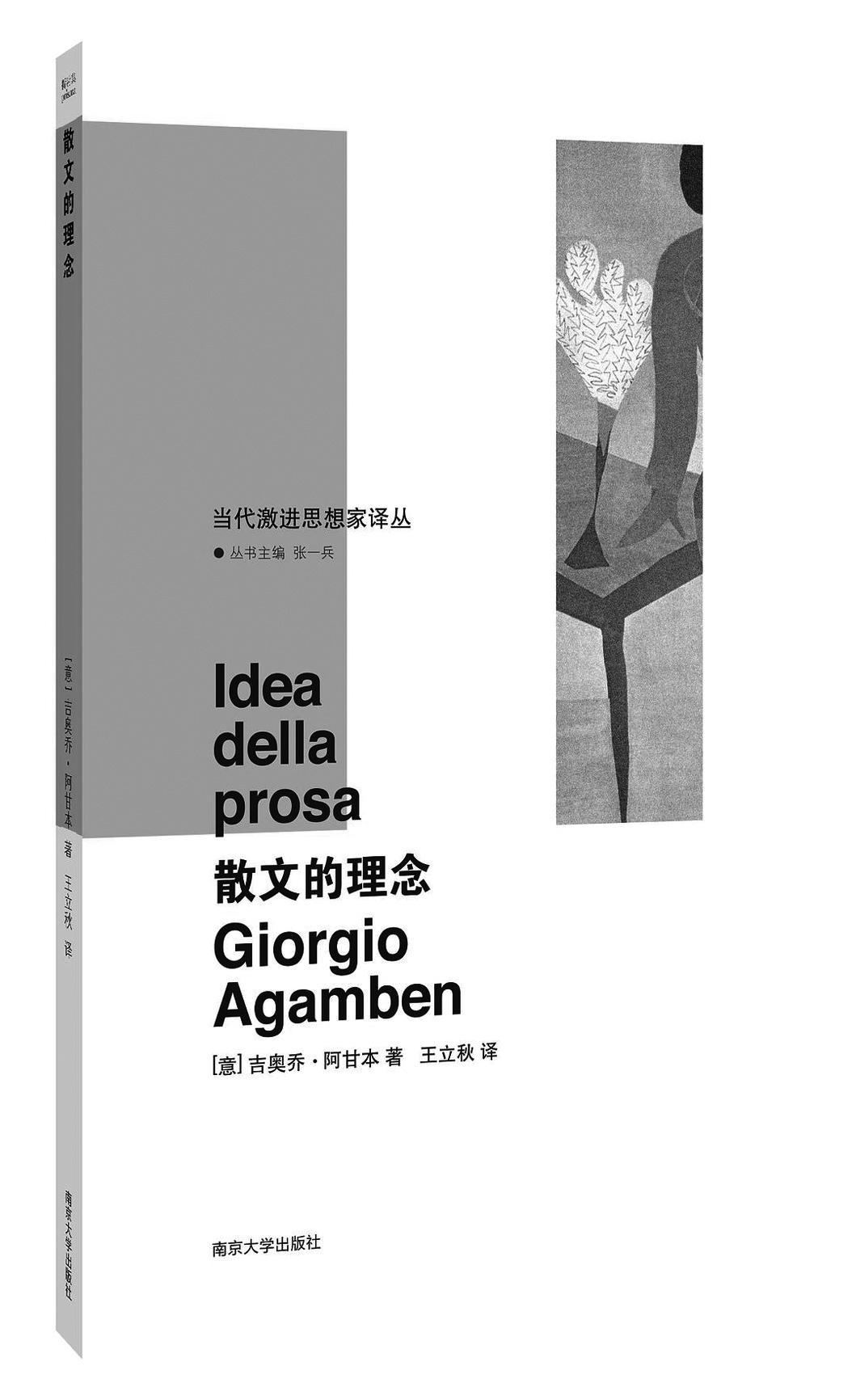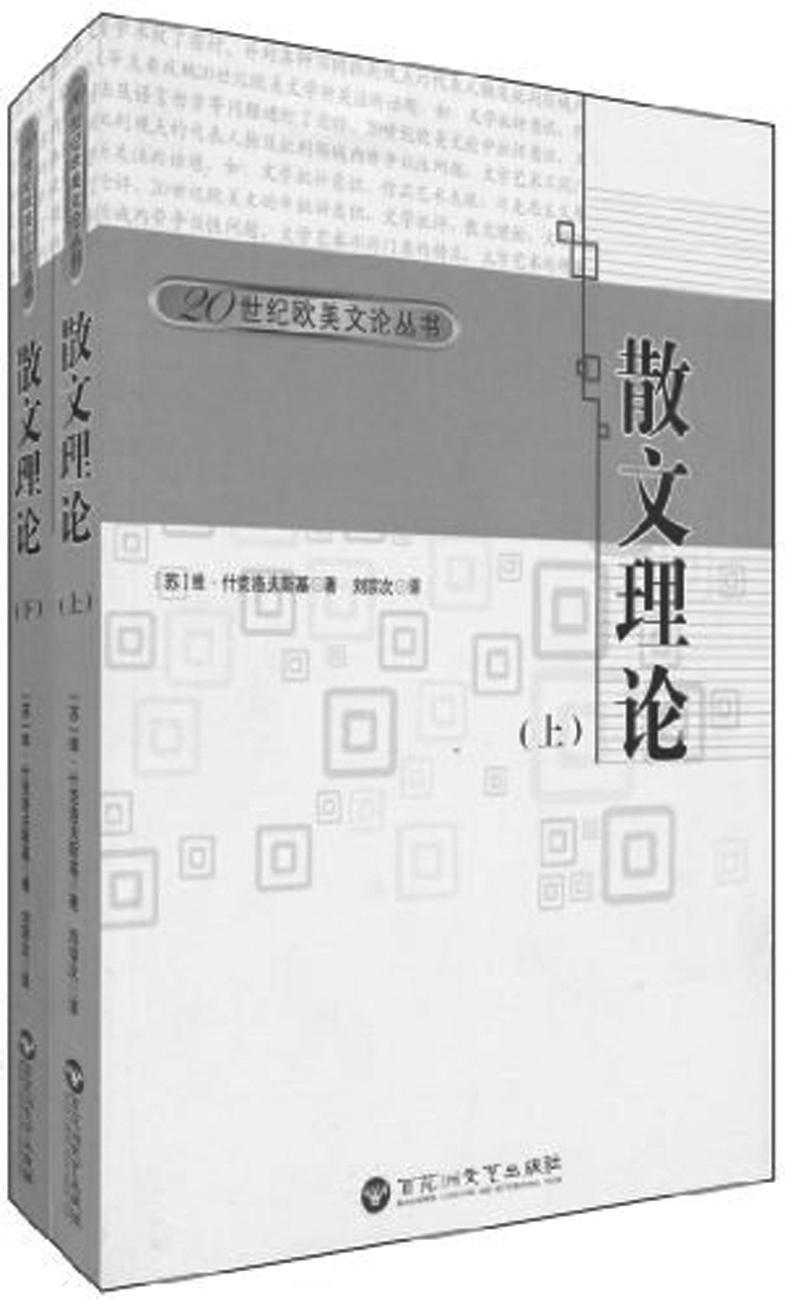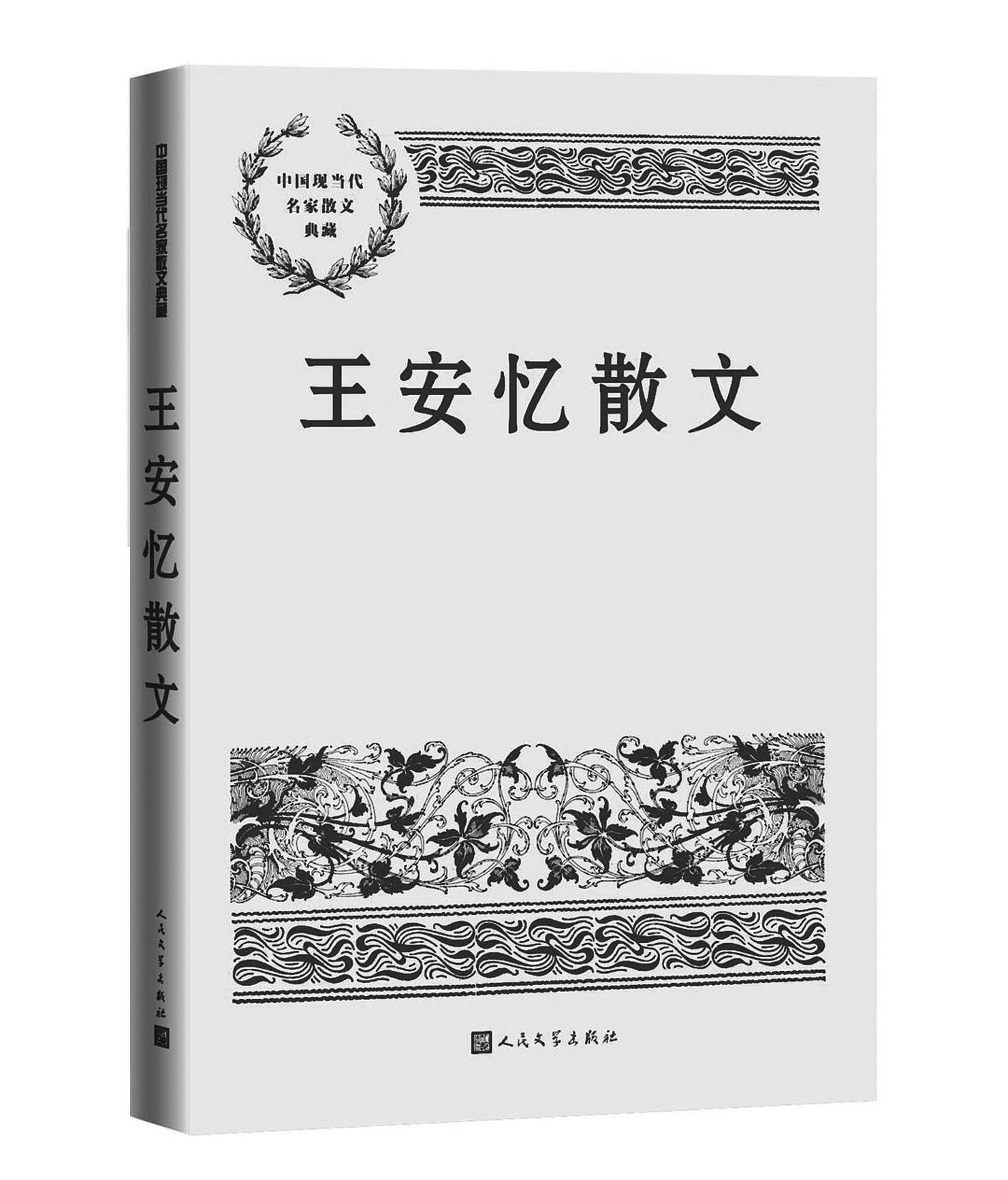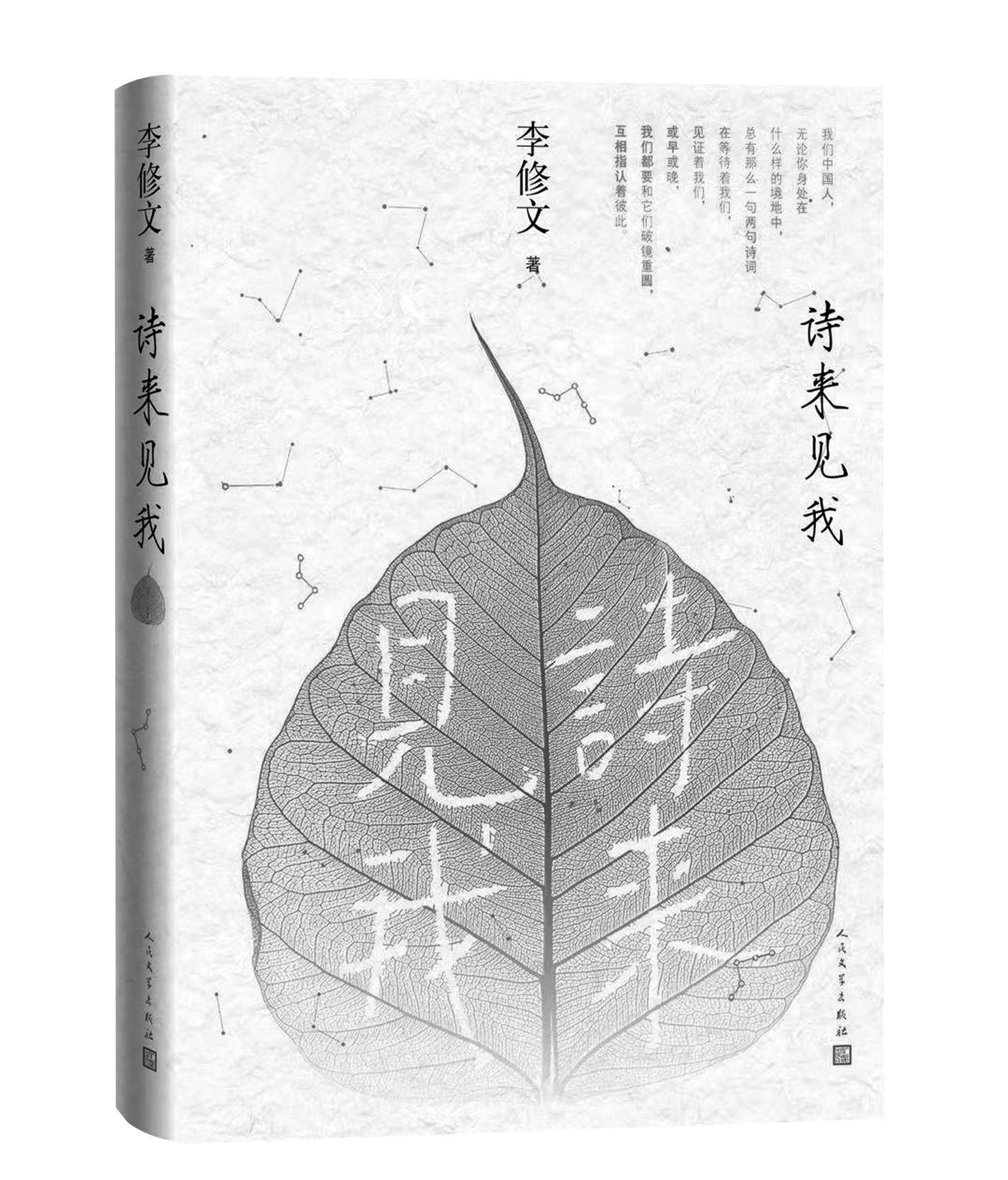现代散文是中国新文学传统的重要一支,近年来,随着创意写作学科在中国如火如荼落地发展、众多新媒体平台涌现,散文写作也在悄然变身,产生了新的生机和可能性。
今年热播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是少有的由散文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是首部入围戛纳电视剧节主竞赛的长篇华语剧集。此前,刘梓洁的散文《父后七日》也曾被改编成电影,获得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我们开始探讨现代散文是怎么回事、它的前途在哪里、未来的散文可能是什么样的。在《散文的变身》一书中,王安忆、胡桑、张怡微、陶磊、朱婧、包慧怡等二十余位作家、学者分享了他们对现代散文文体演变的观察与思考,可以说是一堂十分生动的“散文课”。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
“散文是用自己创造自己”
关于散文的文体界定,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现在的“散文”之名来自于英文的“essay”,是狭义的散文。广义的散文被称作“prose”,它打破了很多界限。先秦的诸子散文,后来的史传、策论、墓志、随笔、信札等,以至于当代的非虚构以及其他新的文本形式,都属于广义的散文。
作家王安忆在《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中把散文定义为“那种最明显区别于小说和诗的东西”,在她看来,散文与小说、诗存在非虚构与虚构的对立,“小说是情节的虚构,诗是语言的虚构”,而散文“最接近于天然”“在情节和语言上都是真实的”。
2004年,王安忆受聘复旦中文系,创立了中国内地第一个MFA“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开班之际,就定下了小说和散文两个方向。2020年,王安忆又为创意写作专业新开了一门“非虚构写作”课。非虚构所规定的“真实性”既是限制,却也提供了取材的路径;三万至五万字的标准,无形中开辟了长篇幅的散文体例,在大容积的迫使下,学生们开始将叙事汇入散文作品,“将亲历的生活提供给文章,让未明的存在熠熠生辉,而这些正是虚构努力要做又未必能做到的。”
但这样一来,散文与小说的界限再次变得模糊。王安忆由此提出了“记忆”一词,“‘记忆’几乎是非虚构的伦理。我们不能如小说那样,假定事情在进行时发生,只能在文字里让逝去的时间重现和还原,写作是唯一的机会……散文的文体大约就是工具的性质,用自己创造自己,此自己创造彼自己!”
散文家龚静曾负责讲授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散文写作实践”和“散文经典细读”课,她说:“周作人提出过文章之‘余情’观,意谓拥有了作者的情致,那么即使是同一篇说明文,也是可以成为佳作的。对此,我深以为然。”龚静对散文的甄别和评判,不再囿于狭隘的体裁区隔,好的散文就是“有我”的文章。
上海中学国际部老师张心怡认为:“怎样的生活经验能够被放入小说,需要经过一个与自我疏离的阶段。而散文的书写即标榜从自我经验开始,广义的散文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和现实生活联系的抓手。”比如,名人先成为某个领域的“名人”,后成为散文写作者,对工作、行业本身的书写往往带有自传性,李安的《十年一觉电影梦》、贾樟柯的《贾想》、许鞍华的《许鞍华说许鞍华》中自述部分,诸如此类。
“真正意义的国民文体”
说到现代散文的源头,郁达夫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提到,在五四运动、个人的发现、思想的觉醒和文字的自由等几个前提下,散文“就滋长起来了”。各种文体中,小说、诗歌和话剧相对而言都有审美难度和准入门槛。唯有散文可以接纳更多的普通写作者,可以说是真正意义的国民文体。所以,郁达夫才会说:“正因为那种不拘形式的散文的流行,正因为引车卖浆者流的语气和村妇骂街的口吻,都被收到了散文里去的缘故。”
郁达夫在导言中还提到“散文的心”,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情”在散文文体中的重要性开始往前提,情的背后是个人,是日常生活,而不是历史、天理、国家。现代散文的内容范围得以扩大,其实,扩大的不只是题材内容,也是国民的文学生活疆域和精神边界。
现代散文能够被大众参与和分享,自然离不开现代传媒变革。“五四”以后,白话文报刊大量涌现,发表散文的媒体,有像《新青年》以思想文化见长的;有如《语丝》专事散文随笔的;而《创造》《现代》这些综合性文学刊物也都有散文的一席之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种类型的报纸副刊,像鲁迅发表了许多杂文的《申报》“自由谈”,它们包容了自由、短小、可读性强的“小”散文,直接面对受过基本现代教育的普通读者。
当代散文也不例外,除了专门的杂志,很多报纸的副刊都是重要的散文发表园地。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众传媒的复苏直接带来散文的繁荣,散文专栏作家大量出现,比如大家熟悉的王小波就给《辽宁青年》《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写过散文随笔专栏。
当代散文的多元变体
新世纪以来,非虚构的繁荣是当代散文文体十分重要的新现象,它可能意味着文学审美的变革和读者对“真实”诉求的不满足。非虚构成为出版热潮,它背后的学科交叉特征是不能忽略的。这意味着,基于“事实”的“叙述”文体,开始是从新闻学科进入文学学科,近年来又有了与人类学、历史学学科交叉的特征。从家族回忆史、地方回忆史到文化回忆史,散文呈现出多样的发展路线。
祝勇的《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古物之美》等“故宫系列”散文非常具有个人辨识度,与黄仁宇、史景迁的非虚构历史写作相比,祝勇的作品更加发散和抒情,强调想象与历史的叙事性。
李修文的散文则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实现自我的田野化,把“我”作为一种方法,从体制僵硬的文人世界走向江湖与山河。《山河袈裟》里的“我”写奔忙途中的山林与小镇,写途中遇到的一个个具体的人,《诗来见我》则把自己置于显示器的位置上,诗词及诗人携带的风雪、尘埃、怨与仇都一一与“我”相逢。
邹世奇的散文集《只向花低头》具有文化散文的品格,其中谈诗词、谈中西名著、谈电影、谈历史名家、旅游见闻,不拘一格,写法上也没有一本正经的约束和拘泥,有时以小说笔法入散文。
“至少有一个散文写作类别,具有开采的资源,即传记文学。”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怡微说,1952年担任复旦中文系主任的朱东润,素以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筚路蓝缕之功为学界称道,同时也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朱东润的传记作品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遗著《李方舟传》,原型是朱东润的妻子邹莲舫。为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立传,可以说是中国传记史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始。相对稀缺的女性传记书写,在现实处境下大有可为。
公众号、短视频都是新媒体时代的“私散文”
新世纪前后,从互联网到移动终端的普及,如果不把网络文学局限地理解为大型网文平台发布的长篇叙事,可以说,正是网络新媒体使得散文蓬勃地滋长起来。更多的普通读者同时也是散文的写作者,全民写作成为可能。
自媒体平台发表的方式,使得普通写作者可以让作品第一时间接触到读者,而非被一种标准挑拣或修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时代的最大获益者是散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提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21世纪有两个文类会重新崛起,一个是散文,一个是诗,原因正在于两者的“业余性”。
网络文学二十年,从最早的榕树下到天涯社区“散文天下”等的文学论坛时代,到博客,再到微博、微信、APP时代,网络技术不断更迭,散文的版图不断扩张。今天的豆瓣阅读、腾讯大家、网易人间、“ONE一个”、简书以及微信公众号积聚着新散文创作的潜能。以豆瓣阅读为例,活跃的散文作者有沈书枝、风行水上、黎戈、张天翼、邓安庆、苏美。
如果要说进一步丰富反映当代生活的散文门类的话,公众号、微博乃至长短视频因其即时性的特点和追逐热点的本能,正在成为这一门类的新生力量。它们的文学性虽然有待商榷,但很明显,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这十年是网络创作者不断提升创作自觉性的十年,从无差别、碎片化、未修剪的日常生活复刻性展示,到有意识、有主题、剪裁明确的日常生活场景化表达,同时还涌现出一批以思想性、智识性见长的网络散文创作者。网络新媒体对个体日常生活差异性的尊重,造就了一个“私散文”时代。
从短视频到公众号非虚构文体爆炸式的繁荣,吸引着巨大的读者流量。好像每个人都在通过不同的形式,发抖音、快手,自建公众号,包括向“三明治”等媒体平台投稿,每个人都想为自己发声,每个人都想作为自己发声,而不是被别人赋义,这充分说明了郁达夫“散文的心”中发现人、建立人的现代性思想已经通过文化启蒙运动根植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面对这种广义上的散文创作狂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婧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如果作者过度沉溺自我表演,文字有可能沦为一种装饰性的‘软文’。专注于表演、被观看和被注意,不利于文字的深度和深刻,进而带来新媒体散文过于偏向和偏执‘轻’阅读。”因此,新媒体滋生的新散文,未来如果要有一个好的前景,需要写作者更多的审美自律和文学进取心。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张祯认为,当代散文的困境,还有一部分源自“有情的主体”的衰败和消散。“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探讨了“情”的纯粹和生命力。而当代社会在努力培养一种“理性的主体”,强调用科学的方式,将情感控制在所谓正常的范围之内,加以理性调控。
与此同时,在商业社会的消费主义影响下,很多公众号写作者将世态人情和审美消费结合在一起,这种类型的散文写作实际上也有其历史脉络可循,比如“时尚博主”章小蕙从报纸副刊专栏延续下来的写作方式,以及新世纪初安妮宝贝塑造的一系列穿棉布长裙、光脚穿球鞋的女孩子形象,实际上也带着一种很强的恋物气质。
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筛选出适合讲述的生活、如何全面客观地展示自己与他人的生活经验?如何在信息茧房、具身模拟的时代超越自己狭隘的认知,提供阐释、提炼日常生活精神的方法?这些都是今后传统散文写作者与网络散文创作者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