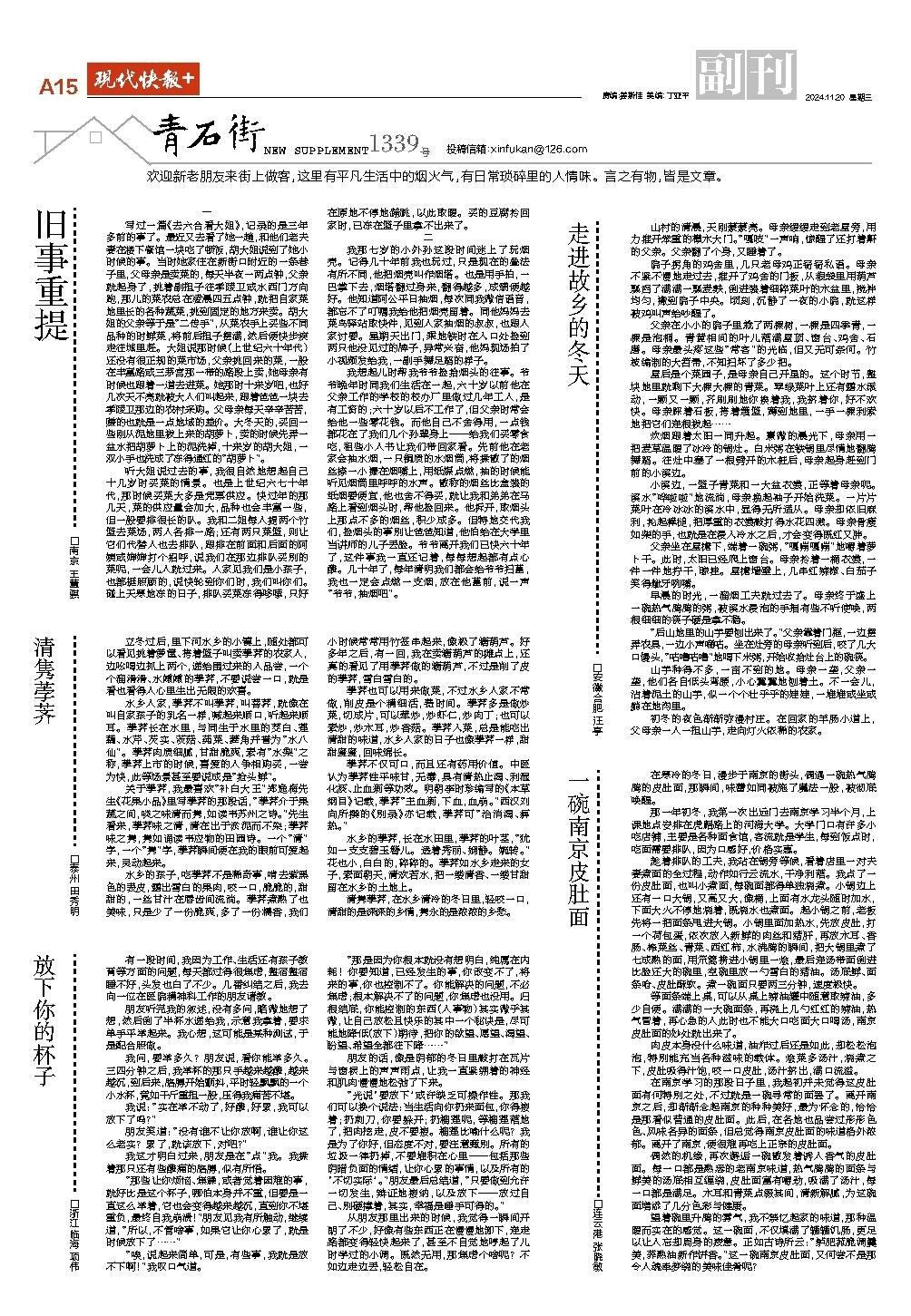□南京 王慧骐
一
写过一篇《去六合看大姐》,记录的是三年多前的事了。最近又去看了她一趟,和他们老夫妻在楼下餐馆一块吃了顿饭,胡大姐说到了她小时候的事。当时她家住在新街口附近的一条巷子里,父母亲是卖菜的,每天半夜一两点钟,父亲就起身了,挑着副担子往孝陵卫或水西门方向跑,那儿的菜农总在凌晨四五点钟,就把自家菜地里长的各种蔬菜,挑到固定的地方来卖。胡大姐的父亲等于是“二传手”,从菜农手上买些不同品种的时鲜菜,将前后担子摆满,然后便快步疾走往城里赶。大姐说那时候(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没有很正规的菜市场,父亲挑回来的菜,一般在丰富路或三茅宫那一带的路段上卖,她母亲有时候也跟着一道去进菜。她那时十来岁吧,也好几次天不亮就被大人们叫起来,跟着爸爸一块去孝陵卫那边的农村采购。父母亲每天辛辛苦苦,赚的也就是一点地域的差价。大冬天的,买回一些刚从泥地里拔上来的胡萝卜,卖的时候先弄一盆水把胡萝卜上的泥洗掉,十来岁的胡大姐,一双小手也洗成了冻得通红的“胡萝卜”。
听大姐说过去的事,我很自然地想起自己十几岁时买菜的情景。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候买菜大多是凭票供应。快过年的那几天,菜的供应量会加大,品种也会丰富一些,但一般要排很长的队。我和二姐每人提两个竹篮去菜场,两人各排一路;还有两只菜篮,则让它们代替人也去排队,跟排在前面和后面的阿姨或婶婶打个招呼,说我们在那边排队买别的菜呢,一会儿人就过来。人家见我们是小孩子,也都挺照顾的,说快轮到你们时,我们叫你们。碰上天寒地冻的日子,排队买菜冻得哆嗦,只好在原地不停地蹦跳,以此取暖。买的豆腐拎回家时,已冻在篮子里拿不出来了。
二
我那七岁的小外孙这段时间迷上了玩烟壳。记得几十年前我也玩过,只是现在的叠法有所不同,他把烟壳叫作烟塔。也是用手拍,一巴掌下去,烟塔翻过身来,翻得越多,成绩便越好。他知道阿公平日抽烟,每次同我微信语音,都忘不了叮嘱我给他把烟壳留着。同他妈妈去菜鸟驿站取快件,见到人家抽烟的叔叔,也跟人家讨要。星期天出门,乘地铁时在入口处捡到两只他没见过的牌子,异常兴奋,他妈现场拍了小视频发给我,一副手舞足蹈的样子。
我想起儿时帮我爷爷捡拾烟头的往事。爷爷晚年时同我们生活在一起,六十岁以前他在父亲工作的学校的校办厂里做过几年工人,是有工资的;六十岁以后不工作了,但父亲时常会给他一些零花钱。而他自己不舍得用,一点钱都花在了我们几个孙辈身上——给我们买零食吃,租些小人书让我们带回家看。先前他在老家会抽水烟,一只铜质的水烟筒,将揉散了的烟丝捺一小撮在烟嘴上,用纸媒点燃,抽的时候能听见烟筒里呼呼的水声。散称的烟丝比盒装的纸烟要便宜,他也舍不得买,就让我和弟弟在马路上看到烟头时,帮他捡回来。他拆开,取烟头上那点不多的烟丝,积少成多。但特地交代我们,捡烟头的事别让爸爸知道,他怕给在大学里当讲师的儿子丢脸。爷爷离开我们已快六十年了,这件事我一直还记着,每每想起都有点心酸。几十年了,每年清明我们都会给爷爷扫墓,我也一定会点燃一支烟,放在他墓前,说一声“爷爷,抽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