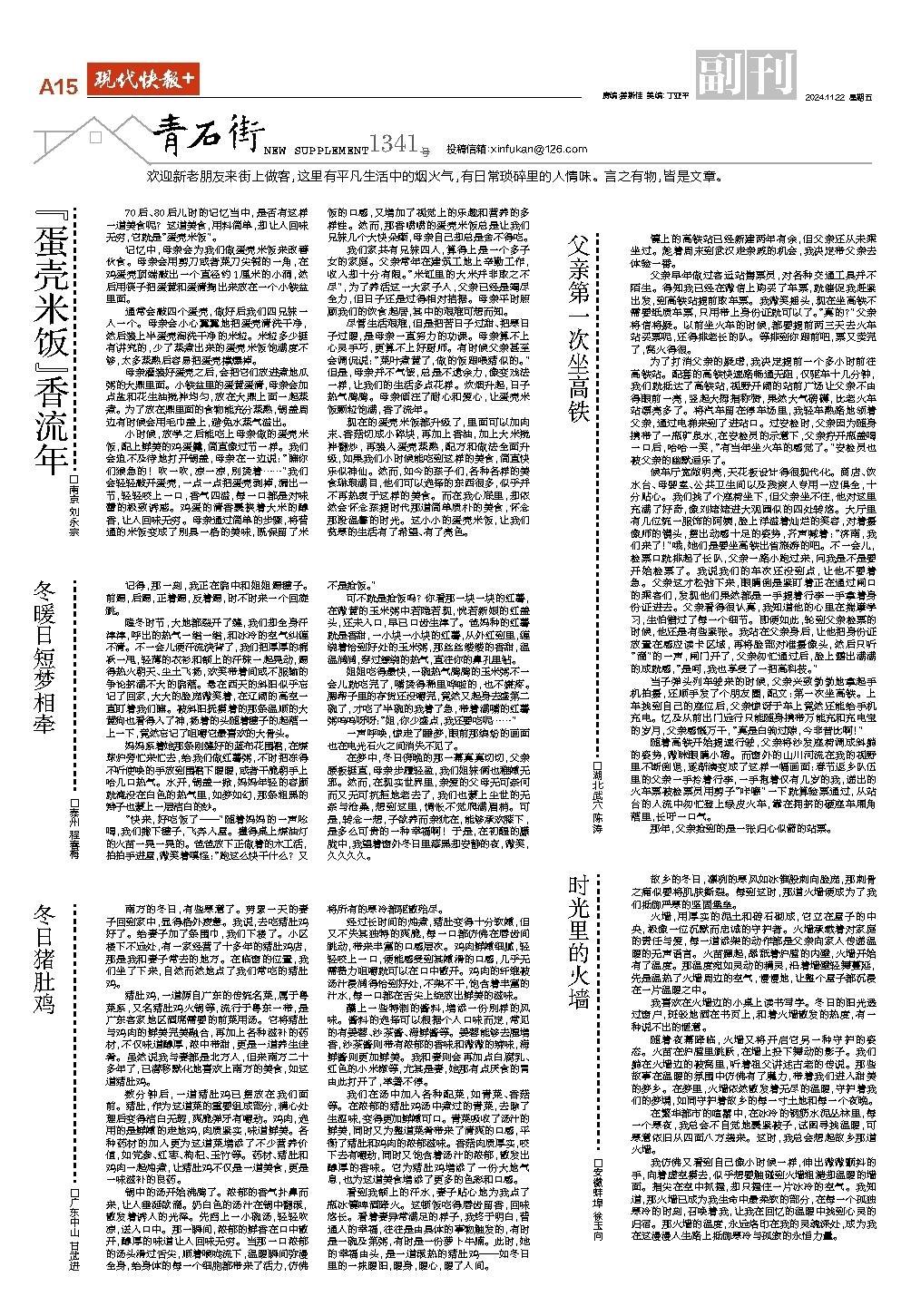□泰州 程春梅
记得,那一刻,我正在院中和姐姐踢毽子。前踢,后踢,正着踢,反着踢,时不时来一个回旋跳。
隆冬时节,大地都裂开了缝,我们却全身汗津津,呼出的热气一绺一绺,和冰冷的空气纠缠不清。不一会儿便汗流浃背了,我们把厚厚的棉袄一甩,轻薄的衣衫和额上的汗珠一起晃动,踢得热火朝天、尘土飞扬,欢笑带着间或不服输的争论挤满不大的院落。悬在西天的斜阳似乎忘记了回家,大大的脸庞微笑着,在辽阔的高空一直盯着我们瞧。被斜阳抚摸着的那条温顺的大黄狗也看得入了神,扬着的头随着毽子的起落一上一下,竟然忘记了咀嚼它最喜欢的大骨头。
妈妈系着她那条刚缝好的蓝布花围裙,在煤球炉旁忙来忙去,给我们做红薯粥,不时把冻得不听使唤的手放到围裙下暖暖,或者干脆朝手上哈几口热气。水开,锅盖一掀,妈妈年轻的容颜就淹没在白色的热气里,如梦如幻,那条粗黑的辫子也蒙上一层洁白的纱。
“快来,好吃饭了——”随着妈妈的一声吆喝,我们撇下毽子,飞奔入屋。撞得桌上煤油灯的火苗一晃一晃的。爸爸放下正做着的木工活,拍拍手进屋,微笑着嗔怪:“跑这么快干什么?又不是抢饭。”
可不就是抢饭吗?你看那一块一块的红薯,在微黄的玉米粥中若隐若现,恍若新娘的红盖头,还未入口,早已口齿生津了。爸妈种的红薯就是香甜,一小块一小块的红薯,从外红到里,缠绕着恰到好处的玉米粥,那丝丝缕缕的香甜,温温润润,穿过缭绕的热气,直往你的鼻孔里钻。
姐姐吃得最快,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嘴烫得稀里哗啦的,也不嫌疼。腮帮子里的存货还没嚼完,竟然又起身去盛第二碗了,才吃了半碗的我着了急,带着满嘴的红薯粥呜呜呀呀:“姐,你少盛点,我还要吃呢……”
一声呼唤,惊走了睡梦,眼前那缤纷的画面也在电光石火之间消失不见了。
在梦中,冬日傍晚的那一幕真真切切,父亲腰板挺直,母亲步履轻盈,我们姐妹俩也稚嫩无邪。然而,在现实世界里,亲爱的父母无可奈何而又无可抗拒地老去了,我们也蒙上尘世的无奈与沧桑,想到这里,惆怅不觉爬满眉梢。可是,转念一想,子欲养而亲犹在,能够承欢膝下,是多么可贵的一种幸福啊!于是,在初醒的朦胧中,我望着窗外冬日里漆黑却安静的夜,微笑,久久久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