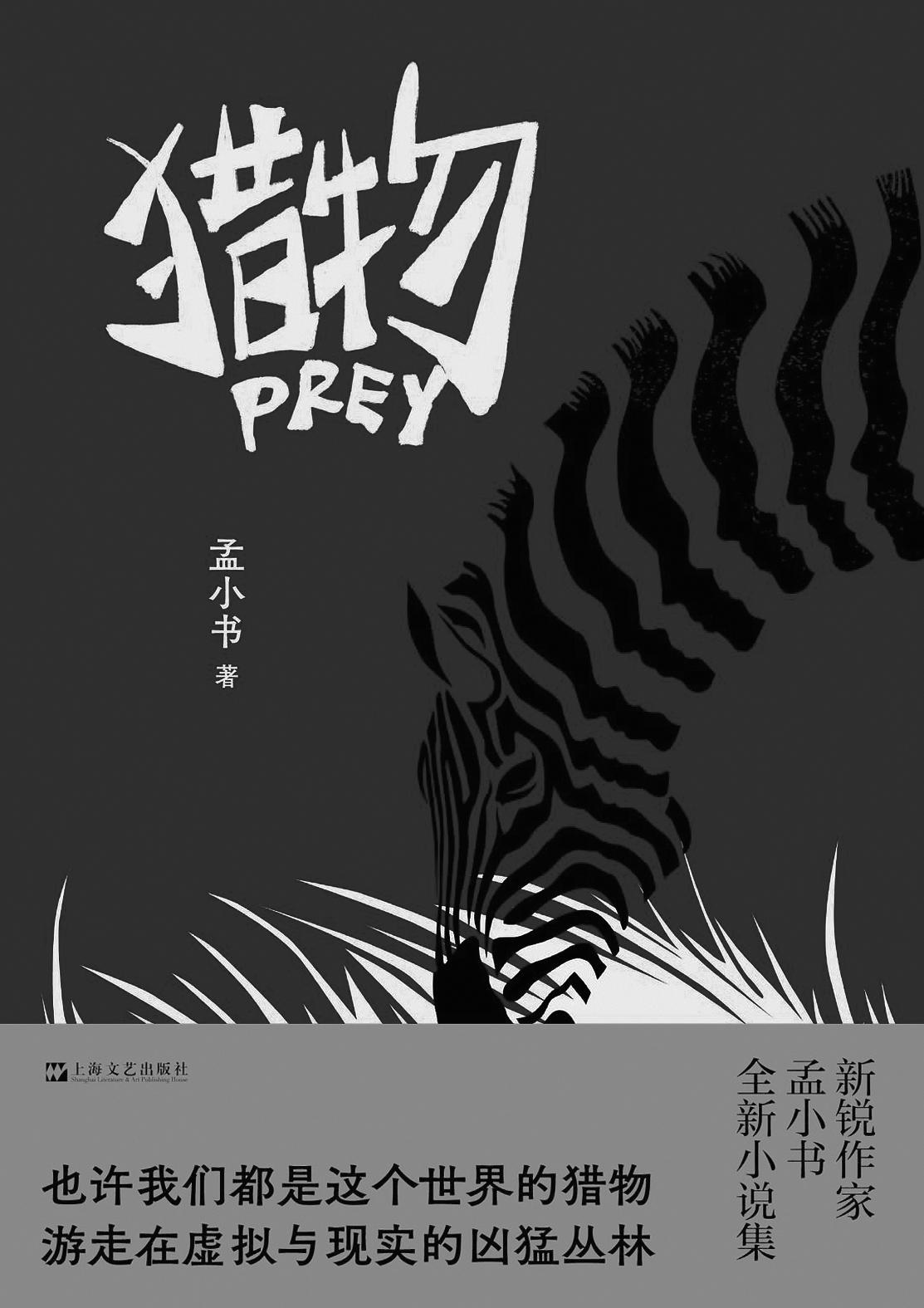非洲丛林里的一场狩猎,高贵的白色长颈鹿轰然倒下;引发网络暴力的龙卷风,导致女孩的死亡;婚姻破裂的父母面临人间悲剧,陷入自我怀疑,广漠丛林无法告诉他们关于婚姻、情感的正确答案;在“云端”掩盖残疾身躯的网红少女奔赴K的约定,等待她的是美好梦想,或是孤注一掷的“杀猪盘”;网络世界的林林总总,与现实的温情与残暴纠缠往复,无尽的故事由此产生……
新锐作家孟小书刺破现实的新作《猎物》,拨开网暴迷雾,探讨生命样式的多种可能:当“数量”等同于“正义”时,乌合之众脚下的虚拟之地犹如猎场,你我都是他人眼中的猎物,只是你不知道。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
人是猎手,也是猎物
读品:首先请您谈谈《猎物》的创作契机。书中三个故事涉及非洲狩猎、网红经济、网络暴力、杀猪盘骗局等,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些话题?
孟小书:这本书由三个中篇小说组成,是按照创作顺序排列的。写第一个故事《狩猎》差不多是两三年前,那时候看了很多关于非洲打猎的纪录片,导演给了很多镜头语言,关于人和动物的关系,他其实是从一个批判的角度去拍摄的。看完纪录片,我觉得在猎场里面,不见得人是主导动物的,人如果没有枪支、汽车保护的话,也是猎场的猎物之一。当时社会上的网暴事件也挺严重的,我觉得人在互联网中,和在猎场的情景是差不多的,会被网民追索。所以我就把这两个事件结合到一块,写了一个故事。
第二篇小说《白色长颈鹿》是第一篇小说的延续。女主人公Leila因为网暴去世,感情已经破碎的父母去非洲安葬女儿,他们再次回到猎场,探索关于女儿死亡真相的蛛丝马迹,同时试图重启他们以前的记忆,看看能不能再走到一起去,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两篇小说有连贯性,如果拆开来看的话,各自也是完整的故事。
第三个小说《终极范特西》是关于“杀猪盘”的故事,我看了很多资料、新闻,在写作的时候保留了一点人性之光,读者看完这个小说后,应该对人性还是有信心的。我觉得写作和平时阅读的审美趣味还是有很大关系,我平时做杂志编辑,看到很多小说写得特别悲观,很容易把人写死掉,但是我喜欢看一点有人性之光的东西,所以写的时候可能也会把这些东西带入小说里面。
读品:三个故事通过“猎物”这个线索被串起来,在每个故事中,“猎物”都有不同的含义,能具体阐释一下吗?
孟小书:前两个故事里的意象主要是白色的长颈鹿,白色长颈鹿其实就是得了白化病的长颈鹿。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病态的女主人公Leila其实和得了白化病的长颈鹿还挺像的。在猎场,我觉得长颈鹿是最不应该被猎杀的动物,因为它太大了,作为目标太明显了,动作又没有那么灵活,相对于豹子、狮子或者羚羊,它非常容易被捕猎。这一点也和Leila挺像的,因为她是网红,作为网暴的目标也很明显。在最后一个故事里,残疾的女网红Leila是猎物,被骗到“科技园区”的K也是猎物,而两个猎物彼此之间还在互相猎杀。
读品:《狩猎》里的K是我觉得全书最复杂的角色,他在学生时代热衷狩猎异性的游戏,遇到Leila后却“偃旗息鼓”、默默陪伴;他对Leila有很深的爱意,却又被Leila的抑郁症消磨到放弃与她发展为真正的爱情;他在非洲狩猎中原本只是辅助记录的角色,却在最后一刻果断、冷酷地对受伤的长颈鹿扣下扳机,那一刻他心里的莫名兴奋耐人寻味。能谈谈创作这个人物的灵感吗?
孟小书:K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可能就是出于人类的狩猎本能。很现实的是,即使他再爱Leila,再想为对方付出,他也很难耐得住一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人去消磨,也很难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她。包括我自己也是经历过产后抑郁,我发现女性情绪不稳定的时候,男性只是理论上理解,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很难做到真正的理解。
网络让人与人的感情脆弱又疏离
读品:《白色长颈鹿》里,老贺和竹桑同时为了追寻女儿死亡的真相奔赴南非,心态和表现却截然相反,老贺虽然有悲伤,但更多梦想着与竹桑复合的未来;竹桑心中失去女儿的沉重、痛苦居多,甚至女儿的死亡让她的梦想也随之失落了。我们似乎能看到父亲和母亲对待女儿的情感浓度、表达方式的不同。
孟小书:这对父母其实是一个成功的父亲和一个失败的母亲。竹桑一生中几乎没做过什么事,哪怕她去美国看女儿,也因为找不着路没看成,她是一个被照顾的,几乎没什么生活能力的女性。面对老贺这样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她内心还是很自卑的,尤其在女儿面前,她想证明自己和她的父亲一样优秀,但是女儿死了,她没有办法证明了。老贺身上则有逃避的成分在,如果女儿是因为他的推荐去非洲后死掉,他的整个人生都会被自责压迫着,当他发现女儿去非洲跟他没有关系,他轻松了很多。这就是人性比较复杂的部分,即使是自己的女儿,他也不愿意承担那么大的责任。
读品:从小说的描写看,当下的人越来越难在现实中与人建立深厚、真挚的情感关联。
孟小书:上一代人与当下年轻人处理情感的方式不一样,他们还是比较传统的。老贺和竹桑的关系其实非常脆弱,尤其分开了那么长时间,他们重逢之后彼此之间的好感,都建立在想象的层面上。实际生活在一起没几天,他们就可能因为一个喷嚏、一个恶心的饭粒,回想起以前无数引发彼此怨恨的场景,所以他们再次建立感情是很难的。
现在的年轻人又面临着另一种状况。我们现在太依赖于网络了,很多朋友之间的关系都停留在微信朋友圈的点赞之交。我们不太容易也不太愿意随便地进入另一个人的生活,大家自我保护的界限感越来越明显。我认为这可能跟网络以及短视频、网络小说的发展有关,大家都沉迷于手机,几乎一分钟都离不开它。包括算法,我觉得庞大的外卖员群体、电商的从业人员,在某种程度上都被算法奴役了。
读品:“自由”也是全书着重探讨的命题。故事中的人物一半拥有自由,但一点也不快乐,烦恼和焦虑随时产生,另一半丧失了自由,愿意用条件换取自由,同时又不断问一个问题,拿到自由的权利以后怎么办。这种围城一样的局面,请您具体谈谈。
孟小书:我觉得自由都是相对的,同一个人不同年龄段对自由的理解、向往程度也不一样。比如说老贺这样的艺术家,他在离婚之后确实得到了自由,他很享受与自己独处的时光,不太需要家人的陪伴、亲情的温暖。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开始需要有人来照顾他,所以他想和竹桑重新在一起,其实也不是出于多么爱她,他只是希望自己年迈体衰的时候,有一个人能在他身边而已。
《终极范特西》里的郑宝林,他为了挣钱留在“科技园区”里,也为了帮邻居小北家里还债,小北之前被他骗到这个园区,后来没几天死了。郑宝林之前是椰农,如果他真的出去重获自由,做回了椰农,他在金钱方面也是不自由的,他就是很实际的这么一个人。
快节奏并不能带来良性循环
读品:书中也比较集中地探讨了网络直播、短视频流量网红背后的一系列问题,网络暴力、网络“人设”的建立与崩塌、同质化的生活模式,乃至身材焦虑、抑郁症、被害妄想。互联网究竟为当代人认知世界、认知他人提供了便利,还是增加了难度?
孟小书:就个人来讲,我对互联网上大量的直播是比较抵触和反感的。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做了网红,我觉得他们成了网红之后,失去了很多原有很真实的东西,这是我个人化的、最直观的感触。就整个社会来讲,我觉得如今网络过于便利了,外卖确实让我们半个小时之内可以拿到餐品,但我们节省出来的时间又是用来干吗呢?不管是网店还是外卖,包装盒对自然的破坏,对实体经济的打击,放在长远考虑的话,其实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读品:小说里也提到“绿色和平”这样的环保组织,其中是否也包含了您自己的一些生态主义的态度?
孟小书:我去年去了几个跟气候议题有关系的地方,因此最近对气候议题比较关注。首先去了巴西雨林,看了大豆场、牛场,当地人为了开辟农田、挖炭、挖掘金矿,破坏了很多雨林,雨林里居住的土著被迫迁徙,流离失所。我去采访了几个当地的土著部落,他们特别抵触对自然的破坏,当地政府会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我还去了格陵兰岛看冰川,很多冰川就在我们眼前“噼里啪啦”往下落,当你看到冰川在你眼前消融的时候,你会特别震撼,会切身地为未来的地球气候感到担忧。目前,我在写关于巴西的非虚构作品,会涉及雨林、气候、环境,可能未来还会持续关注。
读品:从时尚杂志到传媒网站,又到影视公司和传统文学期刊,之前的工作经历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孟小书:我觉得还是有影响,不同的工作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我之前在加拿大读书,上大学最后一年学的是时装设计,刚毕业回国的时候,我在《时尚芭莎》工作过一段时间。真正接触以后,我发现实际的工作环境和我理想中时尚杂志的气氛不太一样,就挺失望地离开了。之后去了影视公司做发行,亲身接触后发现,每个电影虽然内容不一样,但那套模式基本都是一样的,就觉得没意思。后来开始写作,对文学感兴趣,就去了杂志社,目前在杂志社有七八年了,我觉得还挺好的。上一本小说,我写了很多在影视公司的人和事。
读品:从开始写作至今,一路走来,您觉得自己哪些方面有了发展,哪些方面还有不足?
孟小书:现在可能心态放得平稳一些,不会焦虑于今年有没有写,不会为了写而写,而是会找一些我感兴趣的话题去写。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技巧和阅读量还应该提高一些。前两天有一个在北京的研讨会,有个老师说现在的小说普遍对内心的描写不够,我平时做编辑看稿子也确实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对故事性的追求太高了,总想写一个很好看的故事,以至于忽略了很多人物心理的描写。我们现在的小说写得越来越快,因为节奏快的作品比较适合改编影视剧,如果内心描写太多的话,就会把整个故事节奏拉慢。影视公司还是会倾向于故事化、节奏快、戏剧冲突强的那种故事。
孟小书
生于北京。著有作品集《满月》《业余玩家》《午后两点半》,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浪尖上的大鱼》等。曾获第六届西湖·中国文学新锐奖、第二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山花双年奖、十月文学奖、丁玲文学奖等。现为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