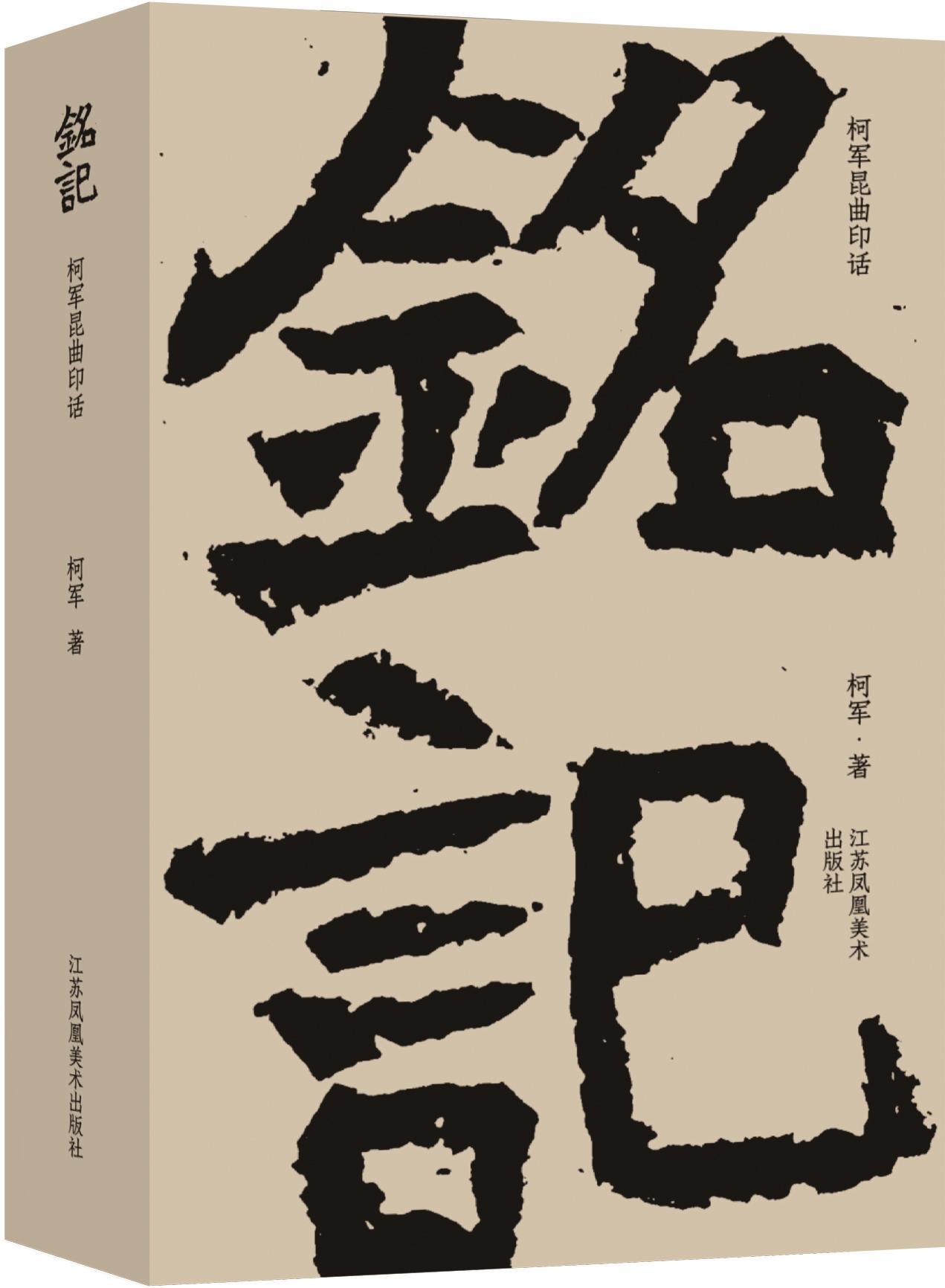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未成名的柯军,一人一枪跟着戏班,天南海北地走穴。
戏台上,百万雄兵酣战,收鼓时,需手握关刀扫台,为战死的猛士安魂。这是戏班传下来的规矩。一具、两具、三具……年轻的武生心底升腾起一阵悲壮,这影响了其后几十年的演艺生涯。
时过境迁,他已是昆曲大家,经典角色自不胜数,又以“素昆”别开天地。昆曲传字辈艺术家从艺百年时,他起心动念,要用篆刻给那些“不重要”的人留名。
“昆曲这样一种样式能让我们艺人忘我地投入:你不重要,杜丽娘重要;你不重要,汤显祖重要;你不重要,把昆曲演红了、演火了重要。传字辈100年了,这些人对昆曲的贡献不可估量,他们的名字随时间流逝,可是多少人能记得他们?”
一位、两位、三位……夜深,案前,捉刀耕石,2024年,这本名为《铭记》的书终于面世。奇思妙构如万斛泉源,从前的江湖夜雨、舞台上的忠义千秋、未来的艺术狂想,一时间气血涌上心头。
大丈夫,悲伤犹在;大武生,翻江倒海。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 陈曦/文
马晶晶/摄 顾闻 张浩然/视频
我想铭记那些“不重要”的人
读品:这本《铭记》,是您“昆书”的第四作。回望前几部作品,《说戏》《素昆》围绕昆曲,《念白》谈的是台下生活,而到了本作,讲的完全是另一门艺术。您是否在有意识地拓宽昆曲“边界”?
柯军:昆曲首先是一门艺术,艺术肯定是无界的,这是其一。第二,艺术一定是生活的,而生活一定也是无界的。所以,我在做任何事情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艺术和生活的融合。不管是最传统的《说戏》、最先锋的《素昆》、最内心的《念白》,再到这次的《铭记》,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打开昆曲的多种样式。包括电影、歌曲、书法、传媒,这些也都是打开方式,但内容和情志以及它的逻辑,一定是围绕着昆曲最传统、最先锋和最内心去展开的。
《铭记》是让我回过头,重新了解昆曲的一本书。最初2021年的时候,我打算刻100枚印,刻100个昆曲的剧目、名人、典故,以此铭记老一代艺术家。尤其是,我想把昆曲传字辈刻出来,传字辈100年了,这些人对昆曲的贡献不可估量,他们的名字随时间流逝,可是多少人能记得他们?都知道昆曲,知道汤显祖,知道牡丹亭,知道杜丽娘,可有谁知道谁演过吗?传字辈传了那么多技艺,可未来又有多少人能记住他们呢?因为昆曲博大,这样一种样式能让我们艺人忘我地投入:你不重要,昆曲重要;你不重要,杜丽娘重要;你不重要,汤显祖重要;你不重要,把昆曲演红了、演火了重要。所以说这本《铭记》,我是想铭记那些“不重要”的人。尽管昆曲是小众的,篆刻是小众的,我写的书更是小众的,但不管怎么样,它刻在那里了。
读品:在大众的心目中您是昆曲名家,那又是怎样和篆刻结缘的呢?
柯军:年轻恋爱时,岳父看上我的人,看不上我的字,我的太太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然后我就开始发奋。当时从戏校刚毕业,跟着学校里的冯怀根老师学习书法、裱画、篆刻。篆刻也是谋生的一个手段,那时候到状元楼、古南都这样的涉外酒店去刻印,一枚印一个字就是60块钱,那个时候我的工资也就30块8毛。记得有一次晚上,一个旅游团来了20多人,每人都选择了一枚,我和老师两个人分工,当时还有一些牛角的印,材质很硬,但为了贴补家用,我们必须连夜刻。因为旅游团今天来,游玩归来,第二天可能就要走。
那个时候练出了很好的手上功夫。让我非常高兴的是,有机会给一些名家刻印,比如说戏曲理论界泰斗级人物郭汉城老师,老先生去世的时候已经100多岁了,他生前很喜欢那枚印,在著作里都会盖上它。还有昆曲大师张继青老师,她去台湾讲学时托我为曾永义等老师治印,她说这既是别致的礼品,也是展示大陆年轻一代昆曲演员的文化修养。很多篆刻名家都喜欢昆曲,像马士达、黄惇、庄天明等老师,这次出版这本《铭记》,也是受了庄天明老师的“鼓动”。
读品: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我们分享?
柯军:刻这些印时,辛尘老师给了点点滴滴的指导。从昆曲庞大剧情里、人物风格里,去找相对应的篆刻,印式里面有古玺、秦汉印,还有元朱文,再细分下去,圆的、方的、长的、阴的、阳的、阴阳融合的……太多了,篆刻的丰富性甚至比昆曲还大。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有一天刻了一枚印,拍张图片发给辛尘老师,然后将近两个小时没有回复。后来他回了一句话,“刚才在服侍90岁的父亲去医院看病,迟复为欠。”想想看,我的老师,从没有收过一分钱,我求教他以后,他还说回迟了感到抱歉,这是什么样的人格魅力?他说即使只有一个人在传播篆刻,他也愿意倾囊相授毫无保留。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传统文化,或者我们为什么要和古人对话,向古人学习,我们就是要去学习怎么做人,怎么把这种风范传递给下一代。
辛尘老师也说,晚清的时候,很多唱戏的名伶也喜欢写写画画,那个时候伶人地位非常低,所以要结交文人雅士、书画大家,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当然,文人们也愿意去扶持和帮助艺人们,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这里面有好作品,也有吹捧的。到了新时代,没有所谓“戏子”之说,我们都是文艺工作者,所以我们现在再去从事学习书画艺术,就不再是去附庸风雅,或者是“跨界”,要么不做,要做就要非常深入去做。现在很多明星大腕,喜欢晒他们的字,显示自己会跨界、很丰富、多才多艺,我没有这样做,而是很专业地学习。有时一笔错了、一刀错了,重刻!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很即兴的撞击、碰撞在里面,但这种率性随意都是处在一种高度的把控之中。
武生是昆曲里的一抹血、一声擂鼓和一道光
读品:这两年,您饰演角色多是很复杂的人物,比如鲁迅、比如王维,当下什么样的角色最能打动您呢?
柯军:对我来说,很多角色都是“扑面而来”,然后欣然接受。戏曲,更大程度上演的就是超出日常生活的可能性,日常生活不可能的,才是戏剧要表达的东西。面对那种非常极端的、近乎于残酷的人生境遇,你的灵魂受到了逼迫,生命遭遇极度的窘境,人物在这个特殊的情景下,不得不做出特殊的挣扎和特殊的选择,于是人格才会释放一种特殊的力量,关键时刻,千钧一发,戏剧的张力就在里面。
这个舞台上,武生,是一抹血、一声擂鼓和一道光。《夜奔》里的林冲奔向他理想的反面,《沉江》中的史可法以死殉国,包括《别母乱箭》周遇吉面对一家殉难,《望乡》苏武苦撑了19年的坚守。每一段,都是特殊场景下的选择,他们的人生面临了很多残酷的境遇,无奈、窘迫、考问。《唐才子传》里的王维也是,他被囚禁起来做了伪官,内心是很痛苦的,他吃药得了哑病,拉肚子老站不起来,但是他也不能去死,心里也害怕死亡。还有《瞿秋白》里的鲁迅,也是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目睹了社会现实,发出自己的呐喊,这些都很沉重,也很复杂。
下周开始,我要拍《顾炎武》的电影,顾炎武更是这样的人,他一直“拧巴”,处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状态里。昆曲有三个表达点,一个是人与自然的表达,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表达,还有最重要的是人和自己,“我和我”的冲撞、表达。我更喜欢的是关注人物内心,这样一层一层抽丝剥茧的表达,正是昆曲所擅长的。
读品:昆曲不光是风花雪月,也有江湖夜雨,此前采访白先勇先生,他说带领戏班巡演如“闯江湖”“跑码头”,您从艺这几十年来,是否也经历过创业维艰的时刻?
柯军:当然,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去温州草台班演出,当时我的工资是30块8一个月,而到那边去,一天就14块5。因为我是武生应工,住的地方和其他人都不一样,我的条件最好,在“头家”的家里面,单独一个房间,其他人都是住大床铺。他们特别喜欢武生,也爱惜武生,在草台班子里面,演了好多好多戏,《挑滑车》《长坂坡》《花蝴蝶》……很多京剧的戏我也演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今天不知道明天演什么,这完全由“头家”、由观众来点,你还不能说不会。有一次,他们和我们班主说,明天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演《长坂坡》,那时武生就我一个人,可我是昆曲武生啊,京剧我不会。怎么办?那天,专门有个教戏的老师一大早坐船,在船舱里给我讲戏,说人物剧情结构。船到了,我们蹲在地上五分钟吃完饭,赶紧排练做身段。11点多到地方,下午两点半开打,就这么一点时间必须拿下。而且它的地板是搭出来的,拼缝不严实,踩上去是瓤的,穿着厚底容易崴脚,所以特别锻炼人。
这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件事,草台班演出他们有个习俗,就是演出之后会有一个关公拿个大刀裹上红布扫台。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扫台,后来那些老先生说了,因为我们扮演了很多角色,他们已然身死,他们都是故人,既然把他们演活了,那么戏唱完了,理应扫一扫以为安魂。这是因为,我们演员深入研究,心无旁骛地演活了一个人物,观众能看到栩栩如生的古代英雄,这是我们传统戏演员的价值。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我们每个艺术家必须要忘记自我,从始至终全心投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看似古老的传统一直传承至今。
昆曲传承要“照着讲”,也要有勇气“接着讲”
读品:您所开创的“素昆”有不一般的意义。然而,比起母体昆曲,先锋实验见长的“素昆”尚属小众,如何让观众看懂它、欣赏它,乃至拥抱它,可否谈谈您的思考?
柯军:“素昆”的概念更多讲的是探索、是实验、是尝试,是过去没有的。我认为,我除了昆曲传承人的身份之外,我还是个艺术家。艺术家的初心是什么、本性是什么?就是探知未来。不要以为只有科学家是一直在实验,其实艺术家的本能,也是不断做实验,敢于尝试不同的表达方式,以不同的材质去表达不同的内容。所以说,艺术家其实就是不安分的、不安逸的、不断往前走的一群人,有时候甚至表现得不太合群。但在保护遗产方面,我们是要全身心投入的,像“考古”一样做到慎之又慎。不要以为它破了、旧了,就把它扔掉,或者就乱抹,涂上你的色彩,涂上你的观念,涂上你认为的那种“创新”,这些东西全是破坏。所以说,一方面我是一个传承者,一方面我也是一个探险者。
我们一方面需要有耐心照着讲,去做搬运工,也要有勇气接着讲,如果我们不接着讲,只做搬运工的话,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在昆曲里面是空白,是可以跳过的,下一代不会搬我们的东西。
柯军
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著有《说戏》《素昆》《念白》《铭记》等。现任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