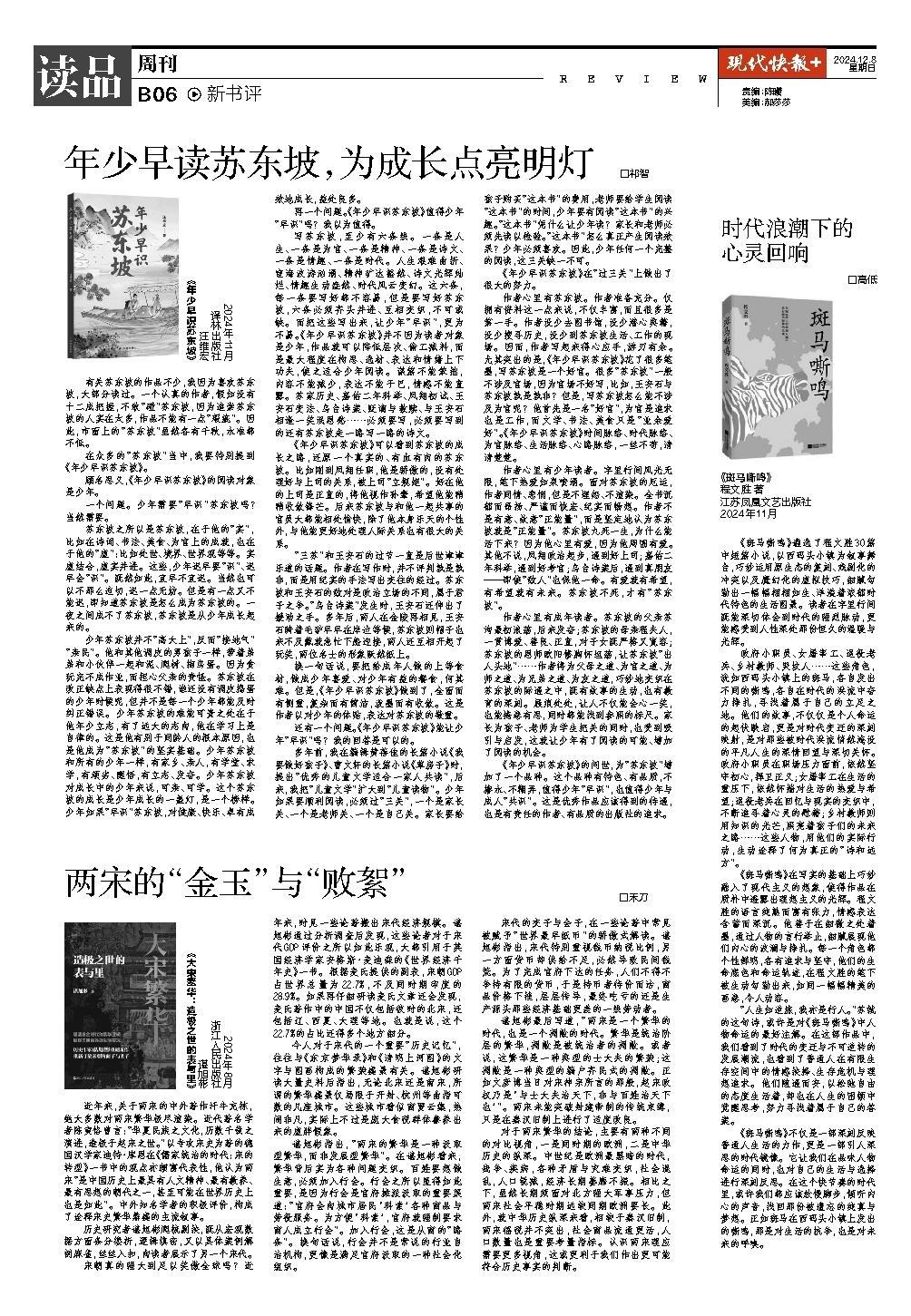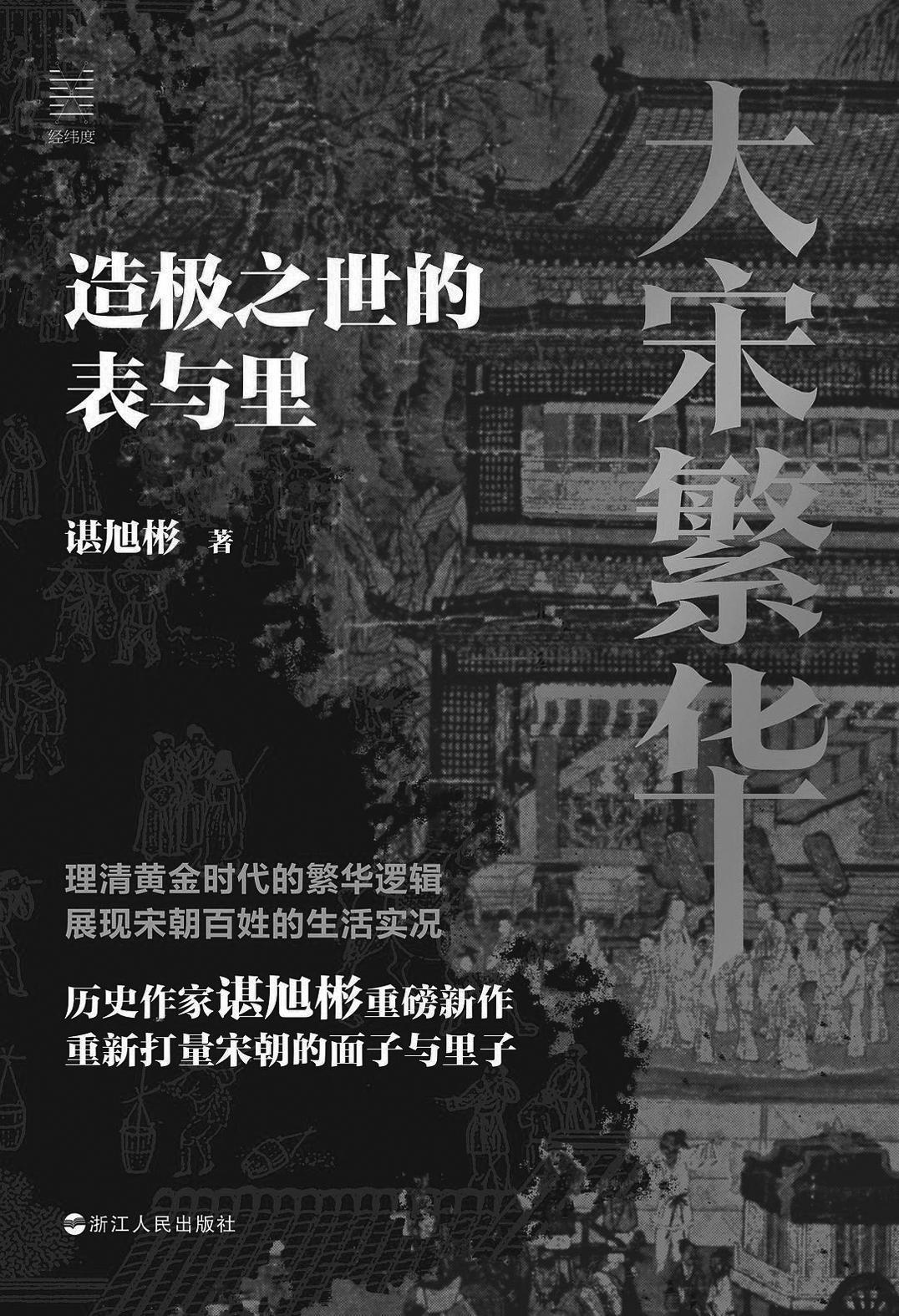□禾刀
近年来,关于两宋的中外著作汗牛充栋,绝大多数对两宋繁华极尽渲染。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以专攻宋史为著的德国汉学家迪特·库恩在《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一书中的观点亦颇富代表性,他认为两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中外知名学者的积极评价,构成了诠释宋史繁华鼎盛的主流叙事。
历史研究者谌旭彬爬梳剔抉,既从宏观数据方面条分缕析,逻辑缜密,又以具体案例解剖麻雀,丝丝入扣,向读者展示了另一个宋代。
宋朝真的强大到足以笑傲全球吗?近年来,时见一些论著搬出宋代经济规模。谌旭彬通过分析调查后发现,这些论者对于宋代GDP评价之所以如此乐观,大都引用于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根据麦氏提供的副表,宋朝GDP占世界总量为22.7%,不及同时期印度的28.9%。如果再仔细研读麦氏文章还会发现,麦氏著作中的中国不仅包括彼时的北宋,还包括辽、西夏、大理等地。也就是说,这个22.7%的占比还得多个地方细分。
今人对于宋代的一个重要“历史记忆”,往往与《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的文字与图画构成的繁荣盛景有关。谌旭彬研读大量史料后指出,无论北宋还是南宋,所谓的繁华盛景仅局限于开封、杭州等曲指可数的几座城市。这些城市看似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实际上不过是庞大食税群体豢养出来的虚胖假象。
谌旭彬指出,“两宋的繁华是一种汲取型繁华,而非发展型繁华”。在谌旭彬看来,繁华背后实为各种问题交织。百姓要想做生意,必须加入行会。行会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行会是官府摊派汲取的重要渠道:“官府会向城市居民‘科索’各种商品与劳役服务。为方便‘科索’,官府就强制要求商人成立行会”。加入行会,这是从商的“路条”。换句话说,行会并不是常说的行业自治机构,更像是满足官府汲取的一种社会化组织。
宋代的交子与会子,在一些论著中常见被赋予“世界最早纸币”的骄傲式解读。谌旭彬指出,宋代特别重视钱币纳税比例,另一方面货币却供给不足,必然导致民间钱荒。为了完成官府下达的任务,人们不得不争持有限的货币,于是持币者待价而沽,商品价格下挫,层层传导,最终吃亏的还是生产源头那些经济基础更差的一线劳动者。
谌旭彬最后写道,“两宋是一个繁华的时代,也是一个凋敝的时代。繁华是统治阶层的繁华,凋敝是被统治者的凋敝。或者说,这繁华是一种典型的士大夫的繁荣;这凋敝是一种典型的编户齐民式的凋敝。正如文彦博当日对宋神宗所言的那般,赵宋政权乃是‘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两宋未能突破封建帝制的传统束缚,只是在秦汉旧制上进行了适度改良。
对于两宋繁华的结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对比视角,一是同时期的欧洲,二是中华历史的纵深。中世纪是欧洲最黑暗的时代,战争、疾病,各种矛盾与灾难交织,社会混乱,人口锐减,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相比之下,虽然长期须面对北方强大军事压力,但两宋社会平稳时期远较同期欧洲要长。此外,就中华历史纵深来看,相较于秦汉旧制,两宋徭税并不突出,社会商品流通更活,人口数量也是重要考量指标。认识两宋理应需要更多视角,这或更利于我们作出更可能符合历史事实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