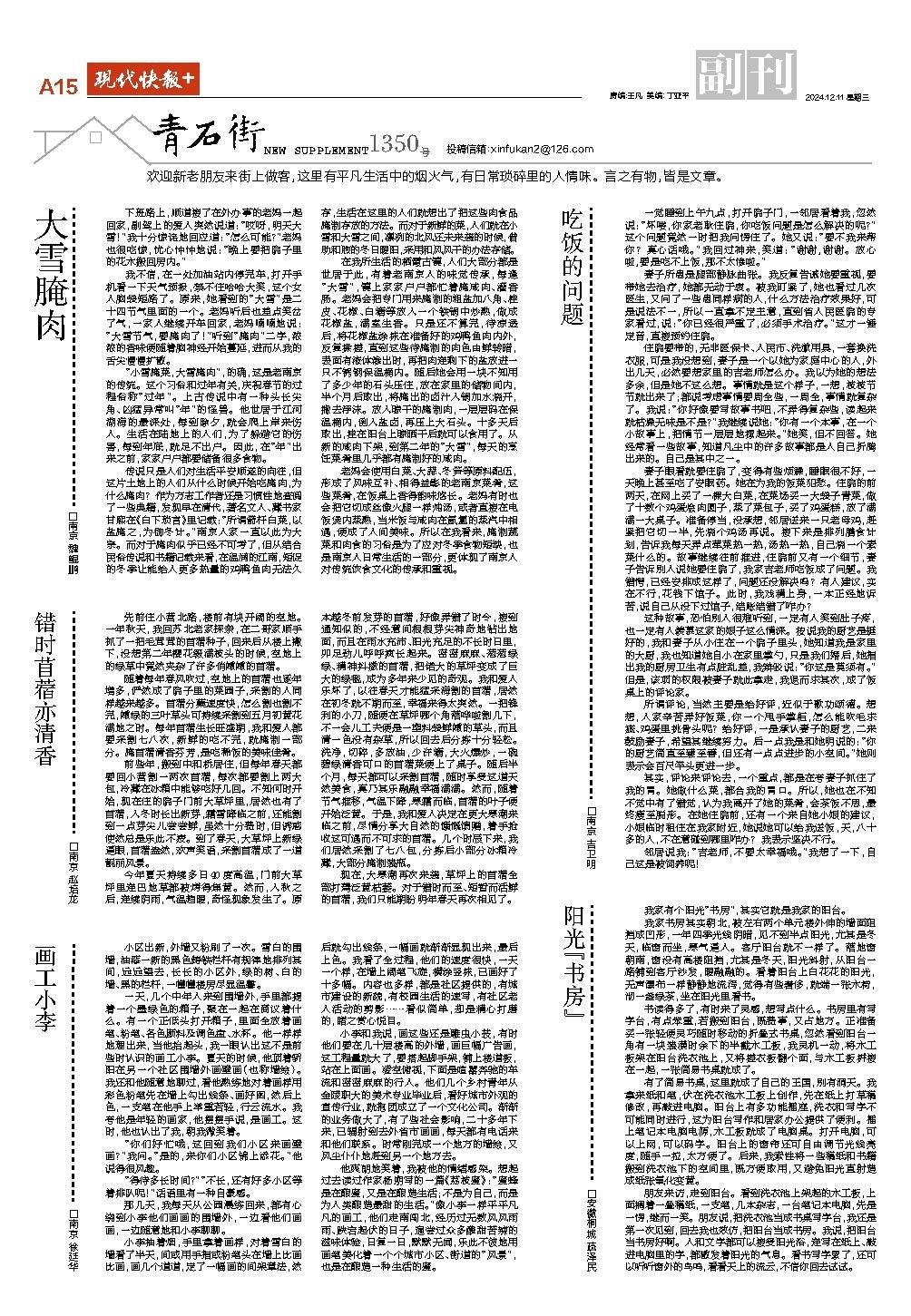□南京 魏鲲鹏
下班路上,顺道接了在外办事的老妈一起回家,副驾上的爱人突然说道:“哎呀,明天大雪!”我十分惊诧地回应道:“怎么可能?”老妈也很吃惊,忧心忡忡地说:“晚上要把院子里的花木搬回房内。”
我不信,在一处加油站内停完车,打开手机看一下天气预报,禁不住哈哈大笑,这个女人脑袋短路了。原来,她看到的“大雪”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一个。老妈听后也差点笑岔了气,一家人继续开车回家,老妈喃喃地说:“大雪节气,要腌肉了!”听到“腌肉”二字,浓浓的香味便随着脑神经开始蔓延,进而从我的舌尖慢慢扩散。
“小雪腌菜,大雪腌肉”,的确,这是老南京的传统。这个习俗和过年有关,庆祝春节的过程俗称“过年”。上古传说中有一种头长尖角、凶猛异常叫“年”的怪兽。他世居于江河湖海的最深处,每到除夕,就会爬上岸来伤人。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为了躲避它的伤害,每到年底,就足不出户。因此,在“年”出来之前,家家户户都要储备很多食物。
传说只是人们对生活平安顺遂的向往,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腌肉,为什么腌肉?作为方志工作者还是习惯性地查阅了一些典籍,发现早在清代,著名文人、藏书家甘熙在《白下琐言》里记载:“所谓箭杆白菜,以盐腌之,为御冬计。”南京人家一直以此为大宗。而对于腌肉似乎已经不可考了,但从结合民俗传说和书籍记载来看,在温润的江南,短促的冬季让能给人更多热量的鸡鸭鱼肉无法久存,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想出了把这些肉食品腌制存放的方法。而对于新鲜的菜,人们就在小雪和大雪之间,凛冽的北风还未来袭的时候,借助和煦的冬日暖阳,采用和风风干的办法存储。
在我所生活的栖霞古镇,人们大部分都是世居于此,有着老南京人的味觉传承,每逢“大雪”,镇上家家户户都忙着腌咸肉、灌香肠。老妈会把专门用来腌制的粗盐加八角、桂皮、花椒、白糖等放入一个铁锅中炒熟,做成花椒盐,满室生香。只是还不算完,待凉透后,将花椒盐涂抹在准备好的鸡鸭鱼肉内外,反复揉搓,直到这些待腌制的肉色由鲜转暗,表面有液体渗出时,再把肉连剩下的盐放进一只不锈钢保温桶内。随后她会用一块不知用了多少年的石头压住,放在家里的储物间内,半个月后取出,将腌出的卤汁入锅加水烧开,撇去浮沫。放入晾干的腌制肉,一层层码在保温桶内,倒入盐卤,再压上大石头。十多天后取出,挂在阳台上晾晒干后就可以食用了。从新的咸肉下架,到第二年的“大雪”,每天的烹饪菜肴里几乎都有腌制好的咸肉。
老妈会使用白菜、大蒜、冬笋等原料配伍,形成了风味互补、相得益彰的老南京菜肴,这些菜肴,在饭桌上香得韵味悠长。老妈有时也会把它切成丝像火腿一样炖汤,或者直接在电饭煲内蒸熟,当米饭与咸肉在氤氲的蒸汽中相遇,便成了人间美味。所以在我看来,腌制蔬菜和肉食的习俗是为了应对冬季食物短缺,也是南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体现了南京人对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