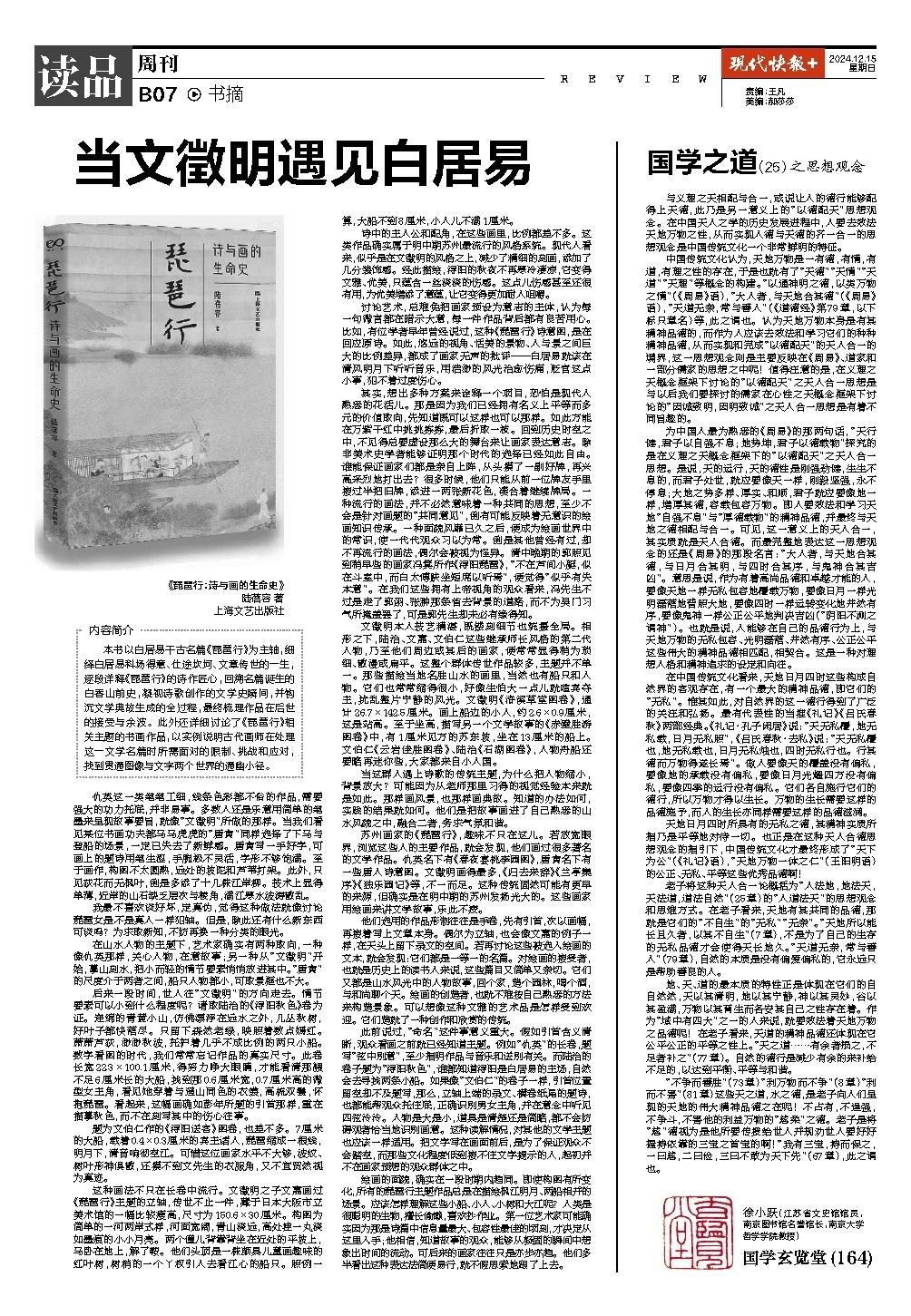内容简介
本书以白居易千古名篇《琵琶行》为主轴,细绎白居易科场得意、仕途坎坷、文章传世的一生,逐段详释《琵琶行》的诗作匠心,回溯名篇诞生的白香山前史,凝视诗歌创作的文学史瞬间,并钩沉文学典故生成的全过程,最终梳理作品在后世的接受与余波。此外还详细讨论了《琵琶行》相关主题的书画作品,以实例说明古代画师在处理这一文学名篇时所需面对的限制、挑战和应对,找到贯通图像与文字两个世界的通幽小径。
仇英这一类笔笔工细,线条色彩都不俗的作品,需要强大的功力托底,并非易事。多数人还是乐意用简单的笔墨来呈现故事要旨,就像“文徵明”所做的那样。当我们看见某位书画功夫都马马虎虎的“唐寅”同样选择了下马与登船的场景,一定已失去了新鲜感。唐寅写一手好字,可画上的题诗用笔生涩,手腕极不灵活,字形不够饱满。至于画作,构图不太圆熟,远处的坡陀和芦苇打架。此外,只见荻花而无枫叶,倒是多添了十几株江岸柳。技术上显得单薄,近岸的山石缺乏层次与棱角,满江寒水波涛散乱。我最不喜欢谈好坏,定真伪,觉得这种做法就像讨论琵琶女是不是真人一样犯轴。但是,除此还有什么新东西可谈吗?为求取新知,不妨再换一种分类的眼光。
在山水人物的主题下,艺术家确实有两种取向,一种像仇英那样,关心人物,在意故事;另一种从“文徵明”开始,摹山刻水,把小而轻的情节要素悄悄放进其中。“唐寅”的尺度介于两者之间,船只人物都小,可取景框也不大。
后来一段时间,世人往“文徵明”的方向走去。情节要素可以小到什么程度呢?请取陆治的《浔阳秋色》卷为证。连绵的青黄小山,仿佛漂浮在远水之外,几丛秋树,好叶子都快落尽。只留下森然老绿,映照着数点嫣红。萧萧芦荻,渺渺秋波,托护着几乎不成比例的两只小船。数字看图的时代,我们常常忘记作品的真实尺寸。此卷长宽22.3×100.1厘米,得努力睁大眼睛,才能看清那艘不足6厘米长的大船,找到那0.6厘米宽,0.7厘米高的微型女主角,看见她穿着与遥山同色的衣裳,高梳双鬟,怀抱琵琶。看起来,这幅画确如彭年所题的引首那样,重在描摹秋色,而不在刻写其中的伤心往事。
题为文伯仁作的《浔阳送客》图卷,也差不多。7厘米的大船,载着0.4×0.3厘米的宾主诸人,琵琶缩成一根线,明月下,清音响彻空江。可惜这位画家水平不大够,波纹、树叶形神俱散,还摸不到文先生的衣服角,又不宜贸然视为真迹。
这种画法不只在长卷中流行。文徵明之子文嘉画过《琵琶行》主题的立轴,传世不止一件,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一幅比较瘦高,尺寸为150.6×30厘米。构图为简单的一河两岸式样,河面宽阔,青山淡远,高处挂一丸淡如墨痕的小小月亮。两个僮儿背靠背坐在近处的平坡上,马卧在地上,解了鞍。他们头顶是一株颇具儿童画趣味的红叶树,树梢的一个丫杈引人去看江心的船只。照例一算,大船不到8厘米,小人儿不满1厘米。
诗中的主人公和配角,在这些画里,比例都差不多。这类作品确实属于明中期苏州最流行的风格系统。现代人看来,似乎是在文徵明的风格之上,减少了精细的刻画,添加了几分装饰感。经此描绘,浔阳的秋夜不再寒冷凄凉,它变得文雅、优美,只蕴含一丝淡淡的伤感。这点儿伤感甚至还很有用,为优美增添了意蕴,让它变得更加耐人咀嚼。
讨论艺术,总难免把画家预设为意志的主体,认为每一句微言都在暗示大意,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有良苦用心。比如,有位学者早年曾经说过,这种《琵琶行》诗意图,是在回应原诗。如此,悠远的视角、恬美的景物、人与景之间巨大的比例差异,都成了画家无声的批评——白居易就该在清风明月下听听音乐,用浩渺的风光治愈伤痛,贬官这点小事,犯不着过度伤心。
其实,想出多种方案来诠释一个项目,恐怕是现代人熟悉的花活儿。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名义上平等而多元的价值取向,先知道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如此方能在万紫千红中挑挑拣拣,最后折取一枝。回到历史时空之中,不见得总要虚设那么大的舞台来让画家表达意志。除非美术史学者能够证明那个时代的选择已经如此自由。谁能保证画家们都是亲自上阵,从头摸了一副好牌,再兴高采烈地打出去?很多时候,他们只能从前一位牌友手里接过半把旧牌,添进一两张新花色,凑合着继续牌局。一种流行的画法,并不必然意味着一种共同的思想,至少不会是针对画题的“共同意见”,倒有可能反映着无意识的绘画知识传承。一种面貌风靡已久之后,便成为绘画世界中的常识,使一代代观众习以为常。倒是其他曾经有过,却不再流行的画法,偶尔会被视为怪异。清中晚期的郭照见到稍早些的画家冯箕所作《浔阳琵琶》,“不在芦间小艇,似在斗室中,而白太傅趺坐短席以听焉”,便觉得“似乎有失本意”。在我们这些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看来,冯先生不过是走了郭诩、张翀那条省去背景的道路,而不为吴门习气所掩盖罢了,可是郭先生却未必有缘得知。
文徵明本人技艺精湛,既镂刻细节也统摄全局。相形之下,陆治、文嘉、文伯仁这些继承师长风格的第二代人物,乃至他们周边或其后的画家,便常常显得稍为琐细、散漫或扁平。这整个群体传世作品较多,主题并不单一。那些描绘当地名胜山水的画里,当然也有船只和人物。它们也常常缩得很小,好像生怕大一点儿就喧宾夺主,扰乱整片宁静的风光。文徵明《浒溪草堂图卷》,通计 26.7×142.5厘米。画上船边的小人,约2.6×0.9厘米,这是站高。至于坐高,描写另一个文学故事的《赤壁胜游图卷》中,有1厘米见方的苏东坡,坐在13厘米的船上。文伯仁《云岩佳胜图卷》、陆治《石湖图卷》,人物舟船还要略再迷你些,大家都来自小人国。
当这群人遇上诗歌的传统主题,为什么把人物缩小,背景放大?可能因为从老师那里习得的视觉经验本来就是如此。那样画风景,也那样画典故。知道的办法如何,实践的结果就如何。他们是把故事画进了自己熟悉的山水风貌之中,融合二者,务求气氛和谐。
苏州画家的《琵琶行》,趣味不只在这儿。若放宽眼界,浏览这些人的主要作品,就会发现,他们画过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仇英名下有《春夜宴桃李园图》,唐寅名下有一些唐人诗意图。文徵明画得最多,《归去来辞》《兰亭集序》《独乐园记》等,不一而足。这种传统固然可能有更早的来源,但确实是在明中期的苏州发扬光大的。这些画家用绘画来讲文学故事,乐此不疲。
他们选用的作品形制往往是手卷,先有引首,次以画幅,再接着写上文章本身。偶尔为立轴,也会像文嘉的例子一样,在天头上留下录文的空间。若再讨论这些被选入绘画的文本,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一等一的名篇。对绘画的接受者,也就是历史上的读书人来说,这些篇目又简单又亲切。它们又都是山水风光中的人物故事,回个家,造个园林,喝个酒,与和尚聊个天。绘画的创造者,也就不难按自己熟悉的方法来构造景象。可以想像这种文雅的艺术品是怎样受到欢迎。它们造就了一种创作和欣赏的传统。
此前说过,“命名”这件事意义重大。假如引首含义清晰,观众看画之前就已经知道主题。例如“仇英”的长卷,题写“弦中别意”,至少指明作品与音乐和送别有关。而陆治的卷子题为“浔阳秋色”,谁都知道浔阳是白居易的主场,自然会去寻找两条小船。如果像“文伯仁”的卷子一样,引首位置留空却不及题写,那么,立轴上端的录文、横卷纸尾的题诗,也都能帮观众托住底,正确识别男女主角,并在意念中听见四弦泠泠。人物是大是小,道具是清楚还是简略,都不会妨碍观者恰当地识别画意。这种读解情况,对其他的文学主题也应该一样适用。把文字写在画面前后,是为了保证观众不会踏空,而那些文化程度低到接不住文字提示的人,起初并不在画家预想的观众群体之中。
绘画的面貌,确实在一段时期内趋同。即使构图有所变化,所有的琵琶行主题作品总是在描绘枫江明月、两船相并的场景。应该怎样理解这些小船、小人、小树和大江呢?人类是很聪明的生物,擅长偷懒,喜欢抄作业。第一位艺术家可能确实因为那是诗篇中信息量最大、包容性最佳的顷刻,才决定从这里入手;他相信,知道故事的观众,能够从凝固的瞬间中想象出时间的流动。可后来的画家往往只是亦步亦趋。他们多半看出这种表达法简便易行,就不假思索地跟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