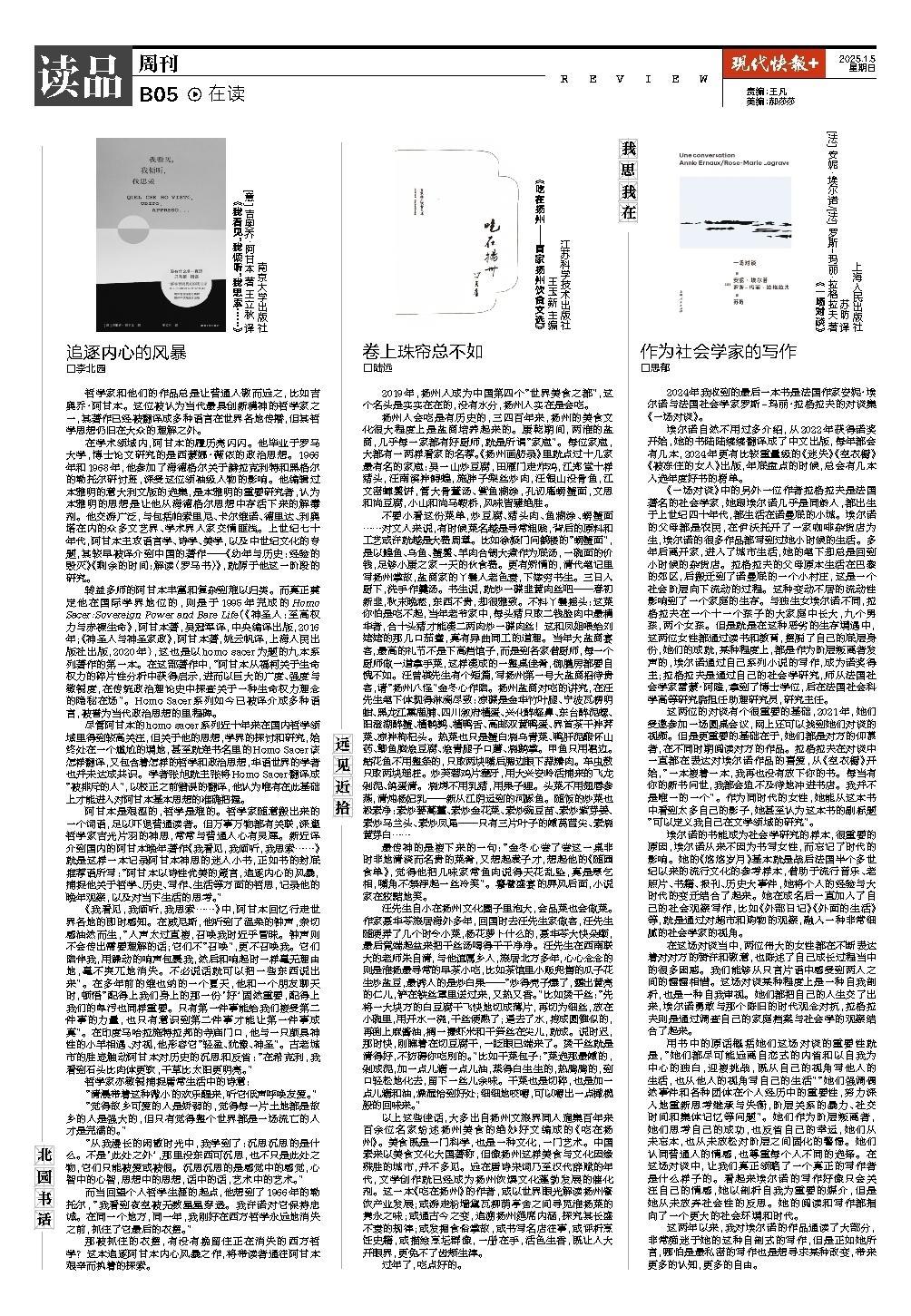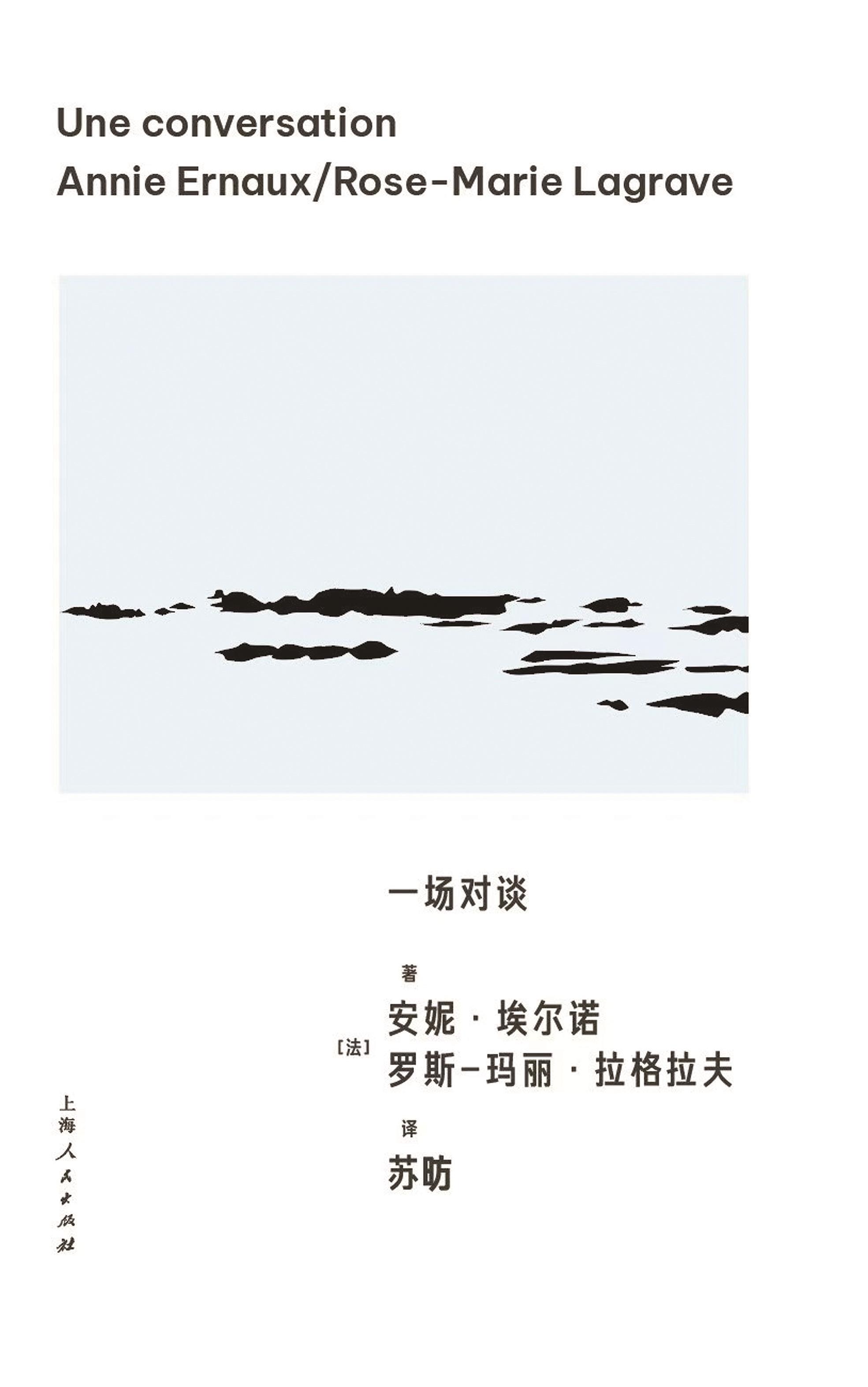□思郁
2024年我收到的最后一本书是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与法国社会学家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的对谈集《一场对谈》。
埃尔诺自然不用过多介绍,从2022年获得诺奖开始,她的书陆陆续续翻译成了中文出版,每年都会有几本,2024年更有比较重量级的《迷失》《空衣橱》《被冻住的女人》出版,年底盘点的时候,总会有几本入选年度好书的榜单。
《一场对谈》中的另外一位作者拉格拉夫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她跟埃尔诺几乎是同龄人,都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都生活在诺曼底的小城。埃尔诺的父母都是农民,在伊沃托开了一家咖啡杂货店为生,埃尔诺的很多作品都写到过她小时候的生活。多年后离开家,进入了城市生活,她的笔下却总是回到小时候的杂货店。拉格拉夫的父母原本生活在巴黎的郊区,后搬迁到了诺曼底的一个小村庄,这是一个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过程。这种变动不居的流动性影响到了一个家庭的生存。与独生女埃尔诺不同,拉格拉夫在一个十一个孩子的大家庭中长大,九个男孩,两个女孩。但是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生存境遇中,这两位女性都通过读书和教育,摆脱了自己的底层身份,她们的成就,某种程度上,都是作为阶层叛离者发声的,埃尔诺通过自己系列小说的写作,成为诺奖得主;拉格拉夫是通过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师从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拿到了博士学位,后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助理研究员,研究主任。
这两位的对谈有个很重要的基础,2021年,她们受邀参加一场圆桌会议,网上还可以找到她们对谈的视频。但是更重要的基础在于,她们都是对方的仰慕者,在不同时期阅读对方的作品。拉格拉夫在对谈中一直都在表达对埃尔诺作品的喜爱,从《空衣橱》开始,“一本接着一本,我再也没有放下你的书。每当有你的新书问世,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冲进书店。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作为同时代的女性,她能从这本书中看到太多自己的影子,她甚至认为这本书的副标题“可以定义我自己在文学领域的研究”。
埃尔诺的书能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样本,很重要的原因,埃尔诺从来不因为书写女性,而忘记了时代的影响。她的《悠悠岁月》基本就是战后法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流行文化的参考样本,借助于流行音乐、老照片、书籍、报刊、历史大事件,她将个人的经验与大时代的变迁结合了起来。她在成名后一直加入了自己的社会观察写作,比如《外部日记》《外面的生活》等,就是通过对超市和购物的观察,融入一种非常细腻的社会学家的视角。
在这场对谈当中,两位伟大的女性都在不断表达着对对方的赞许和敬意,也陈述了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很多困惑。我们能够从只言片语中感受到两人之间的惺惺相惜。这场对谈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剖析,也是一种自我审视。她们都把自己的人生交了出来,埃尔诺勇敢与那个陈旧的时代观念对抗,拉格拉夫则是通过调查自己的家庭档案与社会学的观察结合了起来。
用书中的原话概括她们这场对谈的重要性就是,“她们都尽可能远离自恋式的内省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白,迎接挑战,既从自己的视角写他人的生活,也从他人的视角写自己的生活”“她们强调偶然事件和各种团体在个人经历中的重要性,努力深入地重新思考继承与失衡,阶层关系的暴力、社交时间和集体记忆等问题”。她们作为阶层叛离者,她们思考自己的成功,也反省自己的幸运,她们从未忘本,也从未放松对阶层之间固化的警惕。她们认同普通人的情感,也尊重每个人不同的选择。在这场对谈中,让我们真正领略了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是什么样子的。看起来埃尔诺的写作好像只会关注自己的情感,她以剖析自我为重要的媒介,但是她从未放弃社会性的反思。她的阅读和写作都指向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和时代。
这两年以来,我对埃尔诺的作品通读了大部分,非常痴迷于她的这种自剖式的写作,但是正如她所言,哪怕是最私密的写作也是想寻求某种改变,带来更多的认知,更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