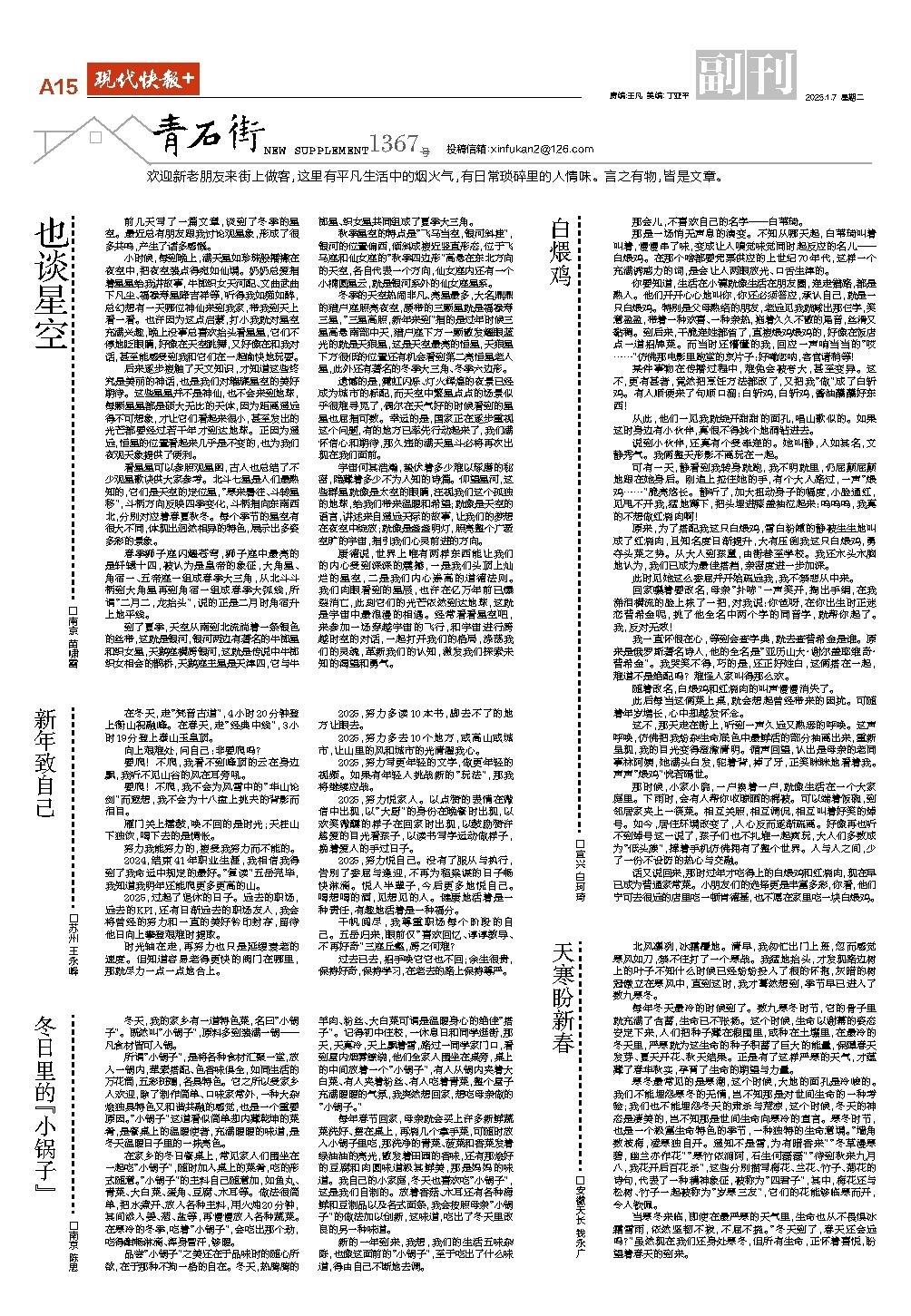□宜兴 白珂琦
那会儿,不喜欢自己的名字——白苇琦。
那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演变。不知从哪天起,白苇琦叫着叫着,慢慢串了味,变成让人嗅觉味觉同时起反应的名儿——白煨鸡。在那个啥都要凭票供应的上世纪70年代,这样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词,是会让人两眼放光、口舌生津的。
你要知道,生活在小镇就像生活在朋友圈,连走错路,都是熟人。他们开开心心地叫你,你还必须答应,承认自己,就是一只白煨鸡。特别是父母熟络的朋友,老远见我就喊出那仨字,笑意盈盈,带着一种欢喜、一种亲热,拖着久久不散的尾音,丝滑又黏稠。到后来,干脆连姓都省了,直接煨鸡煨鸡的,好像在饭店点一道招牌菜。而当时还懵懂的我,回应一声响当当的“哎……”仿佛那电影里跑堂的京片子:好嘞您呐,客官请稍等!
某件事物在传播过程中,难免会被夸大,甚至变异。这不,更有甚者,竟然把烹饪方法都改了,又把我“做”成了白斩鸡。有人顺便来了句顺口溜:白斩鸡,白斩鸡,酱油蘸蘸好东西!
从此,他们一见我就绽开甜甜的面孔,唱山歌似的。如果这时身边有小伙伴,真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说到小伙伴,还真有个受牵连的。她叫静,人如其名,文静秀气。我俩整天形影不离玩在一起。
可有一天,静看到我转身就跑,我不明就里,仍屁颠屁颠地跟在她身后。刚追上拉住她的手,有个大人路过,一声“煨鸡……”脆亮悠长。静听了,加大扭动身子的幅度,小脸通红,见甩不开我,猛地蹲下,把头埋进膝盖抽泣起来:呜呜呜,我真的不想做红烧肉啊!
原来,为了搭配我这只白煨鸡,雪白粉嫩的静被生生地叫成了红烧肉,且知名度日渐提升,大有压倒我这只白煨鸡,勇夺头菜之势。从大人到孩童,由街巷至学校。我还木头木脑地认为,我们已成为最佳搭档,亲密度进一步加深。
此时见她这么委屈并开始疏远我,我不禁悲从中来。
回家嚷着要改名,母亲“扑哧”一声笑开,掏出手绢,在我涕泪横流的脸上抹了一把,对我说:你爸呀,在你出生时正迷恋普希金呢,挑了他全名中两个字的同音字,就帮你起了。我,反对无效!
我一直怀恨在心,等到会查字典,就去查普希金是谁。原来是俄罗斯著名诗人,他的全名是“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我哭笑不得,巧的是,还正好姓白,这俩搭在一起,难道不是绝配吗?难怪人家叫得那么欢。
随着改名,白煨鸡和红烧肉的叫声慢慢消失了。
此后每当这俩菜上桌,就会想起曾经带来的困扰。可随着年岁增长,心中却越发怀念。
这不,那天走在街上,听到一声久远又熟悉的呼唤。这声呼唤,仿佛把我纷杂生命底色中最鲜活的部分抽离出来,重新呈现,我的目光变得澄澈清明。循声回望,认出是母亲的老同事林阿姨,她满头白发,驼着背,掉了牙,正笑眯眯地看着我。声声“煨鸡”恍若隔世。
那时候,小家小院,一户挨着一户,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下雨时,会有人帮你收晾晒的棉被。可以端着饭碗,到邻居家夹上一筷菜。相互关照,相互调侃,相互叫着好笑的绰号。如今,居住环境改变了,人心反而逐渐疏离。好像再也听不到绰号这一说了,孩子们也不扎堆一起疯玩,大人们多数成为“低头族”,捧着手机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人与人之间,少了一份不设防的热心与交融。
话又说回来,那时过年才吃得上的白煨鸡和红烧肉,现在早已成为普通家常菜。小朋友们的选择更是丰富多彩,你看,他们宁可去很远的店里吃一顿肯德基,也不愿在家里吃一块白煨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