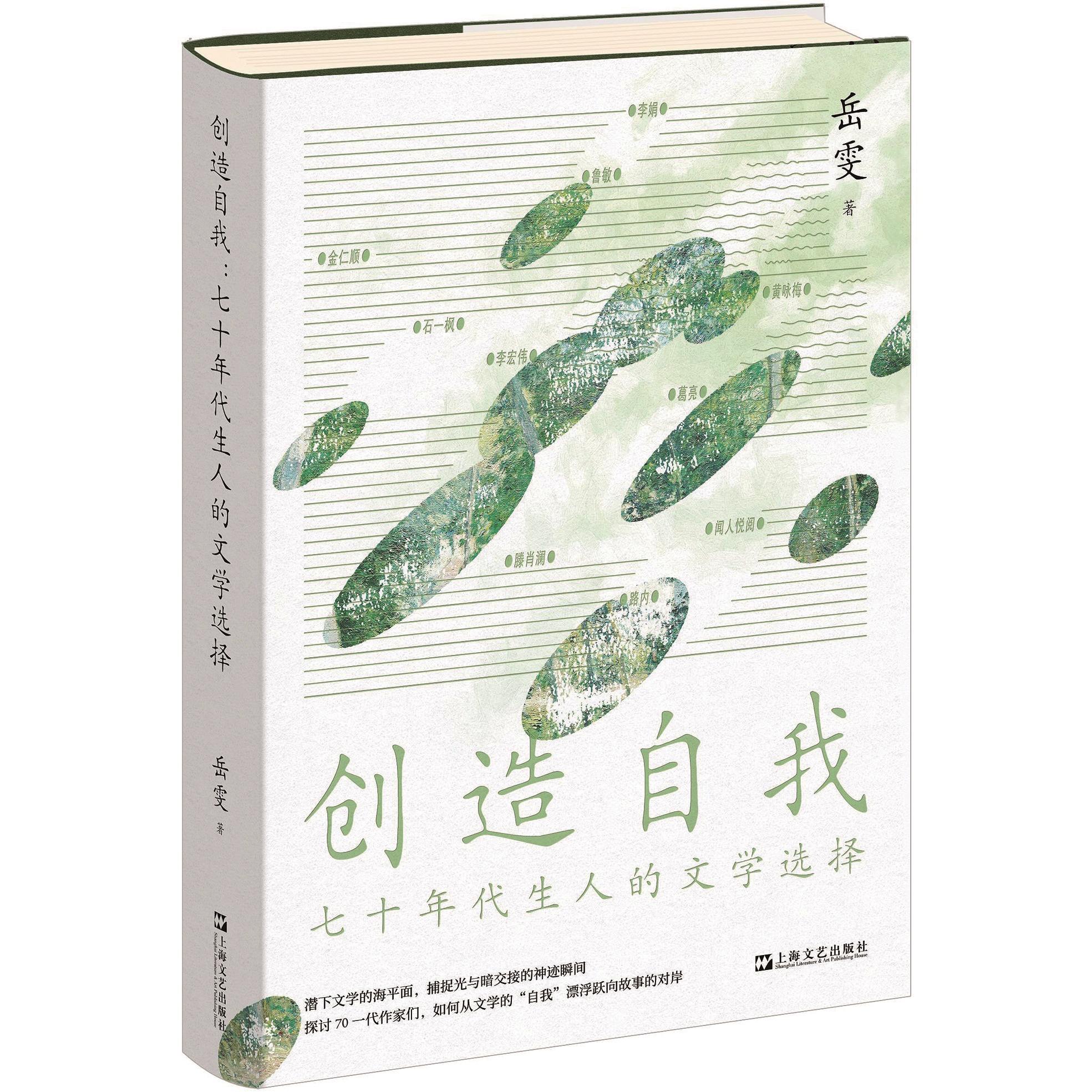在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眼中,岳雯是一个天生的文学人,也是一个天生的批评家。
从业十多年,她完成了以灵气显露文坛到成为批评界中坚力量的转身。在新近出版的评论新著《创造自我:七十年代生人的文学选择》中,她细读李娟、鲁敏、葛亮等10位作家的代表作品,潜下文学的海平面,探讨70后作家们如何从文学的“自我”漂浮跃向故事的对岸,从而完成对人物与时代的理解。
创造自我的又岂止是她笔下的作家们?创造自我亦是岳雯的“批评观”。文学于她而言,是身体皮肤,是度过一生的生活方式。尽管媒体的迭代已将主流注意力转移给视频,但她仍然乐意从文字中获取她所要的一切。读了不计其数的小说,写了不计其数的评论,她始终遵循这样的批评路径——以熔铸个人生活经验的形式谈论文学,表达我们对于世界的体认与判断,不以“论者”“笔者”的心态来写批评文章,不回避自己的感性存在,“因为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正是以感性而著称,性情是以一个人的才华、禀赋、经验、学识、智慧等熔铸起来的。”
想来,如今正当红的DeepSeek是否也正因为缺乏这份文学的性情,而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作家或者批评家?讽刺的是,当岳雯尝试着让DeepSeek回答这个提问时,它自己也洞悉了这一点。
不过,当我们谈论文学的时候,过分强调人在AI面前的优越性,又有多大意义呢?真正让岳雯感到快乐的还是那些不必言说、心领神会的文学时刻,“当我看完一本小说,一天正好到了落日时分。北方的太阳温和无言地挂在窗外,内心涌动着既充盈饱满又怅然若失的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文学时刻吧。”
这样的时刻有多美妙,DeepSeek永远也不会懂。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凡
文字在心灵之湖里激起的震感之深,影像不能达到
读品:李敬泽老师说有些人自认为爱好文学,但其实与文学天性不合。文学需要对人性、对世界之微妙苍茫有深入的领悟力。他称赞你是天生的文学人。所以,第一个问题,先聊聊你的文学天性吧。你的这种天性开启于何时?
岳雯:我理解,你的“天性说”其实是在追溯一个人的来路,或者说,给人画像时落下的第一滴墨。这个问题建立在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基础上,即我们倾向于认为文学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是植根于人的天性的,是某种天赋的外在显现。许多作家也为这一“神话”添砖加瓦——想想看,有多少作家把开启阅读和写作的道路描述得简直比他们写的小说还精彩。我们从后设的视角出发,认定一个“起源”,但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套“说辞”,就像敬泽老师的评价也不过是善意的、鼓励后学好好努力的“说辞”而已,当不得真的。
至于我自己,谈不上什么天性,只是在一个相对匮乏、拘谨的年代将文学当作度过生活的方法并延续至今罢了。说白了,文学非常适合我这样喜欢独处的人“自己和自己玩儿”。它成本足够低,一本书就可以将喧嚣的世界关在你的心灵之外,又足够丰富和迷人,对于人的心智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天性,我觉得文学适合那些以语言文字的方式想象世界的人。时至今日,即使短视频像瀑布一样流淌、随处可见,我仍然不适应以影像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这是我的缺憾。影像的逻辑和文字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影像是空间化的,直接而鲜活,在一个瞬间,你需要抓住层层叠加的不同信息要素并予以综合。语言文字是历时性的,更抽象,反而在我的心灵之湖里激起的震感之深,是影像所不能达到的。这里没有孰优孰劣的意思,完全与个人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关。在数智文明取代印刷文明的今天,或许很多人不会再将文学当作度过一生的方式了,但我仍然为此感到庆幸,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度过这一生的方式。
读品:你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比喻,“文学之于我,不是一堆语言材料,它更像是身体发肤,文学是使‘我’成为‘我’的那个
最要紧的东西。”回顾你的文学世界,请你阐释一下,文学怎样使“我”成为“我”?
岳雯:自我的问题始终是现代性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仍然认为,绝大多数人的自我是未完成的,或者更绝对一点说,人的一生,其实是寻找自我、塑造自我的过程。这就涉及对自我的理解。没有什么单一的本质意义上的自我,自我一定是在某种关系性网络中形成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自我与宇宙的关系。而这一切都是文学可以教会我们的事。
就像读小说,我们深入到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处境之中,理解他的所思所想,理解他何以如此。当我们进入到无数个人的生活中去,进入到他们的心灵中去,你会发现,你的视域大大拓宽了,你不会那么狭隘,上下左右只看到自己。不同的人,尽管他们都在二次元,是“纸片人”,都构成你生命的一部分;无数双眼睛,都在和你一起看这个世界,生命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也是文学的功能之一,让我们领会多样性的意义。
文学批评是对作家的解谜,也是与他们的“较量”
读品:从一个文学人成为一个批评家,是你的既定目标吗?你当初为什么会作出文学批评这样的“文学选择”?
岳雯:最近比较流行“我命由我不由天”,对吧?但其实流行反映的是我们的匮乏,越是缺什么就越嚷嚷得厉害。在我看来,这世界上的事你能决定的部分很少,即使你一生的志向追求,有时候都不是你主动选择的结果。反正我是这样的悲观主义者。这么说吧,不是我作出了文学批评这样的文学选择,而是职业塑造了我。我毕业后到中国作协创研部工作,这个工作岗位对人的要求就是要看大量的文学作品,做出判断,把握文学乃至文化的大势,就这样,被工作推动着,就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我的意思是,命运恰好把我掷入文化生产的机制的一环,那就沿着画好的棋盘,一格一格往下走就是了。
读品:我读到同龄人金理写你的一篇文章,说“我们从事文学批评,主要原因也是热爱,出于生命和创造的内在欲求。”文学批评对你的吸引力是什么?
岳雯:金理说的热爱没有错,就是因为热爱,所以不会视职业为苦役,反而有点乐在其中的意思,这是我十分幸运的地方。时至今日,还在写评论,一方面是因为,我也不是多么有规划,多么积极主动展开个人选择的人;另外一方面,就像你说的,文学批评对我还有吸引力。我着迷于在作家所构筑的感性世界里寻找到那些并未显现的东西,就像解谜;我愿意在文本中和他们展开思想上、审美上的对话,乃至于心智上的较量。在我看来,文学批评是思想体操,也是花样滑冰。
读品:你新出的这本评论集书名是《创造自我》,你在文中写道,70后作家以自我表达和自我追求为首义。而我看到你的批评观是:“在沉默中求真理,于抒情中听惊雷,分析爱,创造自我,无尽无涯”,也有创造自我这个关键词。请你做一个解读。
岳雯: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援引王尔德的一段话,他说,“这才是最高层次批评的本质:是对自我灵魂的记录。它比历史更精彩,因为它只涉及自己。它比哲学更可喜,因为它的主题具体而不抽象、真切而不含糊。它是自传的唯一文明形式,因为它处理的不是事件,而是个人生活的思想;不是生活中行为或环境的有形事件,而是心灵的精神气氛和想象激情。”本质意义上说,作家的自我和批评家的自我,其实是一回事,它不是本来就有的,是时刻处于运动中的。批评观,说起来是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当《北京文艺评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我的批评观时,我的目光恰好停留在这些年我出的几本书上:《沉默所在》《抒情的张力》《爱的分析》《未尽集》《创造自我》,单从书名看,似乎也构成了我的人物画像。是的,我们总是在无意识中写出自己的命运。
面对AI,批评家们不如保持沉默
读品:你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沉默所在》的文章,谈到了你批评生涯中曾经的沉默。你说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变得不再沉默,愿意为孩子,乃至更多的人挑选值得读的书。现在还会渴望沉默吗?
岳雯:怎么说呢,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鲁迅先生早就给出了答案——“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很充实,当我开口说话,就感到了空虚”。于我而言,沉默,一方面是面对文学时近乎本能的敬畏,另外一方面,其实缘于我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开口说话。到现在仍然如此。是的,这也是天性的一部分,笨拙、怯懦、惶惑……
你知道吗?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刻是在文学中心领神会,什么都不必说的时刻。最近一次的经验,当我看完一本小说,一天正好到了落日时分。北方的太阳温和无言地挂在窗外,内心涌动着既充盈饱满又怅然若失的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文学时刻吧。是的,当我开口说话,包括现在坐在这里絮絮叨叨回答你的问题时,我充满了对自身的厌弃。我羡慕那些有强大表达欲望和表达才华的人,但是我也清晰地意识到我永远不会成为这样的人。我渴望沉默。就是这么精神分裂。
读品:我注意到,你从事文学批评非常强调的一点是表达个人的生命体验。你说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是以感性而著称。性情是以一个人的才华、禀赋、经验、学识、智慧等等熔铸起来的。你总结的性情,似乎是文学不可能被DeepSeek这样的AI打败的利器。想听听你的观点。
岳雯:关于“性情”之于文学批评的意义,我始终相信这是人类面对技术浪潮时最后的堡垒,也是文学永不褪色的光芒所在。当批评家们纷纷披上“论者”的铠甲,用“笔者认为”的盾牌遮挡肉身时,文字便成了无主的游魂——精准、周全却失温。这让我想起萨义德所说的“业余者精神”:真正的批评不是职业化的技术表演,而是以完整的生命经验介入文本,用血肉之躯感知字里行间的震颤。AI可以模仿逻辑的链条、知识的图谱甚至修辞的韵律,但它永远无法复刻“性情”——那是独属于人类的精神指纹,由无数幽微的瞬间熔铸而成。这些经验如同隐形的墨汁,早已渗透进批评的笔尖。有人将性情误解为情绪的泛滥,实则不然。性情是批评家以全部感官为网,打捞文本与生活共振的频率。文学批评的“高级感”,恰恰在于它必须携带个体的生命密码。当DeepSeek们用数据洪流冲刷文学时,人类批评家要做的,恰恰是更彻底地袒露自己的脆弱与炽热——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凡尼亚舅舅,在星空下呐喊:“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度过一连串漫长的黑夜,耐心地忍受命运所给予的考验。”这呐喊本身,就是文学不死的证明。
以上是DeepSeek替我做出的回答,是不是令人悚然?如果我不作说明,真的能区分出是我还是AI在回答吗?更令人悚然的是它回答的内容,太符合我们这些以文字为业的人为我们的存在找的合法性了。目力所及,我的同行们几乎都是这么说的。过分强调人这么一个脆弱、有限的主体在AI面前的优越性,已经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了。讽刺的是,AI也洞悉了这一点。当AI可以无限沉浸于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并运用一切它所能掌握并不断进化的方法使用这些巨大财富时,它必然会超越我们大部分人。与它合作?如果我们的合作者通晓的远多于我们,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称自己是合作吗?我们到底能贡献多少智慧?我说了,我是悲观主义者,我没那么乐观,我也没那么信任所谓的生命密码就能让我们的文字活下来。那么,就保持沉默吧,像它说的,先活下去,度过漫长黑夜,忍受命运的考验,看看这个世界还会发生什么?
岳雯
《文艺报》社副总编辑。著有《创造自我》《未尽集》《爱的分析》《沉默所在》《抒情的张力》等。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文学报》《钟山》等报刊优秀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