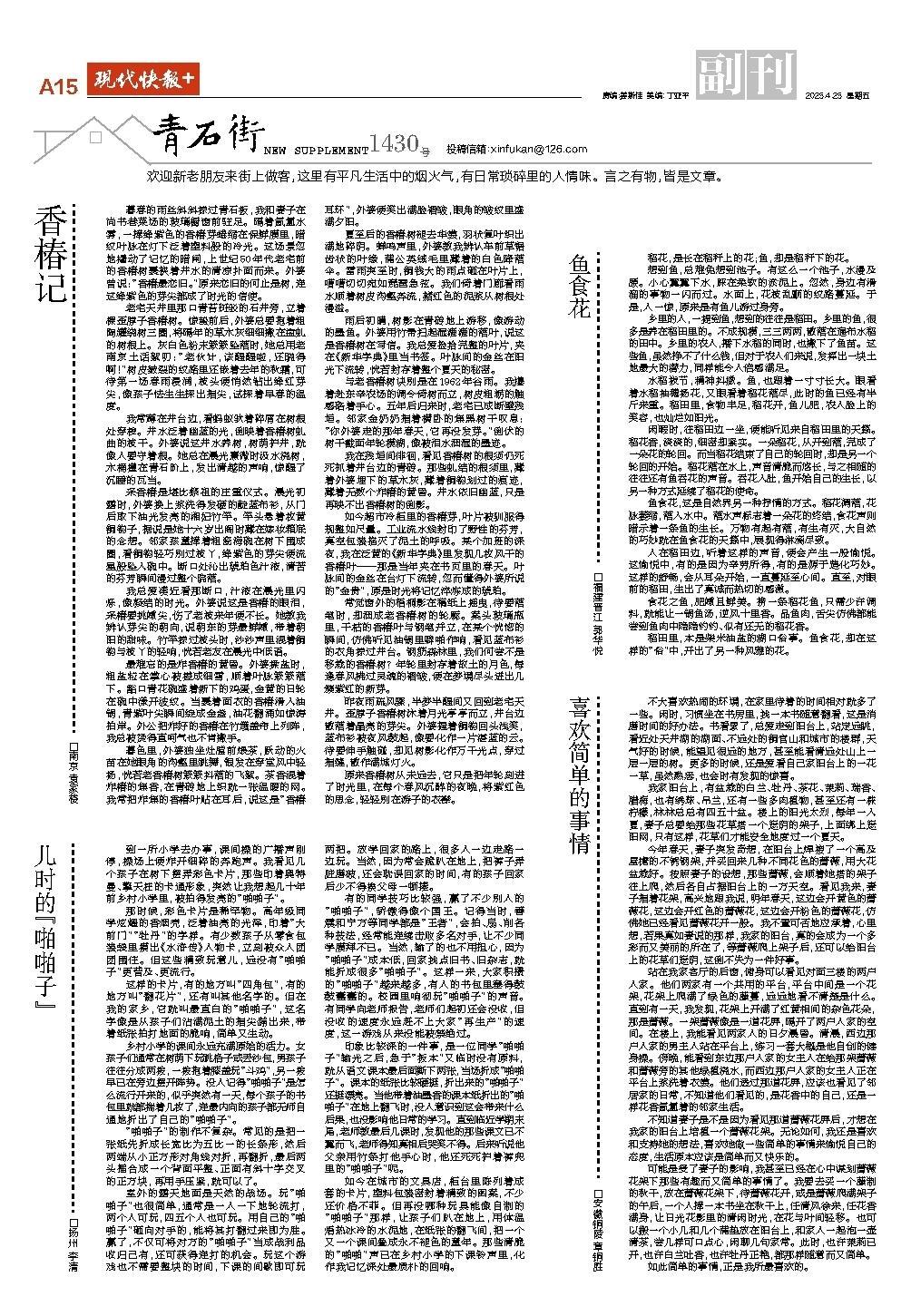□南京 袁家楼
暮春的雨丝斜斜掠过青石板,我和妻子在尚书巷菜场的玻璃橱窗前驻足。隔着氤氲水雾,一捧绛紫色的香椿芽蜷缩在保鲜膜里,暗纹叶脉在灯下泛着塑料般的冷光。这场景忽地撬动了记忆的暗闸,上世纪50年代老宅前的香椿树裹挟着井水的清凉扑面而来。外婆曾说:“香椿最恋旧。”原来恋旧的何止是树,连这绛紫色的芽尖都成了时光的信使。
老宅天井里那口青苔斑驳的石井旁,立着棵歪脖子香椿树。惊蛰前后,外婆总要抱着粗陶罐绕树三圈,将隔年的草木灰细细撒在盘虬的树根上。灰白色粉末簌簌坠落时,她总用老南京土话絮叨:“老伙计,该醒醒啦,还晓得啊!”树皮皴裂的纹路里还嵌着去年的秋霜,可待第一场春雨浸润,枝头便悄然钻出绛红芽尖,像孩子怯生生探出指尖,试探着早春的温度。
我常蹲在井台边,看蚂蚁驮着碎屑在树根处穿梭。井水泛着幽蓝的光,倒映着香椿树虬曲的枝干。外婆说这井水养树,树荫护井,就像人要守着根。她总在晨光熹微时汲水浇树,木桶撞在青石阶上,发出清越的声响,惊醒了沉睡的瓦当。
采香椿是堪比祭祖的庄重仪式。晨光初露时,外婆换上浆洗得发硬的靛蓝布衫,从门后取下油光发亮的湘妃竹竿。竿头悬着枚黄铜钩子,据说是她十六岁出阁时藏在嫁妆箱底的念想。邻家孩童捧着粗瓷海碗在树下围成圈,看铜钩轻巧别过枝丫,绛紫色的芽尖便流星般坠入碗中。断口处沁出琥珀色汁液,清苦的芬芳瞬间漫过整个院落。
我总爱凑近看那断口,汁液在晨光里闪烁,像凝结的时光。外婆说这是香椿的眼泪,采椿要挑嫩尖,伤了老枝来年便不长。她教我辨认芽尖的朝向,说朝东的芽最鲜嫩,带着朝阳的甜味。竹竿掠过枝头时,沙沙声里混着铜钩与枝丫的轻响,恍若老友在晨光中低语。
最难忘的是炸香椿的黄昏。外婆揉盐时,粗盐粒在掌心被搓成细雪,顺着叶脉簌簌落下。豁口青花碗盛着新下的鸡蛋,金黄的日轮在碗中漾开波纹。当裹着面衣的香椿滑入油锅,青紫叶尖瞬间绽成金盏,油花翻涌如惊涛拍岸。外公把炸好的香椿在竹篾盖帘上列阵,我总被烫得直呵气也不肯撒手。
暮色里,外婆独坐灶膛前煨茶,跃动的火苗在她眼角的沟壑里跳舞,银发在穿堂风中轻扬,恍若老香椿树簌簌抖落的飞絮。茶香混着炸椿的焦香,在青砖地上织就一张温暖的网。我常把炸焦的香椿叶贴在耳后,说这是“香椿耳环”,外婆便笑出满脸褶皱,眼角的皱纹里盛满夕阳。
夏至后的香椿树褪去华裳,羽状复叶织出满地碎阴。蝉鸣声里,外婆教我辨认车前草锯齿状的叶缘,蒲公英绒毛里藏着的白色降落伞。雷雨突至时,铜钱大的雨点砸在叶片上,嘈嘈切切宛如琵琶急弦。我们倚着门廊看雨水顺着树皮沟壑奔流,赭红色的泥浆从树根处漫溢。
雨后初晴,树影在青砖地上游移,像游动的墨鱼。外婆用竹帚扫起湿漉漉的落叶,说这是香椿树在写信。我总爱捡拾完整的叶片,夹在《新华字典》里当书签。叶脉间的金丝在阳光下流转,恍若封存着整个夏天的秘密。
与老香椿树诀别是在1962年谷雨。我攥着赴东辛农场的调令倚树而立,树皮粗粝的触感硌着手心。五年后归来时,老宅已成断壁残垣。邻家金奶奶指着横卧的焦黑树干叹息:“你外婆走的那年春天,它再没发芽。”倒伏的树干截面年轮模糊,像被泪水洇湿的墨迹。
我在残垣间徘徊,看见香椿树的根须仍死死抓着井台边的青砖。那些虬结的根须里,藏着外婆埋下的草木灰,藏着铜钩划过的痕迹,藏着无数个炸椿的黄昏。井水依旧幽蓝,只是再映不出香椿树的倒影。
如今超市冷柜里的香椿芽,叶片被驯服得规整如尺量。工业流水线封印了野性的芬芳,真空包装掐灭了泥土的呼吸。某个加班的深夜,我在泛黄的《新华字典》里发现几枚风干的香椿叶——那是当年夹在书页里的春天。叶脉间的金丝在台灯下流转,忽而懂得外婆所说的“金贵”,原是时光将记忆淬炼成的琥珀。
常觉窗外的梧桐影在稿纸上摇曳,待要落笔时,却洇成老香椿树的轮廓。案头玻璃瓶里,干枯的香椿叶与钢笔并立,在某个恍惚的瞬间,仿佛听见油锅里噼啪作响,看见蓝布衫的衣角掠过井台。钢筋森林里,我们何尝不是移栽的香椿树?年轮里封存着故土的月色,每逢春风拂过灵魂的褶皱,便在梦境尽头迸出几簇紫红的新芽。
昨夜雨疏风骤,半梦半醒间又回到老宅天井。歪脖子香椿树沐着月光亭亭而立,井台边散落着晶亮的芽尖。外婆握着铜钩回头浅笑,蓝布衫被夜风鼓起,像要化作一片湛蓝的云。待要伸手触碰,却见树影化作万千光点,穿过指缝,散作满城灯火。
原来香椿树从未远去,它只是把年轮刻进了时光里,在每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将紫红色的思念,轻轻别在游子的衣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