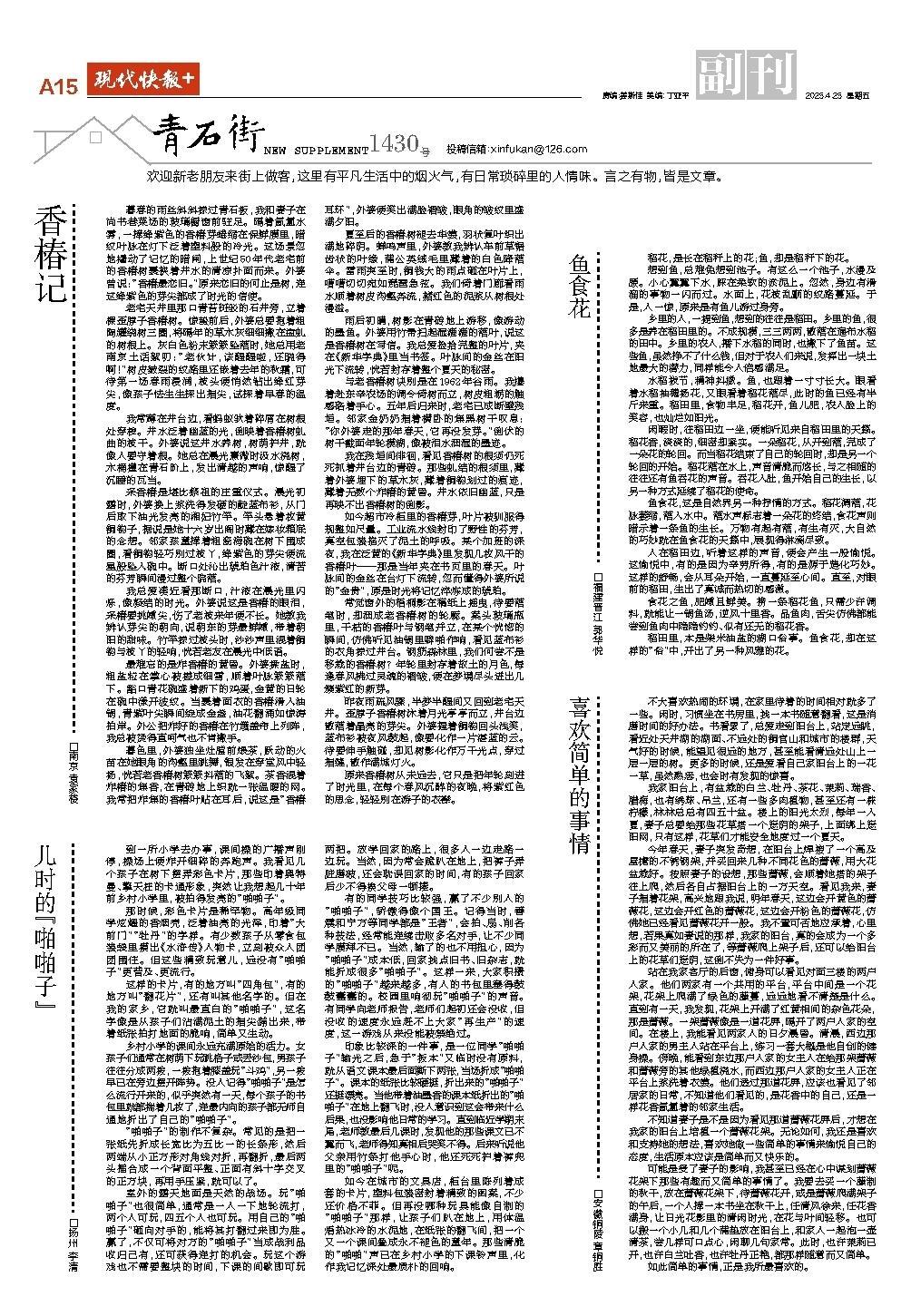□扬州 李清
到一所小学去办事,课间操的广播声刚停,操场上便炸开细碎的奔跑声。我看见几个孩子在树下摆弄彩色卡片,那些印着奥特曼、擎天柱的卡通形象,突然让我想起几十年前乡村小学里,被拍得发亮的“啪啪子”。
那时候,彩色卡片是稀罕物。高年级同学炫耀的香烟壳,泛着油亮的光泽,印着“大前门”“牡丹”的字样。有少数孩子从零食包装袋里摸出《水浒传》人物卡,立刻被众人团团围住。但这些精致玩意儿,远没有“啪啪子”更普及、更流行。
这样的卡片,有的地方叫“四角包”,有的地方叫“翻花片”,还有叫其他名字的。但在我的家乡,它就叫最直白的“啪啪子”,这名字像是从孩子们沾满泥土的指尖蹦出来,带着纸张拍打地面的脆响,简单又生动。
乡村小学的课间永远充满原始的活力。女孩子们通常在树荫下玩跳格子或丢沙包,男孩子往往分成两拨,一拨抱着膝盖玩“斗鸡”,另一拨早已在旁边摆开阵势。没人记得“啪啪子”是怎么流行开来的,似乎突然有一天,每个孩子的书包里就都揣着几枚了,连最内向的孩子都无师自通地折出了自己的“啪啪子”。
“啪啪子”的制作不复杂。常见的是把一张纸先折成长宽比为五比一的长条形,然后两端从小正方形对角线对折,再翻折,最后两头插合成一个背面平整、正面有斜十字交叉的正方块,再用手压紧,就可以了。
室外的露天地面是天然的战场。玩“啪啪子”也很简单,通常是一人一下地轮流打,两个人可玩,四五个人也可玩。用自己的“啪啪子”砸向对手的,能将其打翻过来即为胜。赢了,不仅可将对方的“啪啪子”当成战利品收归己有,还可获得连打的机会。玩这个游戏也不需要整块的时间,下课的间歇即可玩两把。放学回家的路上,很多人一边走路一边玩。当然,因为常会跪趴在地上,把裤子弄脏磨破,还会耽误回家的时间,有的孩子回家后少不得挨父母一顿揍。
有的同学技巧比较强,赢了不少别人的“啪啪子”,骄傲得像个国王。记得当时,善震和宁方等同学都是“王者”,会拍、扇、削各种技法,经常能连续击败多名对手,让不少同学膜拜不已。当然,输了的也不用担心,因为“啪啪子”成本低,回家找点旧书、旧杂志,就能折成很多“啪啪子”。这样一来,大家积攒的“啪啪子”越来越多,有人的书包里塞得鼓鼓囊囊的。校园里响彻玩“啪啪子”的声音。有同学向老师报告,老师们起初还会没收,但没收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大家“再生产”的速度,这一游戏从来没能被禁绝过。
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一位同学“啪啪子”输光之后,急于“扳本”又临时没有原料,就从语文课本最后面撕下两张,当场折成“啪啪子”。课本的纸张比较硬挺,折出来的“啪啪子”还挺漂亮。当他带着油墨香的课本纸折出的“啪啪子”在地上翻飞时,没人意识到这会带来什么后果,也没影响他日常的学习。直到临近学期末尾,老师教最后几课时,发现他的那些课文已不翼而飞,老师得知真相后哭笑不得。后来听说他父亲用竹条打他手心时,他还死死护着裤兜里的“啪啪子”呢。
如今在城市的文具店,柜台里陈列着成套的卡片,塑料包装密封着精致的图案,不少还价格不菲。但再没哪种玩具能像自制的“啪啪子”那样,让孩子们趴在地上,用体温焐热冰冷的水泥地,在纸张的翻飞间,把一个又一个课间叠成永不褪色的童年。那些清脆的“啪啪”声已在乡村小学的下课铃声里,化作我记忆深处最质朴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