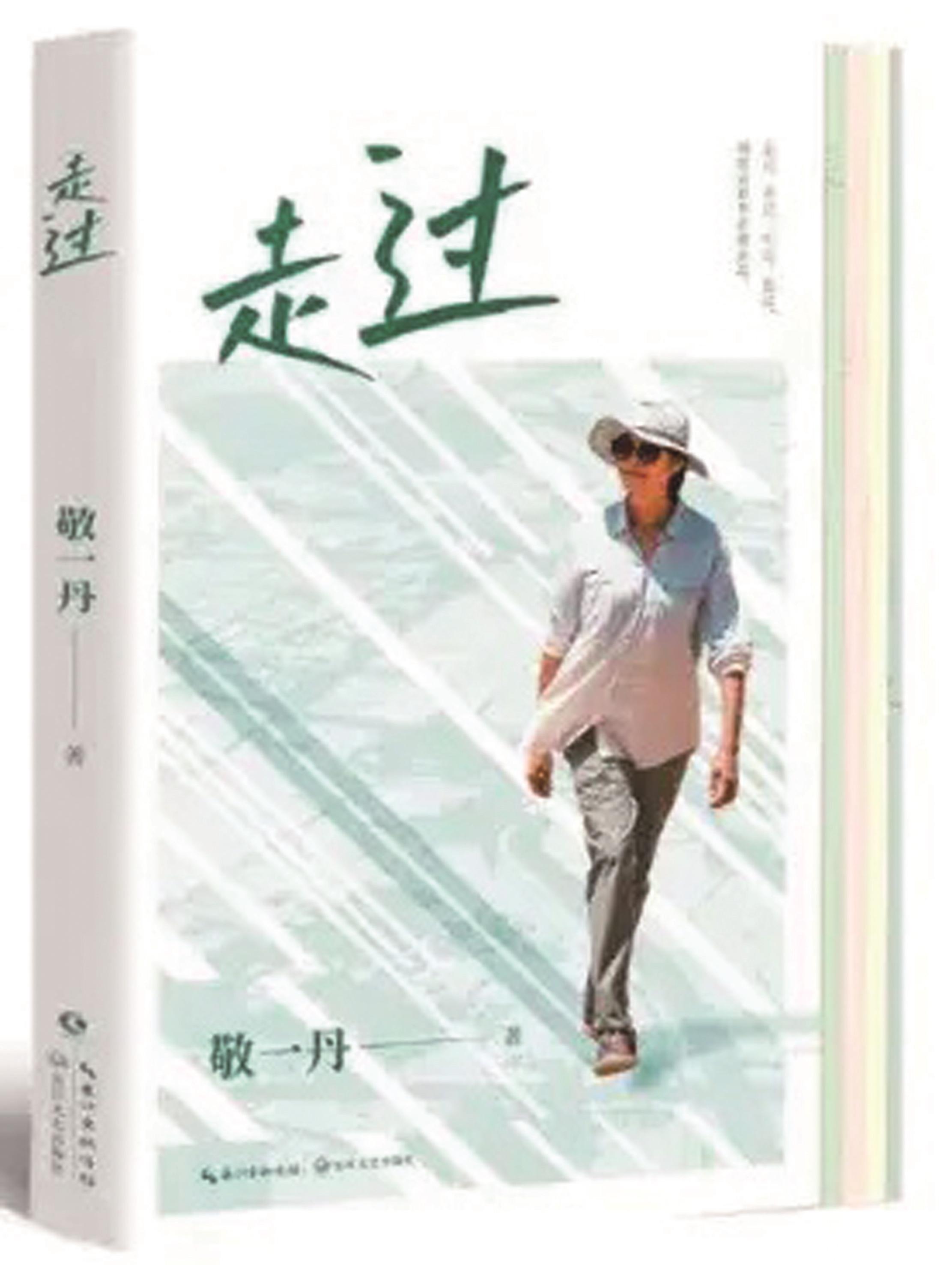《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感动中国》《新闻调查》……那些年,荧幕上的敬一丹常常是眉头紧蹙,声音沉稳而睿智。作为媒体人,半世光阴路上忙,她用脚步丈量时代,用声音和文字温暖人心。
近日,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携新作《走过》走进南京图书馆,分享她走过的路、见过的事。这是《走过》在南京的首场新书分享会,敬一丹分享了自己用心灵书写的“走过”。
作为媒体人,她不仅曾经“走过”,而且在退休之后一直坚持“走着”:先后出版了多本书,还尝试着新媒体的表达。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刘静妍
半世光阴路上忙
作为著名主持人、记者,敬一丹被全国的观众所熟知。她曾经站在电视的前沿,直播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事件。真诚、朴素、知性的主持风格,实力圈粉了各年龄层观众。
在观众的印象中,敬一丹常常是严肃、眉头紧蹙的形象,就像她退休那年出版的《我遇到你》封面照片上的形象。如今相隔十年,《走过》封面上的敬一丹,步履舒展而从容。
从主持人到写作者,从荧幕到图书,她用感性的触角、理性的观察,坚持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敬一丹说,《我遇到你》是她的职业回望,是十年前退休的时候写的,“我的职业形象其实就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总是皱着眉头面对节目中聚焦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初,在《焦点访谈》之前,敬一丹主持了一档节目,叫《一丹话题》。“那时候,我就总是皱着眉头。”她笑着调侃道,“要不然怎么选我去主持《焦点访谈》呢?”如今出版的《走过》,是她退休十年以后写的,相比退休前,有着截然不同的状态。
《走过》是敬一丹的随笔集。作为媒体人,半世光阴路上忙,走过了东南西北,走过了春夏秋冬,也走过了悲欣苦乐。走过、看过、听过、想过,于是,有了不一样的目光,有了不一样的表达。书中以二十四节气作为时间轴,以走过的地方作为空间点,作者在时间与空间交汇处,写下记者、行者的经历与感悟。“走过”不仅是一本书的名字,更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与态度。她用大量的文字描述走过的山川湖海,也呈现了一种跨越年龄、行业、性别的人生状态。她以记者的敏锐记录时代变迁,以行者的姿态感受自然馈赠。
“走过”南京的记忆
职业生涯中,她多次“走过”南京。其中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馆布展的时候。当时,《新闻调查》栏目的记者们在那个场地里开始记录,采访了多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做了一期40分钟的新闻调查节目。“我在那个场馆里待了一星期,节目录制临近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我快抑郁了。那种沉重的话题,那份不堪承受之重……”敬一丹说,在《焦点访谈》工作了那么多年,经常面对阴影里的话题,她一直觉得自己的承受力还是很强的,但是南京大屠杀的话题依旧让她无法释然。该怎么缓解呢?走出纪念馆,她走进了隔壁的云锦博物馆。看到云锦她就在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美好的东西啊?
“我用这种方法调整了我自己,救了我自己。”她说,平时工作中也是如此。如果目光长久地聚焦阴影里的东西,是没有那样的承受力的,幸好在节目里遇到了《感动中国》,这档节目是温暖的、给人信心的。“这样就能保持一种平衡。这世界就是这样:有阴影,也有光明;有冷峻,也有温暖。”
2025年6月15日,夏至到来之前的一个周末午后,敬一丹又一次来到南京,在南京图书馆与读者们分享了新书《走过》。南京图书馆所在的长江路上,坐落着六朝博物馆、江宁织造博物馆、南京总统府景区、江苏省美术馆等多家文博场馆。去南图的路上,她路过这些博物馆,看到门前人头攒动,一时之间感慨万千。
兴之所至,第二天她去参观了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她一边参观,一边与工作人员交谈:“从我们游客的角度,其实特别希望星期一也能到博物馆来参观。这次来到南京,我如愿以偿了。来到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
记录30年间博物馆的冷与热
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也是博物馆之城。与当下的“文博热”相反,敬一丹依然记得30多年前博物馆的“冷”。1993年,她做了一档节目,名叫《寂寞的博物馆》。那时候的博物馆寂寞到什么程度?她说,北京的知名博物馆,居然在出租场馆卖家具。“当时看到那样的状况,我特别难过。”
这么多年过去,她在职业生涯中记录着博物馆的变化。退休之后,敬一丹在央视频做了一档文化类节目——《博物馆九分钟》,主要聚焦小微博物馆,用一镜到底和新媒体的形式讲述博物馆的故事。“走过”这些博物馆录制节目的时候,她看到了什么?又在思考着什么?台前幕后的故事,都收录在了新书《走过》中,比如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六朝博物馆,以及外地的中国皮影博物馆、建川博物馆、传媒博物馆、普通话博物馆……
前年夏至日到来之际,她去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节目在央视频推出的时候,正是高考前后。看到今天很多年轻人来到这儿,见到龙门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跨过去。在对明远楼的仰望中,古今的碰撞,带给她无尽思考:“说到科举,中国人会想着什么?是金榜题名还是五子登科?是想着范进中举,还是名落孙山?那么多成语典故和文人的故事都和科举联系着。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到1905年就被废止了。如今已经100多年了,然而在这之前,它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有的痕迹是无形的,有的是有形的,无形的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基因里,而有形的就珍藏在博物馆里。”
在南京的六朝博物馆,“六朝的微笑”深深触动了她。六朝博物馆人面纹瓦当,带着神秘的微笑,穿越千年时空而来。令她更加印象深刻的是,在博物馆负一层遗址抬头往上看,有一扇窗子直可以看到地面,“我们可以想象,在热闹的南京街头,我们看到今天的南京人的微笑……”这让她突然想到镜头语言的表达方式:一镜穿越,镜头通过窗子从地下穿越到今天的马路上,就看到了今天南京人的微笑,再来一个俯拍的镜头。想到这样表达的时候,她特别兴奋。
“短短的9分钟,我们不是《国家宝藏》,而是新媒体一镜到底的方式,常常会觉得表达得非常有限。”敬一丹说。
■对话
不管哪个城市赢
江苏都赢了
读品:您最近在关注什么新闻?
敬一丹:我现在最想看到的新闻就是苏超。江苏这个活动太引人注目了,让人特别欢乐,这是特别值得让人琢磨的事情。不管哪个城市赢,我觉得江苏都赢了。这次来到南京,是故地重游。我第一次来南京是1978年,那时候在苏州实习,特意来了一趟南京。当时,我的感觉是:这座城市我好像来过。其实在此之前我根本没有来过南京,只是对它非常认同:它兼容了南北的精华,在我面前呈现出非常大气、厚重的气质。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地方,来了好多次,都没有真正读懂它。
读品:您为什么在退休之后开始做新媒体?
敬一丹:回首职业生涯,我是幸运的:我做广播的时候,广播是强势媒体。我做电视的时候,电视是强势媒体。当我快要退休的时候,电视已经面对着新媒体的挑战了。但是,后来我又觉得,如果一个人的职业体验都是高峰,那也未免是一种单调,怎么能不体会到什么叫挑战呢?于是,退休以后,我以一种放松的心态接触了新媒体,在央视频开设了文化类节目。如果说过去做《焦点访谈》节目,让我享受的是直接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成就感。那么,现在做文化类新媒体节目,过程就让我很享受,我觉得特别滋补人。
读品:您先后出版了《声音》《一丹话题》《我遇到你》《那年 那信》《床前明月光》《走过》等多部著作。有读者认为,您是从电视节目主持人“跨界”到了写作者。为什么您无论在职还是退休后,都一直坚持着写作?
敬一丹:前几天,我把我的家书捐给了家书博物馆。一家媒体的稿子是这样写的:年逾古稀的敬一丹捐出了她的四封家书。我的第一个反应:这事和年逾古稀有关吗?我仔细一想,还真有关。如果不是年逾古稀,我能有那么多家书吗?
最近有一个年轻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问了我“未来的人生规划”。特别高兴,一个70岁的人还得面对着年轻记者说人生规划。在我60岁退休的时候,一个老同事跟我说:小敬,你退休以后要做计划,要不然退休以后的日子就很快就会过去了。当年他70岁,我当时说:康老,我离您那时候还远着呢。结果,一转眼小敬也变成了敬老了。
那还要不要去做规划呢?我不太擅长做长期规划,但是我经常会有一个中期的能看得见的目标。当我心里有一个愿望的时候,我非常珍惜;当我心里有一种创作热情的时候,我就想一定得抓住。我也不是那么容易兴奋的人。一旦有一点兴奋,带有一种创造性的兴奋,我就顺势开始了,比如写作。
媒体人写作,不是跨界,是题中应有之义。现代的媒体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可以是镜头和话筒,也可以是文字。用文字表达是基础。我在职的时候写了5本书,都是偏播音主持、编采业务的书。退休以后,我觉得文字的表达更加沉淀。以前在镜头前、话筒前说的话,多半都是公共话语,而写在书上的更像我自己。我退休以后写了5本书,就是特别害怕忘记。我觉得忘记是很危险的,所以把我害怕忘记的这些东西写下来。书出来了以后,有人说你写的东西都是怀旧色彩的。是啊,有旧可怀,也是可以怀旧的。我把怀旧的事做完,再面对新的。那我有没有能力写出一个就是特别当下的话题呢?那得有一种“走着”的状态,而不是“走过”的状态。
敬一丹
中央电视台播音指导,电视节目主持人。1986年在中国传媒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曾主持央视《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感动中国》等节目,三次获得全国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现任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近年来主创新媒体节目《节气 长城》《博物馆九分钟》。著有《声音》《一丹话题》《我遇到你》《那年 那信》《床前明月光》《走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