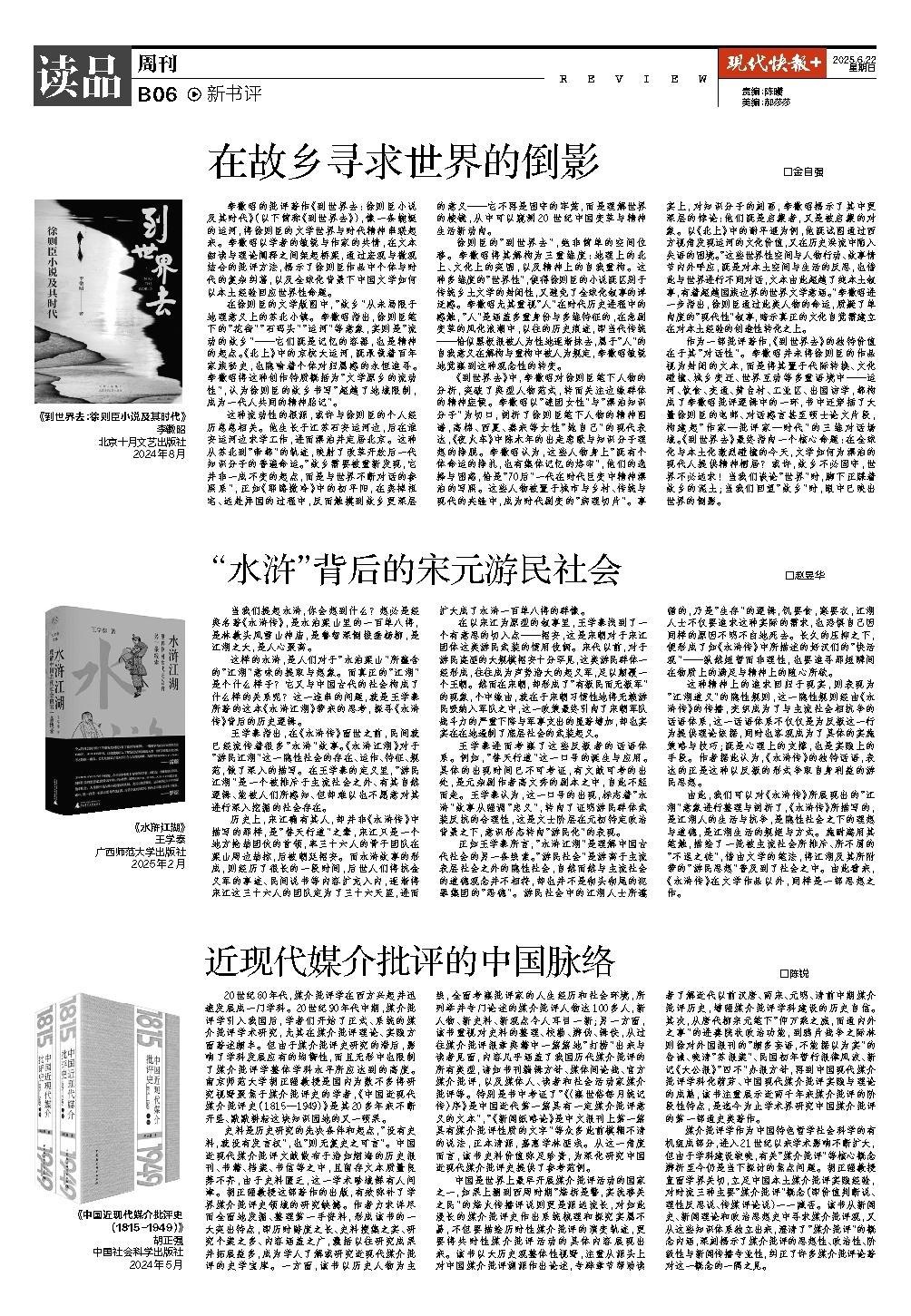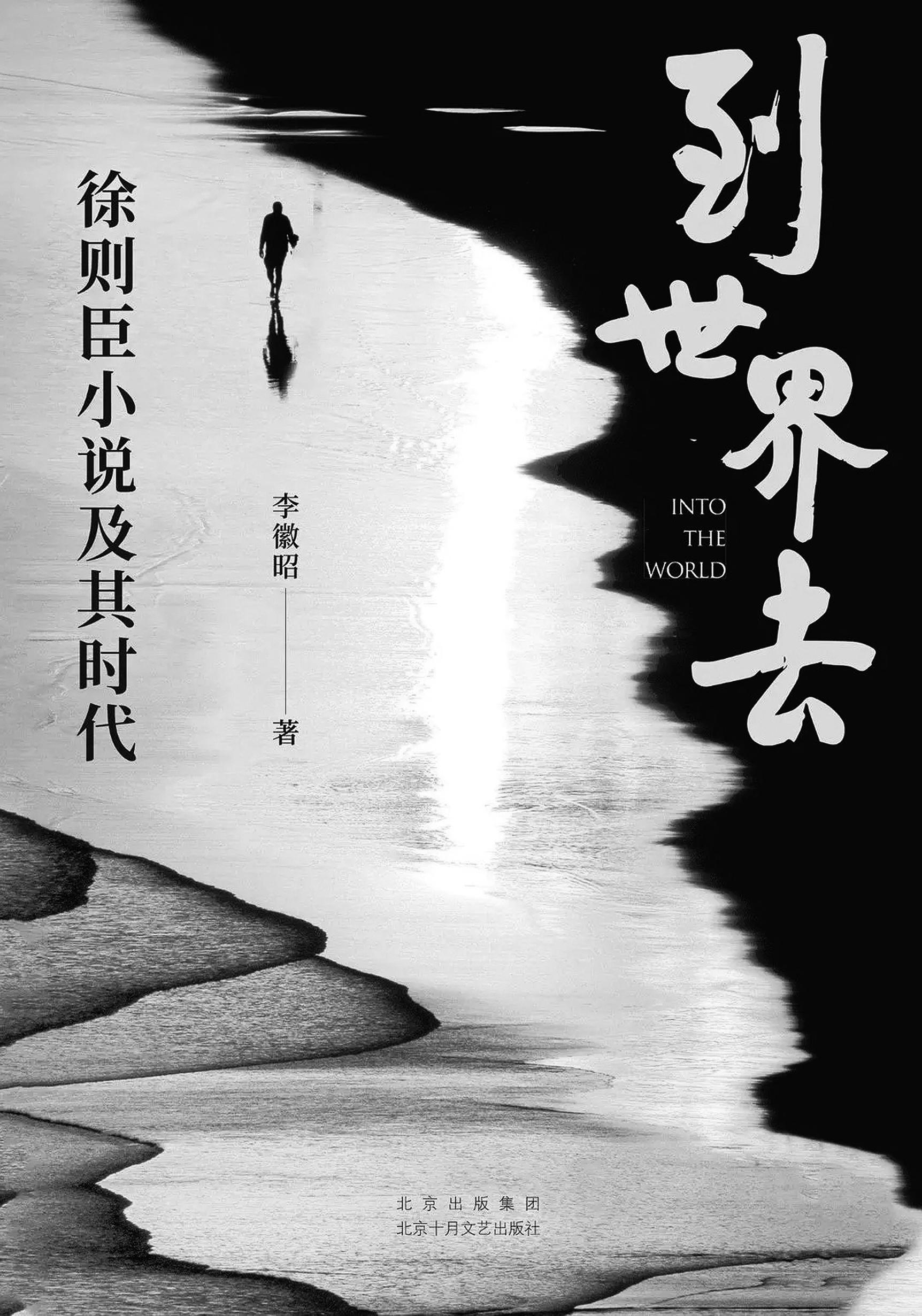□金自强
李徽昭的批评著作《到世界去:徐则臣小说及其时代》(以下简称《到世界去》),像一条蜿蜒的运河,将徐则臣的文学世界与时代精神串联起来。李徽昭以学者的敏锐与作家的共情,在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批评方法,揭示了徐则臣作品中个体与时代的复杂纠葛,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如何以本土经验回应世界性命题。
在徐则臣的文学版图中,“故乡”从未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苏北小镇。李徽昭指出,徐则臣笔下的“花街”“石码头”“运河”等意象,实则是“流动的故乡”——它们既是记忆的容器,也是精神的起点。《北上》中的京杭大运河,既承载着百年家族秘史,也隐喻着个体对归属感的永恒追寻。李徽昭将这种创作特质概括为“文学原乡的流动性”,认为徐则臣的故乡书写“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精神胎记”。
这种流动性的根源,或许与徐则臣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他生长于江苏石安运河边,后在淮安运河边求学工作,进而漂泊并定居北京。这种从苏北到“帝都”的轨迹,映射了改革开放后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故乡需要被重新发现,它并非一成不变的起点,而是与世界不断对话的参照系”,正如《耶路撒冷》中的初平阳,在卖掉祖宅、远赴异国的过程中,反而触摸到故乡更深层的意义——它不再是困守的牢笼,而是理解世界的棱镜,从中可以窥测20 世纪中国变革与精神生活新动向。
徐则臣的“到世界去”,绝非简单的空间位移。李徽昭将其解构为三重维度:地理上的北上、文化上的突围,以及精神上的自我重构。这种多维度的“世界性”,使得徐则臣的小说既区别于传统乡土文学的封闭性,又避免了全球化叙事的浮泛感。李徽昭尤其重视“人”在时代历史进程中的感触,“人”是涵盖多重身份与多维特征的,在急剧变革的风化浪潮中,以往的历史痕迹,即当代传统——恰似黑板报被人为性地逐渐抹去,属于“人”的自我意义在解构与重构中被人为规定,李徽昭敏锐地觉察到这种观念性的转变。
《到世界去》中,李徽昭对徐则臣笔下人物的分析,突破了典型人物范式,转而关注边缘群体的精神症候。李徽昭以“谜团女性”与“漂泊知识分子”为切口,剖析了徐则臣笔下人物的精神图谱,高棉、西夏、秦来等女性“她自己”的现代表达,《夜火车》中陈木年的出走悲歌与知识分子理想的挣脱。李徽昭认为,这些人物身上“既有个体命运的挣扎,也有集体记忆的烙印”,他们的选择与困惑,恰是“70后”一代在时代巨变中精神漂泊的写照。这些人物被置于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成为时代剧变的“病理切片”。事实上,对知识分子的刻画,李徽昭揭示了其中更深层的悖论:他们既是启蒙者,又是被启蒙的对象。以《北上》中的谢平遥为例,他既试图通过西方视角发现运河的文化价值,又在历史洪流中陷入失语的困境。“这些世界性空间与人物行动、故事情节内外呼应,既是对本土空间与生活的反思,也借此与世界进行不同对话,文本由此超越了纯本土叙事,有着超越国族边界的世界文学意涵。”李徽昭进一步指出,徐则臣通过此类人物的命运,质疑了单向度的“现代性”叙事,暗示真正的文化自觉需建立在对本土经验的创造性转化之上。
作为一部批评著作,《到世界去》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对话性”。李徽昭并未将徐则臣的作品视为封闭的文本,而是将其置于代际转换、文化碰撞、城乡变迁、世界互动等多重语境中——运河、饮食、交通、黄台村、工业区、出国访学,都构成了李徽昭批评逻辑中的一环,书中还穿插了大量徐则臣的电邮、对话感言甚至硕士论文片段,构建起“作家—批评家—时代”的三维对话场域。《到世界去》最终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激烈碰撞的今天,文学如何为漂泊的现代人提供精神栖居?或许,故乡不必固守,世界不必远求!当我们谈论“世界”时,脚下正踩着故乡的泥土;当我们回望“故乡”时,眼中已映出世界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