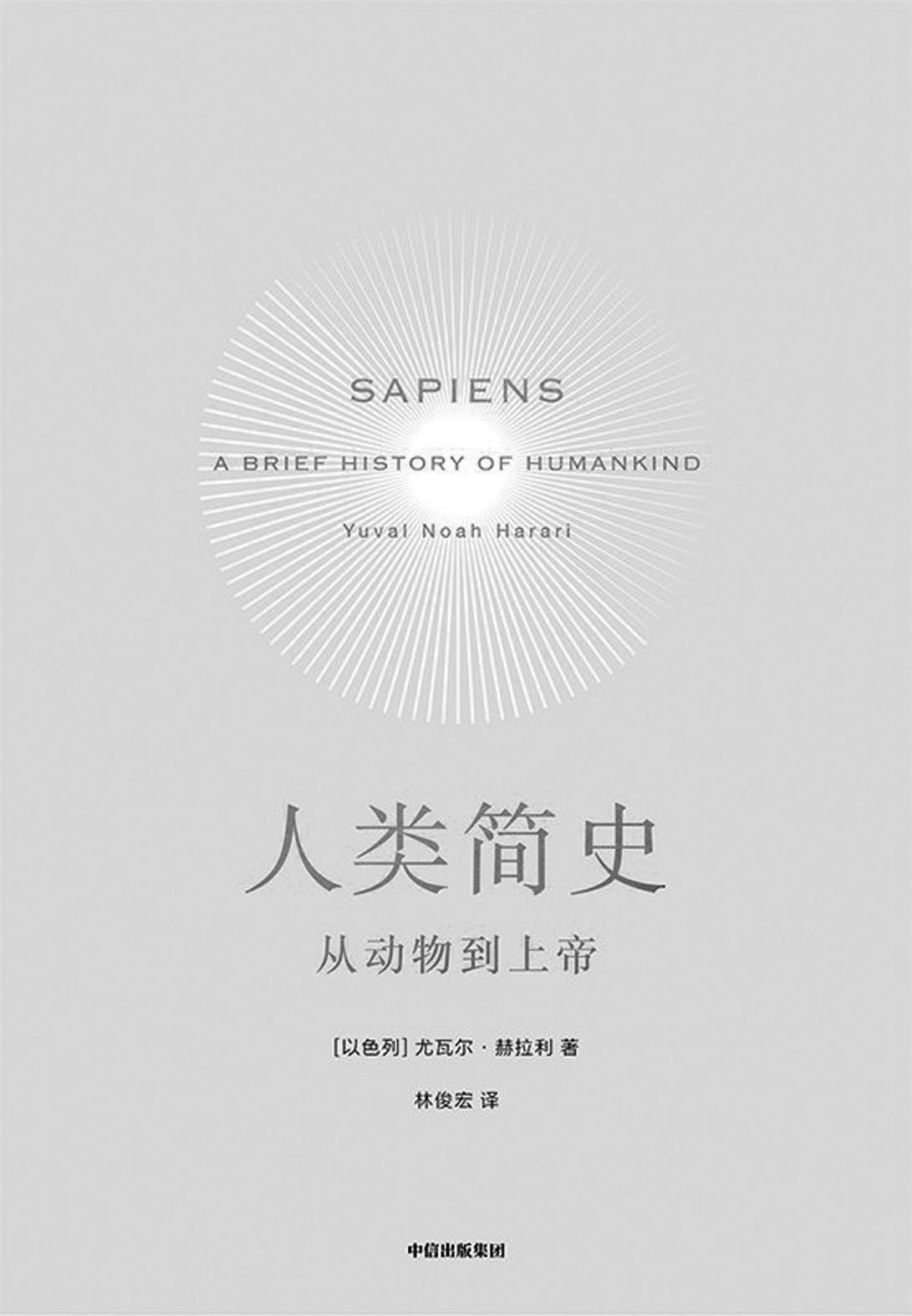□陆远
从物种进化的角度看,人类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成为小小寰球的“主宰者”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如果从古猿露西算起,人类存在的历史已经超过300万年了。在这300多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一直就只是一种弱小的、边缘性的生物。虽然人类很早就已经进化出容量很大的大脑,也能够制造锋利的石器,但是我们的祖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靠采集植物、找寻昆虫、追杀小动物,甚至吃豺狼虎豹留下的腐肉过活,面对大自然这个神威莫测的“君王”,我们先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对生存危机的焦虑和恐惧中艰难度过的。
然而,奇迹在差不多10万年前突然发生了,人类一跃而占据食物链的顶端。这次飞跃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此后人类文明史上让我们倍感自豪的所有成就。要知道,其他曾经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动物,至少都要花费数百万年的时间,才有可能通过演化取得相同的位置,而人类的进化之快、力量之大,简直令整个自然瞠目结舌。
让人类有如神助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称之为“认知革命”。在赫拉利看来,在所有的物种当中,只有人类能够建立(赫拉利用的词是“虚构”,强调集体形成过程中认知和观念发挥的巨大力量)一种集体概念——比如国家、民族、社会等等。这些概念虽然抽象,却具有无比强大的凝聚力,让人类能够有意识地分工合作,守望相助。
读《人类简史》到这里,我想起学者威利斯回忆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一段往事。
20世纪60年代,在米德的一次公开讲演后,有听众提问:发掘出一个原始部落的遗址后,您怎么判断它是否已进入早期文明阶段了?坐在台下的威利斯心里猜想,答案可能是从中发现了陶罐或者鱼钩,要不就是碾米的石臼。没想到,米德的回答却是:文明的最初标志,是部落里出现受伤后又愈合的股骨。她解释说,在一个完全野蛮的部落里,个体的生死纯粹取决于残酷的丛林守则:优胜劣汰,除了少数特例,多数受伤的个体都无法生存下去,更别说等到骨伤痊愈了。如果在一个部落的遗址中出现了大量愈合的股骨,就说明这些原始人在受伤后得到了同伴的保护和照顾,有人跟他们分享火堆、水和食物,直到他们的骨伤愈合。米德意味深长地说:这正是文明与野蛮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某种程度上,懂得互助与合作,并在互助与合作的过程中建立一整套文明与认同的无形之网,是人类能够“逆袭”最重要的社会原因。直到今天,我们依旧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全人类的互助与合作,在肆虐的病毒面前人类的命运会怎样。
不过,别高兴得太早。人类在生物链上过于仓促地飞跃,未必就一定是好事。其他动物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因此生态系统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出种种制衡,避免它造成太大的破坏。相比之下,人类转眼就登上顶端,不仅让生态系统猝不及防,就连我们自己也不知所措。大自然预留的那根伏线,以一种叫作“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如影随形。在过去数万年的时间里,人类每一次巨大的物质进步,都是以征服、改造乃至摧毁自然的方式进行的。如果说,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对自然还多少保有一些敬畏的话——就像拿破仑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油然而生的那种敬畏,那么机器大生产打破了敬畏心在我们内心设下的最后一道防线,人类从内心里认为,我们已经从自然的“臣民”,变成了“主人”。
但是,在人类文明史的每一个阶段,自然都在用一种低沉却很清晰的声音警告我们这个有点得意忘形的物种:无视我的存在,你们会付出巨大的,甚至不可承受的代价。有人曾经问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作家回答道:“毫无意义,人类的出现,不过是自然对环境做出的反应罢了。”作家的话很悲观,但是也很深刻——一切深刻的思想都是悲观的——但我们寻常人至少要永远牢记的是:对于自然来说,我们永远是过客,人类需要大自然,而自然本不需要人类。
所幸,在危机面前,人类那种互助与合作的天性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根稻草。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以及系列相关著作中一再强调,21世纪,需要所有人跳出短视的窠臼,跳出人类中心的局限,以更大的格局和眼界观照人与自然的共生与未来。人类生存与环境问题,从来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某一个行业、某一群人才需要的关心。除非对生存危机的体认和解决环境问题的迫切性成为社会共识,我们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
2024年,世界需要一个新文明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