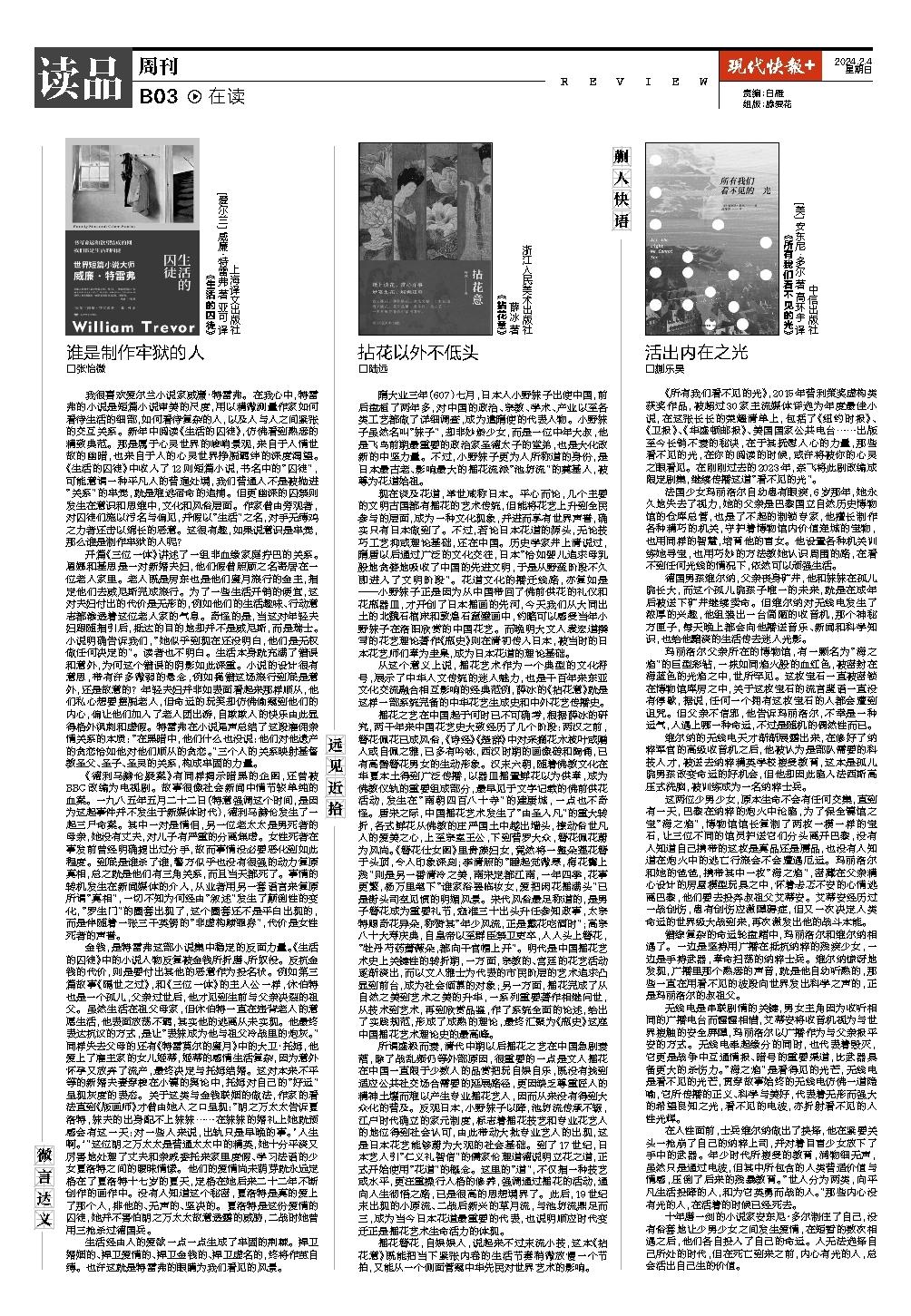□张怡微
我很喜欢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在我心中,特雷弗的小说是短篇小说审美的尺度,用以精微测量作家如何看待生活的细部,如何看待复杂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紧张的交互关系。新年中阅读《生活的囚徒》,仿佛看到熟悉的精致典范。那是属于心灵世界的峻峭景观,来自于人情世故的幽暗,也来自于人的心灵世界挣脱羁绊的深度渴望。《生活的囚徒》中收入了12则短篇小说,书名中的“囚徒”,可能意谓一种平凡人的普遍处境,我们普通人不是被抛进“关系”的牢笼,就是难逃宿命的追捕。但更幽深的囚禁则发生在意识和思维中,文化和风俗层面。作家借由旁观者,对囚徒们施以污名与偏见,并假以“生活”之名,对手无缚鸡之力者还击以绵长的恶意。这很有趣,如果说意识是牢笼,那么谁是制作牢狱的人呢?
开篇《三位一体》讲述了一组非血缘家庭拧巴的关系。恩娜和基思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假借照顾之名寄居在一位老人家里。老人既是房东也是他们蜜月旅行的金主,指定他们去威尼斯完成旅行。为了一些生活开销的便宜,这对夫妇付出的代价是无形的,例如他们的生活趣味、行动意志都渗透着这位老人家的气息。奇怪的是,当这对年轻夫妇跟随指引后,抵达的目的地却并不是威尼斯,而是瑞士。小说明确告诉我们,“她似乎到现在还没明白,他们是无权做任何决定的”。读者也不明白。生活本身就充满了错误和意外,为何这个错误的阴影如此深重。小说的设计很有意思,带有许多微弱的悬念,例如搞错这场旅行到底是意外,还是故意的?年轻夫妇并非如表面看起来那样顺从,他们私心想要摆脱老人,但命运的玩笑却仿佛偷窥到他们的内心,偏让他们加入了老人团出游,自欺欺人的快乐由此显得格外讽刺和虚假。特雷弗在小说尾声总结了这段雇佣亲情关系的本质:“在黑暗中,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对他遗产的贪恋恰如他对他们顺从的贪恋。”三个人的关系映射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构成牢固的力量。
《德利马赫伦疑案》有同样揭示暗黑的企图,还曾被BBC改编为电视剧。故事很像社会新闻中情节较单纯的血案。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特意强调这个时间,是因为这起事件并不发生于新媒体时代),德利马赫伦发生了一起三尸命案。其中一对是情侣,另一位老太太是男死者的母亲,她没有丈夫,对儿子有严重的分离焦虑。女性死者在事发前曾经明确提出过分手,故而事情没必要恶化到如此程度。到底是谁杀了谁,警方似乎也没有很强的动力复原真相,总之就是他们有三角关系,而且当天都死了。事情的转机发生在新闻媒体的介入,从业者用另一套语言来复原所谓“真相”,一切不知为何经由“叙述”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罗生门”的圈套出现了,这个圈套还不是平白出现的,而是伴随着一张三千英镑的“非虚构赎罪券”,代价是女性死者的声誉。
金钱,是特雷弗这部小说集中稳定的反面力量。《生活的囚徒》中的小说人物反复被金钱所折磨、所奴役。反抗金钱的代价,则是要付出其他的恶意作为投名状。例如第三篇故事《隔世之过》,和《三位一体》的主人公一样,休伯特也是一个孤儿,父亲过世后,他才见到生前与父亲决裂的祖父。虽然生活在祖父母家,但休伯特一直在违背老人的意愿生活,他表面放荡不羁,其实他的逃离从未实现。他最终表达抗议的方式,是让“表妹成为他与祖父冷战里的炮灰。”同样失去父母的还有《特雷莫尔的蜜月》中的大卫∙托姆,他爱上了雇主家的女儿姬蒂,姬蒂的感情生活复杂,因为意外怀孕又放弃了流产,最终决定与托姆结婚。这对本来不平等的新婚夫妻穿梭在小镇的舆论中,托姆对自己的“好运”呈现灰度的表态。关于这类与金钱联姻的做法,作家的看法直到《版画师》才借由她人之口呈现:“朗之万太太告诉夏洛特,妹夫的出身配不上妹妹……在妹妹的婚礼上她就预感会有这一天:对一些人来说,出轨只是早晚的事。‘人生啊。’”这位朗之万太太是普通太太中的精英,她十分平淡又厉害地处理了丈夫和亲戚委托来家里度假、学习法语的少女夏洛特之间的暧昧情愫。他们的爱情尚未萌芽就永远定格在了夏洛特十七岁的夏天,定格在她后来二十二年不断创作的画作中。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夏洛特是真的爱上了那个人,排他的、无声的、坚决的。夏洛特是这份爱情的囚徒,她并不害怕朗之万太太故意透露的威胁,二战时她曾用三枪杀过德国兵。
生活经由人的爱欲一点一点生成了牢固的荆棘。捍卫婚姻的、捍卫爱情的、捍卫金钱的、捍卫虚名的,终将作茧自缚。也许这就是特雷弗的眼睛为我们看见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