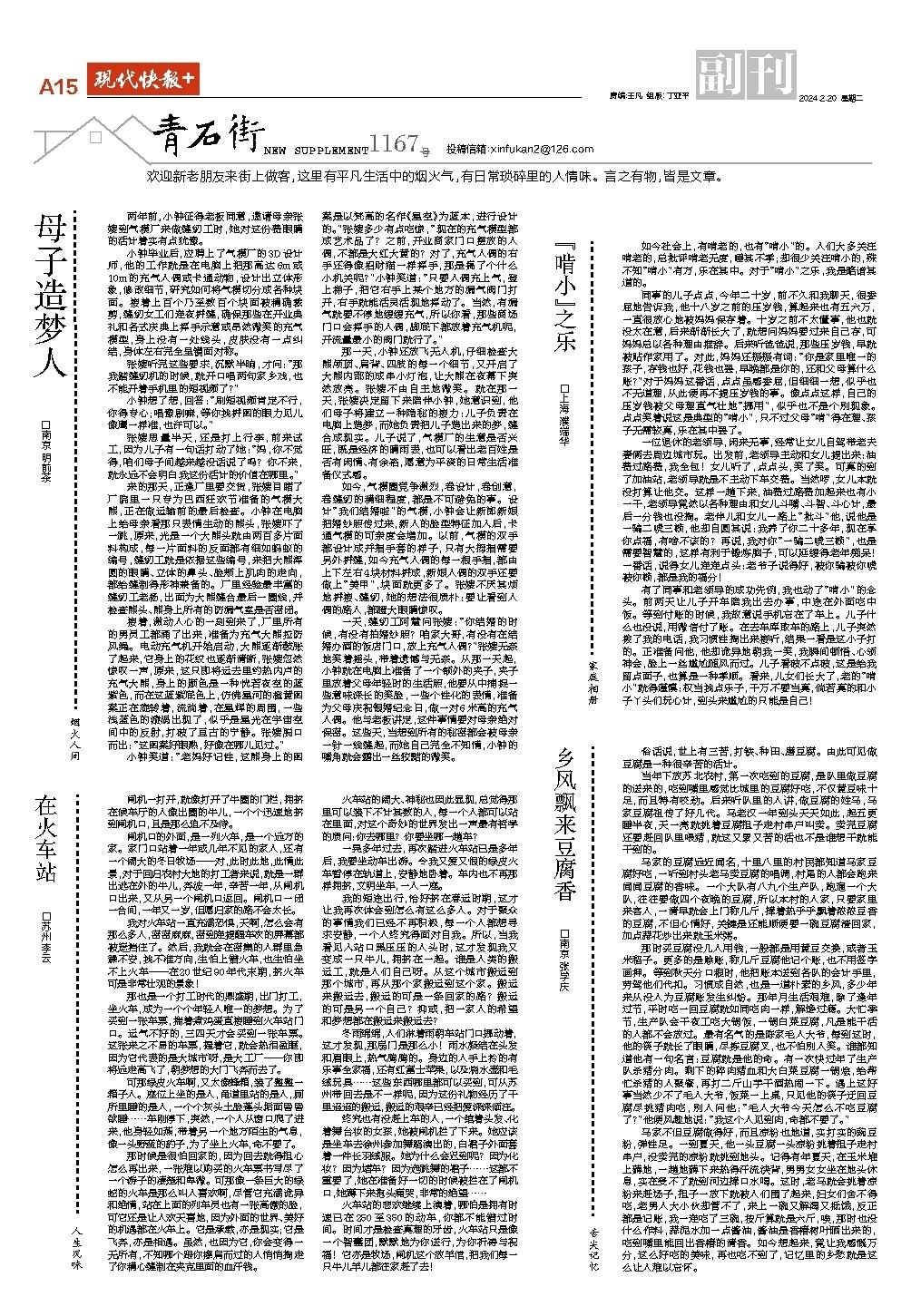□苏州 李云
闸机一打开,就像打开了牛圈的门栏,拥挤在候车厅的人像出圈的牛儿,一个个迅速地挤到闸机口,且是那么迫不及待。
闸机口的外面,是一列火车,是一个远方的家。家门口站着一年或几年不见的家人,还有一个阔大的冬日牧场——对,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对于回归农村大地的打工者来说,就是一群出逃在外的牛儿,奔波一年,辛苦一年,从闸机口出来,又从另一个闸机口返回。闸机口一闭一合间,一年又一岁,但愿归家的路不会太长。
我对火车站一直充满恐惧,天啊,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密密麻麻,密到连提醒车次的屏幕都被遮挡住了。然后,我就会在密集的人群里急躁不安,找不准方向,生怕上错火车,也生怕坐不上火车——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挤火车可是非常壮观的景象!
那也是一个打工时代的鼎盛期,出门打工,坐火车,成为一个个年轻人唯一的梦想。为了买到一张车票,揣着煮鸡蛋直接睡到火车站门口。运气不好的,三四天才会买到一张车票。这张来之不易的车票,握着它,就会热泪盈眶,因为它代表的是大城市呀,是大工厂——你即将远走高飞了,朝梦想的大门飞奔而去了。
可那绿皮火车啊,又太像蜂箱,装了整整一箱子人。座位上坐的是人,甬道里站的是人,厕所里睡的是人,一个个灰头土脸蓬头垢面昏昏欲睡……车刚停下,突然,一个人从窗口爬了进来,他身轻如燕,带着另一个地方陌生的气息,像一头野蛮的豹子,为了坐上火车,命不要了。
那时候是很怕回家的,因为回去就得担心怎么再出来,一张难以购买的火车票书写尽了一个游子的凄楚和卑微。可那像一条巨大的绿蛇的火车是那么叫人喜欢啊,尽管它充满诡异和绝情,站在上面的列车员也有一张高傲的脸,可它还是让人欢天喜地,因为外面的世界、美好的机遇都在火车上。它是承载,亦是现实;它是飞奔,亦是相遇。虽然,也因为它,你会变得一无所有,不知哪个跟你擦肩而过的人悄悄掏走了你精心缝制在夹克里面的血汗钱。
火车站的阔大、神秘也因此显现,总觉得那里可以装下不计其数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里面,对这个奇妙的世界发出一声最有哲学的质问:你去哪里?你要坐哪一趟车?
一晃多年过去,再次踏进火车站已是多年后,我要坐动车出游。令我又爱又恨的绿皮火车暂停在轨道上,安静地卧着。车内也不再那样拥挤,文明坐车,一人一座。
我的短途出行,恰好挤在春运时期,这才让我再次体会到怎么有这么多人。对于聚众的事情我们已经不再积极,每一个人都想寻求安静,一个人终究得面对自我。所以,当我看见入站口黑压压的人头时,这才发现我又变成一只牛儿,拥挤在一起。谁是人类的搬运工,就是人们自己呀。从这个城市搬运到那个城市,再从那个家搬运到这个家。搬运来搬运去,搬运的可是一条回家的路?搬运的可是另一个自己?抑或,把一家人的希望和梦想都在搬运来搬运去?
冬雨绵绵,人们淋着雨朝车站门口挪动着,这才发现,那扇门是那么小!雨水凝结在头发和眉眼上,热气腾腾的。身边的人手上拎的有乐事全家福,还有红富士苹果,以及烧水壶和毛绒玩具……这些东西哪里都可以买到,可从苏州带回去是不一样呢,因为这份礼物经历了千里迢迢的搬运,搬运的艰辛已经把爱深深倾注。
终究也有没赶上车的人,一个绾着头发、化着舞台妆的女孩,她被闸机拦了下来。她应该是坐车去徐州参加舞蹈演出的,白裙子外面套着一件长羽绒服。她为什么会迟到呢?因为化妆?因为堵车?因为选跳舞的裙子……这都不重要了,她在准备好一切的时候被拦在了闸机口,她蹲下来抱头痛哭,非常的绝望……
火车站的悲欢继续上演着,哪怕是拥有时速已在250至350的动车,你都不能错过时间。时间才是检查真理的牙齿,火车站只是像一个智囊团,默默地为你送行,为你祈祷与祝福!它亦是牧场,闸机这个放羊倌,把我们每一只牛儿羊儿都往家赶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