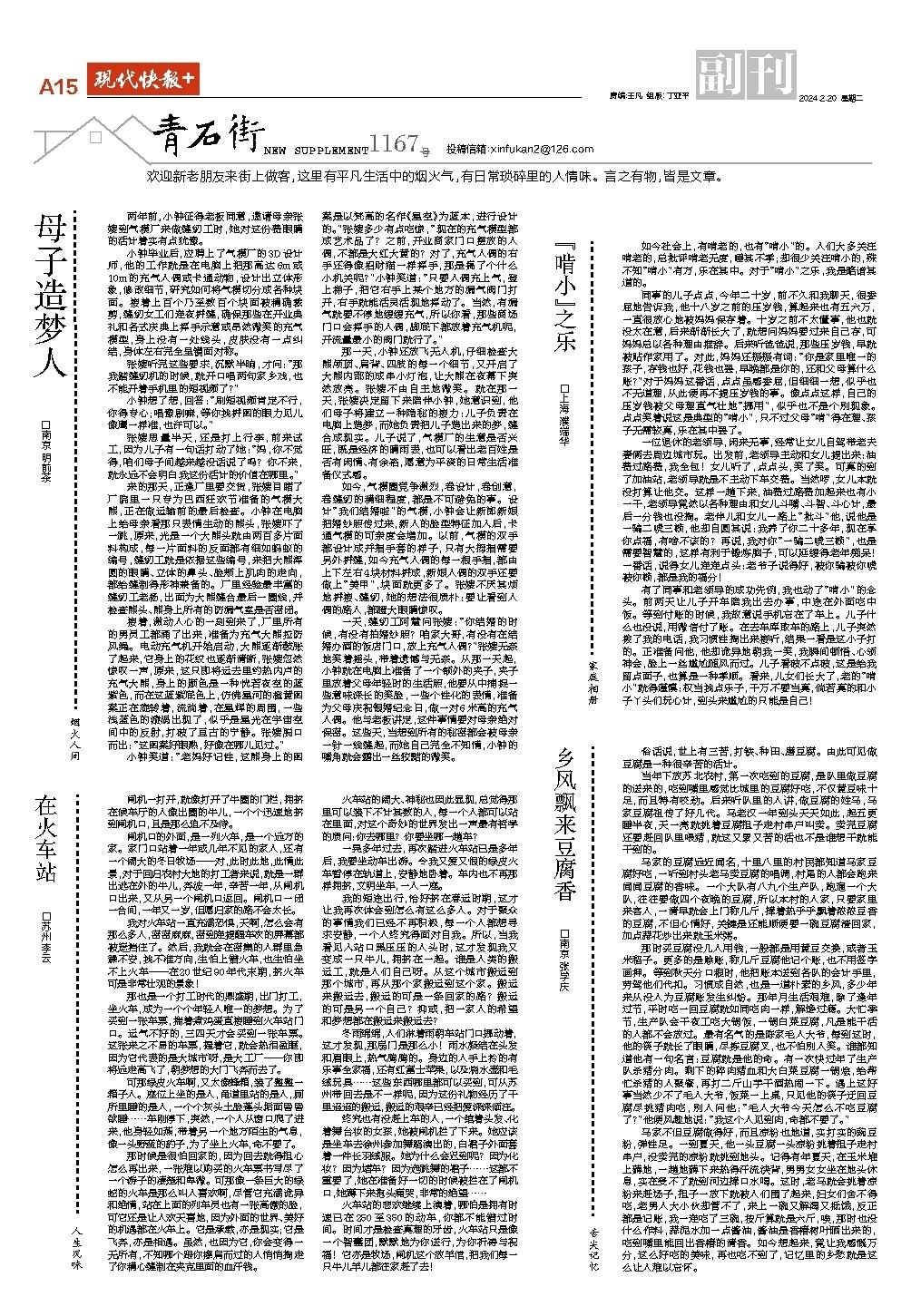□南京 张学庆
俗话说,世上有三苦,打铁、种田、磨豆腐。由此可见做豆腐是一种很辛苦的活计。
当年下放苏北农村,第一次吃到的豆腐,是队里做豆腐的送来的,吃到嘴里感觉比城里的豆腐好吃,不仅黄豆味十足,而且特有咬劲。后来听队里的人讲,做豆腐的姓马,马家豆腐祖传了好几代。马老汉一年到头天天如此,起五更睡半夜,天一亮就挑着豆腐担子走村串户叫卖。卖完豆腐还要赶回队里喂猪,就这又累又苦的活也不是谁想干就能干到的。
马家的豆腐远近闻名,十里八里的村民都知道马家豆腐好吃,一听到村头老马卖豆腐的唱调,村尾的人都会跑来闻闻豆腐的香味。一个大队有八九个生产队,跑遍一个大队,往往要做四个夜晚的豆腐,所以本村的人家,只要家里来客人,一清早就会上门称几斤,捧着热乎乎飘着浓浓豆香的豆腐,不但心情好,关键是还能顺便要一碗豆腐渣回家,加点蒜花炒出来就玉米粥。
那时买豆腐没几人用钱,一般都是用黄豆交换,或者玉米稻子。更多的是赊账,称几斤豆腐他记个账,也不用签字画押。等到秋天分口粮时,他把账本送到各队的会计手里,劳驾他们代扣。习惯成自然,也是一道朴素的乡风,多少年来从没人为豆腐账发生纠纷。那年月生活艰难,除了逢年过节,平时吃一回豆腐就如同吃肉一样,解馋过瘾。大忙季节,生产队会干夜工吃大锅饭,一锅白菜豆腐,凡是能干活的人都不会放过。最有名气的是陈家毛人大爷,每到这时,他的筷子就长了眼睛,尽拣豆腐叉,也不怕别人笑。谁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豆腐就是他的命。有一次快过年了生产队杀猪分肉。剩下的碎肉猪血和大白菜豆腐一锅烩,给帮忙杀猪的人聚餐,再打二斤山芋干酒热闹一下。遇上这好事当然少不了毛人大爷,饭菜一上桌,只见他的筷子迂回豆腐尽挑猪肉吃,别人问他:“毛人大爷今天怎么不吃豆腐了?”他便风趣地说:“我这个人见到肉,命都不要了。”
马家不但豆腐做得好,而且凉粉也地道,实打实的豌豆粉,弹性足。一到夏天,他一头豆腐一头凉粉挑着担子走村串户,没卖完的凉粉就挑到地头。记得有年夏天,在玉米堆上薅地,一趟地薅下来热得汗流浃背,男男女女坐在地头休息,实在受不了就到河边捧口水喝。这时,老马就会挑着凉粉来赶场子,担子一放下就被人们围了起来,妇女们舍不得吃,老男人大小伙却管不了,来上一碗又解渴又抵饿,反正都是记账,我一连吃了三碗,按斤算就是六斤,唉,那时也没什么作料,蒜泥水加一点酱油,酱油是香椿树叶晒出来的,吃到嘴里能回出香椿的清香。如今想起来,竟让我感慨万分,这么好吃的美味,再也吃不到了,记忆里的乡愁就是这么让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