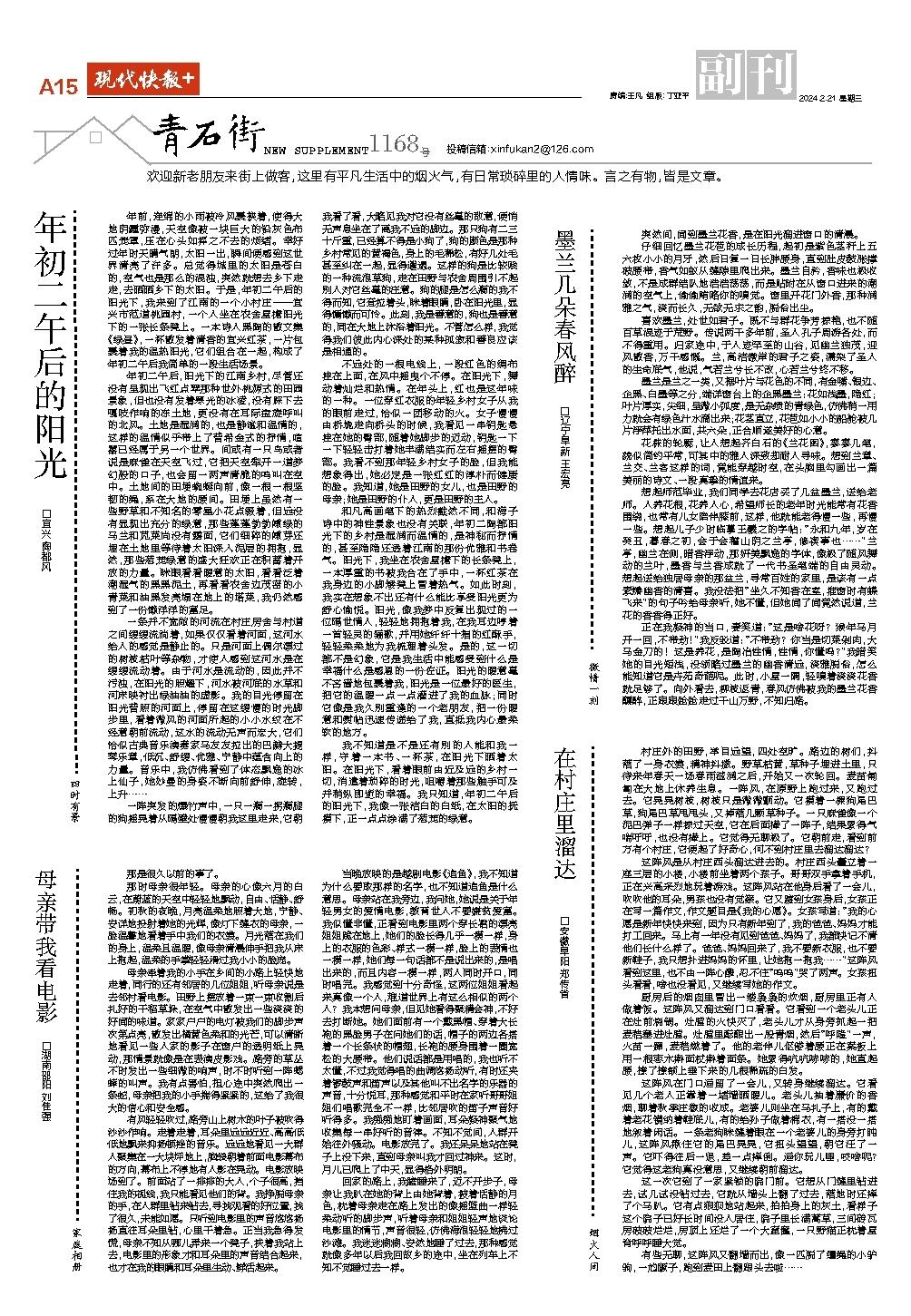□宜兴 陶都风
年前,连绵的小雨被冷风裹挟着,使得大地阴霾弥漫,天空像被一块巨大的铅灰色布匹笼罩,压在心头如挥之不去的烦绪。幸好过年时天晴气朗,太阳一出,瞬间便感到这世界清亮了许多。总觉得城里的太阳是苍白的,空气也是那么的混浊,突然就想去乡下走走,去晒晒乡下的太阳。于是,年初二午后的阳光下,我来到了江南的一个小村庄——宜兴市范道桃园村,一个人坐在农舍屋檐阳光下的一张长条凳上。一本诗人黑陶的散文集《绿昼》,一杯散发着清香的宜兴红茶,一片包裹着我的温热阳光,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年初二午后我简单的一段生活场景。
年初二午后,阳光下的江南乡村,尽管还没有呈现出飞红点翠那种世外桃源式的田园景象,但也没有发着寒光的冰凌,没有踩下去嘎吱作响的冻土地,更没有在耳际盘旋呼叫的北风。土地是湿润的,也是静谧和温情的,这样的温情似乎带上了普希金式的抒情,喧嚣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间或有一只鸟或者说是麻雀在天空飞过,它把天空犁开一道梦幻般的口子,也会留一两声清脆的鸣叫在空中。土地间的田埂蜿蜒向前,像一根一根坚韧的绳,系在大地的腰间。田埂上虽然有一些野草和不知名的零星小花点缀着,但远没有显现出充分的绿意,那些蓬蓬勃勃嫩绿的马兰和苋菜尚没有露面,它们细碎的嫩芽还埋在土地里等待着太阳深入泥层的拥抱,显然,那些葱茏绿意的盛大狂欢正在积蓄着开放的力量。眯眼看看暖意的太阳,看看泛着潮湿气的黑黑泥土,再看看农舍边茂密的小青菜和油黑发亮塌在地上的塔菜,我仍然感到了一份懒洋洋的富足。
一条并不宽敞的河流在村庄房舍与村道之间缓缓流淌着,如果仅仅看着河面,这河水给人的感觉是静止的。只是河面上偶尔漂过的树枝枯叶等杂物,才使人感到这河水是在缓缓流动着。由于河水是流动的,因此并不污浊,在阳光的照耀下,河水被河底的水草和河床映衬出绿油油的虚影。我的目光停留在阳光普照的河面上,停留在这缓慢的时光脚步里,看着微风的河面所起的小小水纹在不经意朝前流动,这水的流动无声而宏大,它们恰似古典音乐演奏家马友友拉出的巴赫大提琴乐章,低沉、舒缓、优雅、宁静中蕴含向上的力量。音乐中,我仿佛看到了体态飘逸的冰上仙子,她妙曼的身姿不断向前舒伸,旋转,上升……
一阵突发的爆竹声中,一只一瘸一拐瘸腿的狗摇晃着从隔壁处慢慢朝我这里走来,它朝我看了看,大略见我对它没有丝毫的敌意,便悄无声息坐在了离我不远的脚边。那只狗有二三十斤重,已经算不得是小狗了,狗的颜色是那种乡村常见的黄褐色,身上的毛稀松,有好几处毛甚至纠在一起,显得邋遢。这样的狗是比较贱的一种流浪草狗,走在田野与农舍周围引不起别人对它丝毫的注意。狗的腿是怎么瘸的我不得而知,它耷拉着头,眯着眼睛,卧在阳光里,显得慵懒而可怜。此刻,我是善意的,狗也是善意的,同在大地上沐浴着阳光。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彼此内心深处的某种孤寂和善良应该是相通的。
不远处的一根电线上,一段红色的绸布挂在上面,在风中摇曳个不停。在阳光下,舞动着灿烂和热情。在年头上,红也是这年味的一种。一位穿红衣服的年轻乡村女子从我的眼前走过,恰似一团移动的火。女子慢慢由桥堍走向桥头的时候,我看见一串钥匙悬挂在她的臀部,随着她脚步的迈动,钥匙一下一下轻轻击打着她丰满结实而左右摇摆的臀部。我看不到那年轻乡村女子的脸,但我能想象得出,她必定是一张红红的淳朴而健康的脸。我知道,她是田野的女儿,也是田野的母亲;她是田野的仆人,更是田野的主人。
和凡高画笔下的热烈截然不同,和海子诗中的神性景象也没有关联,年初二陶都阳光下的乡村是湿润而温情的,是神秘而抒情的,甚至隐隐还透着江南的那份优雅和书卷气。阳光下,我坐在农舍屋檐下的长条凳上,一本厚重的书被我合在了手中,一杯红茶在我身边的小脚矮凳上冒着热气。如此时刻,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能比享受阳光更为舒心愉悦。阳光,像我梦中反复出现过的一位隔世情人,轻轻地拥抱着我,在我耳边哼着一首轻灵的骊歌,并用她纤纤十指的红酥手,轻轻柔柔地为我梳理着头发。是的,这一切都不是幻象,它是我生活中能感受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感恩的一份佐证。阳光的暖意毫不吝啬地包裹着我,阳光是一位最好的医生,把它的温暖一点一点灌进了我的血脉;同时它像是我久别重逢的一个老朋友,把一份暖意和熨帖迅速传递给了我,直抵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人能和我一样,守着一本书、一杯茶,在阳光下晒着太阳。在阳光下,看着眼前由近及远的乡村一切,消遣着琐碎的时光,咀嚼着那些触手可及并稍纵即逝的幸福。我只知道,年初二午后的阳光下,我像一张洁白的白纸,在太阳的抚摸下,正一点点涂满了葱茏的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