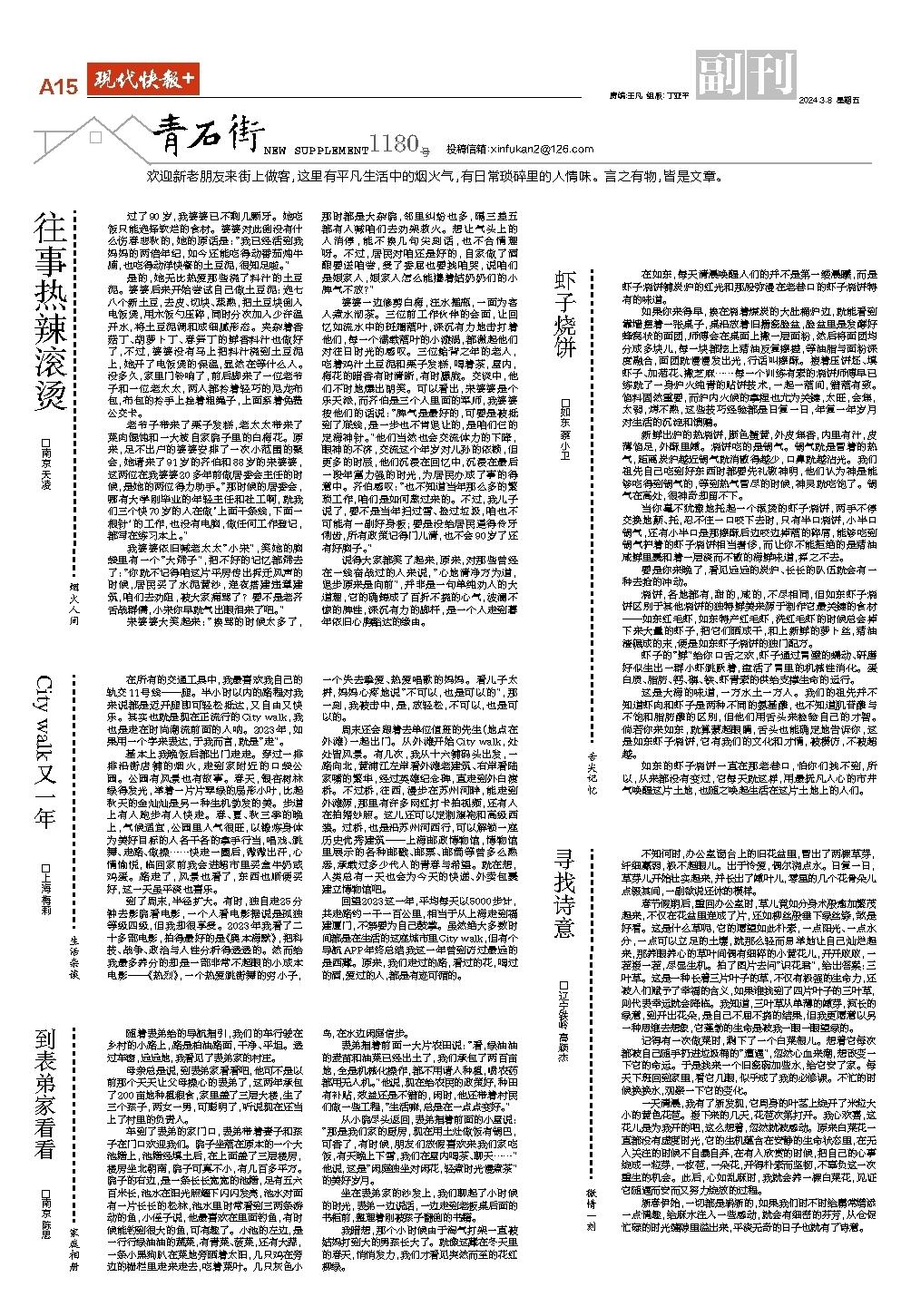□南京 天凌
过了90岁,我婆婆已不剩几颗牙。她吃饭只能选择软烂的食材。婆婆对此倒没有什么伤春悲秋的,她的原话是:“我已经活到我妈妈的两倍年纪,如今还能吃得动番茄炖牛腩,也吃得动洋快餐的土豆泥,很知足啦。”
是的,她无比热爱那些浇了料汁的土豆泥。婆婆后来开始尝试自己做土豆泥:选七八个新土豆,去皮、切块、蒸熟,把土豆块倒入电饭煲,用木饭勺压碎,同时分次加入少许温开水,将土豆泥调和成细腻形态。夹杂着香菇丁、胡萝卜丁、春笋丁的鲜香料汁也做好了,不过,婆婆没有马上把料汁浇到土豆泥上,她开了电饭煲的保温,显然在等什么人。没多久,家里门铃响了,前后脚来了一位老爷子和一位老太太,两人都拎着轻巧的尼龙布包,布包的拎手上拴着粗绳子,上面系着免费公交卡。
老爷子带来了栗子发糕,老太太带来了菜肉馄饨和一大枝自家院子里的白梅花。原来,足不出户的婆婆安排了一次小范围的聚会,她请来了91岁的齐伯和88岁的宋婆婆,这两位在我婆婆20多年前做居委会主任的时候,是她的两位得力助手。“那时候的居委会,哪有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主任和社工啊,就我们三个快70岁的人在做‘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工作,也没有电脑,做任何工作登记,都写在练习本上。”
我婆婆依旧喊老太太“小宋”,笑她的脑袋里有一个“大筛子”,把不好的记忆都筛去了:“你就不记得咱这片平房传出拆迁风声的时候,居民买了水泥黄沙,连夜搭建违章建筑,咱们去劝阻,被大家痛骂了?要不是老齐舌战群儒,小宋你早就气出眼泪来了吧。”
宋婆婆大笑起来:“挨骂的时候太多了,那时都是大杂院,邻里纠纷也多,隔三差五都有人喊咱们去劝架救火。想让气头上的人消停,能不挨几句尖刻话,也不合情理呀。不过,居民对咱还是好的,自家做了酒酿要送咱尝,受了委屈也要找咱哭,说咱们是娘家人,娘家人怎么能攥着姑奶奶们的小脾气不放?”
婆婆一边修剪白梅,注水插瓶,一面为客人煮水沏茶。三位前工作伙伴的会面,让回忆如流水中的斑斓落叶,深沉有力地击打着他们,每一个满载落叶的小漩涡,都激起他们对往日时光的感叹。三位鲐背之年的老人,吃着鸡汁土豆泥和栗子发糕,喝着茶,屋内,梅花的暗香有时清晰,有时朦胧。交谈中,他们不时地爆出朗笑。可以看出,宋婆婆是个乐天派,而齐伯是三个人里面的军师,我婆婆按他们的话说:“脾气是最好的,可要是被抵到了底线,是一步也不肯退让的,是咱们仨的定海神针。”他们当然也会交流体力的下降,眼神的不济,交流这个年岁对儿孙的依赖,但更多的时辰,他们沉浸在回忆中,沉浸在最后一段年富力强的时光,为居民办成了事的得意中。齐伯感叹:“也不知道当年那么多的繁琐工作,咱们是如何熬过来的。不过,我儿子说了,要不是当年扫过雪、捡过垃圾,咱也不可能有一副好身板;要是没给居民逼得伶牙俐齿,所有政策记得门儿清,也不会90岁了还有好脑子。”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原来,对那些曾经在一线奋战过的人来说,“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并非是一句单纯劝人的大道理,它的确铸成了百折不挠的心气,波澜不惊的脾性,深沉有力的脚杆,是一个人走到暮年依旧心胸豁达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