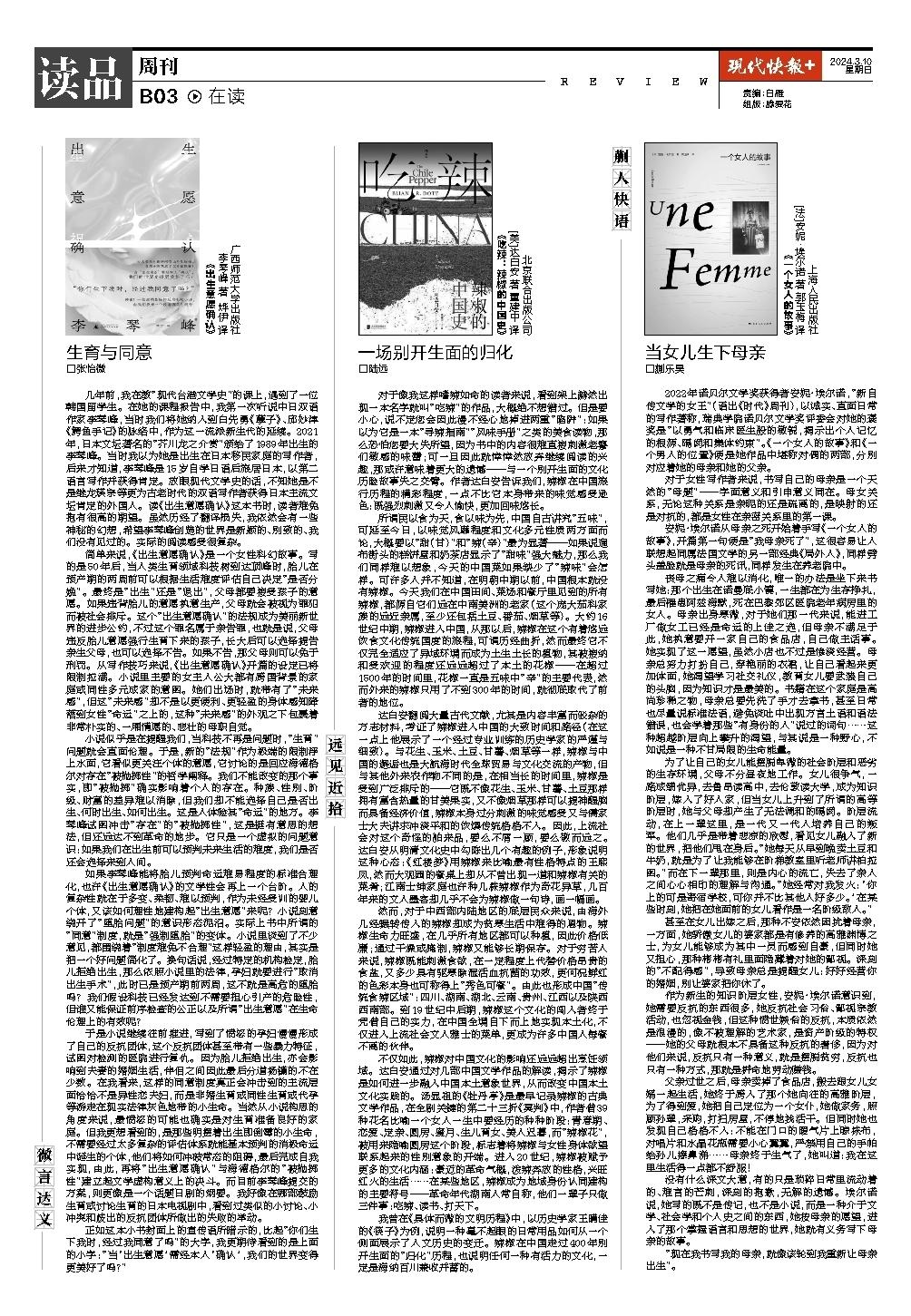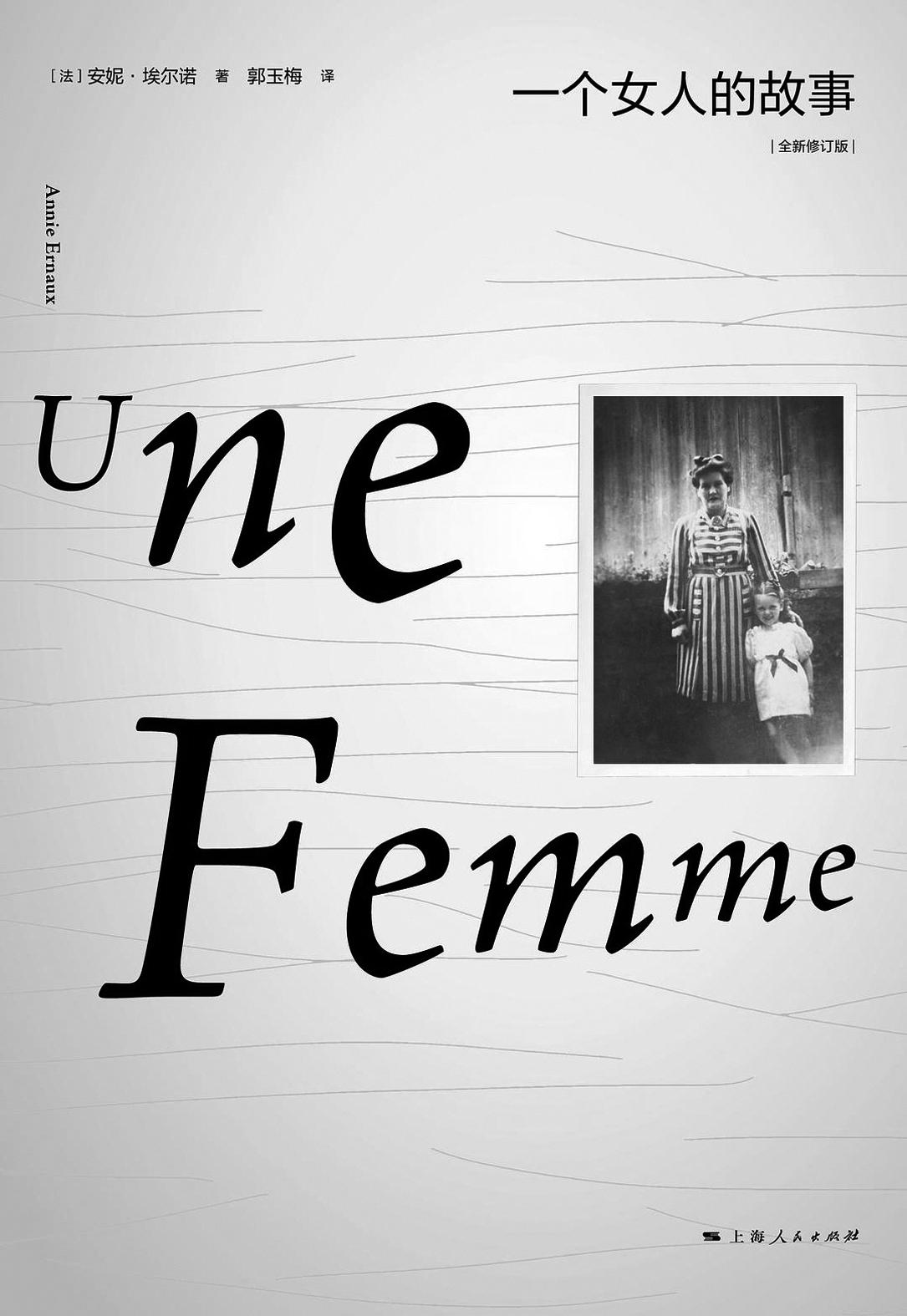□蒯乐昊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妮·埃尔诺,“新自传文学的女王”(语出《时代》周刊),以诚实、直面日常的写作著称,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她的褒奖是“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出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一个女人的故事》和《一个男人的位置》便是她作品中堪称对偶的两部,分别对应着她的母亲和她的父亲。
对于女性写作者来说,书写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天然的“母题”——字面意义和引申意义同在。母女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亲昵的还是疏离的,是映射的还是对抗的,都是女性在亲密关系里的第一课。
安妮·埃尔诺从母亲之死开始着手写《一个女人的故事》,开篇第一句便是“我母亲死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同属法国文学的另一部经典《局外人》,同样劈头盖脸就是母亲的死讯,同样发生在养老院中。
丧母之痛令人难以消化,唯一的办法是坐下来书写她:那个出生在诺曼底小镇,一生都在为生存挣扎,最后罹患阿兹海默,死在巴黎郊区医院老年病房里的女人。母亲出身寒微,对于她们那一代来说,能进工厂做女工已经是命运的上佳之选,但母亲不满足于此,她执意要开一家自己的食品店,自己做主话事。她实现了这一愿望,虽然小店也不过是惨淡经营。母亲总努力打扮自己,穿艳丽的衣裙,让自己看起来更加体面,她渴望学习社交礼仪,教育女儿要武装自己的头脑,因为知识才是最美的。书籍在这个家庭是高尚珍稀之物,母亲总要先洗了手才去拿书,甚至日常也尽量说标准法语,避免谈吐中出现方言土语和语法错误,也会学着那些“有身份的人”说过的词句……这种超越阶层向上攀升的渴望,与其说是一种野心,不如说是一种不甘局限的生命能量。
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能摆脱卑微的社会阶层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父母不分昼夜地工作。女儿很争气,一路成绩优异,去鲁昂读高中,去伦敦读大学,成为知识阶层,嫁入了好人家,但当女儿上升到了所谓的高等阶层时,她与父母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隔阂。阶层流动,在上一辈这里,是一代又一代人培养自己的叛军。他们几乎是带着悲凉的欣慰,看见女儿融入了新的世界,把他们甩在身后。“她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而在下一辈那里,则是内心的流亡,失去了亲人之间心心相印的理解与沟通。“她经常对我发火:‘你上的可是寄宿学校,可你并不比其他人好多少。’在某些时刻,她把在她面前的女儿看作是一名阶级敌人。”
甚至在女儿出嫁之后,那种不安依然困扰着母亲,一方面,她骄傲女儿的婆家都是有修养的高雅渊博之士,为女儿能够成为其中一员而感到自豪,但同时她又担心,那种彬彬有礼里面隐藏着对她的鄙视。深刻的“不配得感”,导致母亲总是提醒女儿:好好经营你的婚姻,别让婆家把你休了。
作为新生的知识阶层女性,安妮·埃尔诺意识到,她需要反抗的东西很多,她反抗社会习俗、鄙视宗教活动,也忽视金钱,但这种愤世嫉俗的反抗,本质依然是浪漫的,像不被理解的艺术家,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她的父母就根本不具备这种反抗的奢侈,因为对他们来说,反抗只有一种意义,就是摆脱贫穷,反抗也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拼命地劳动赚钱。
父亲过世之后,母亲卖掉了食品店,搬去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她终于跨入了那个她向往的高雅阶层,为了得到爱,她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女仆,她做家务,照顾孙辈,采购,打扫房屋,不停地找活干。但同时她也发现自己格格不入:不能在门口的暖气片上晾抹布,对唱片和水晶花瓶需要小心翼翼,严禁用自己的手帕给孙儿擦鼻涕……母亲终于生气了,她叫道:我在这里生活得一点都不舒服!
没有什么深文大意,有的只是琐碎日常里流动着的、难言的芒刺,深刻的抱歉,无解的遗憾。埃尔诺说,她写的既不是传记,也不是小说,而是一种介于文学、社会学和个人史之间的东西,她按母亲的愿望,进入了那个掌握语言和思想的世界,她就有义务写下母亲的故事。
“现在我书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