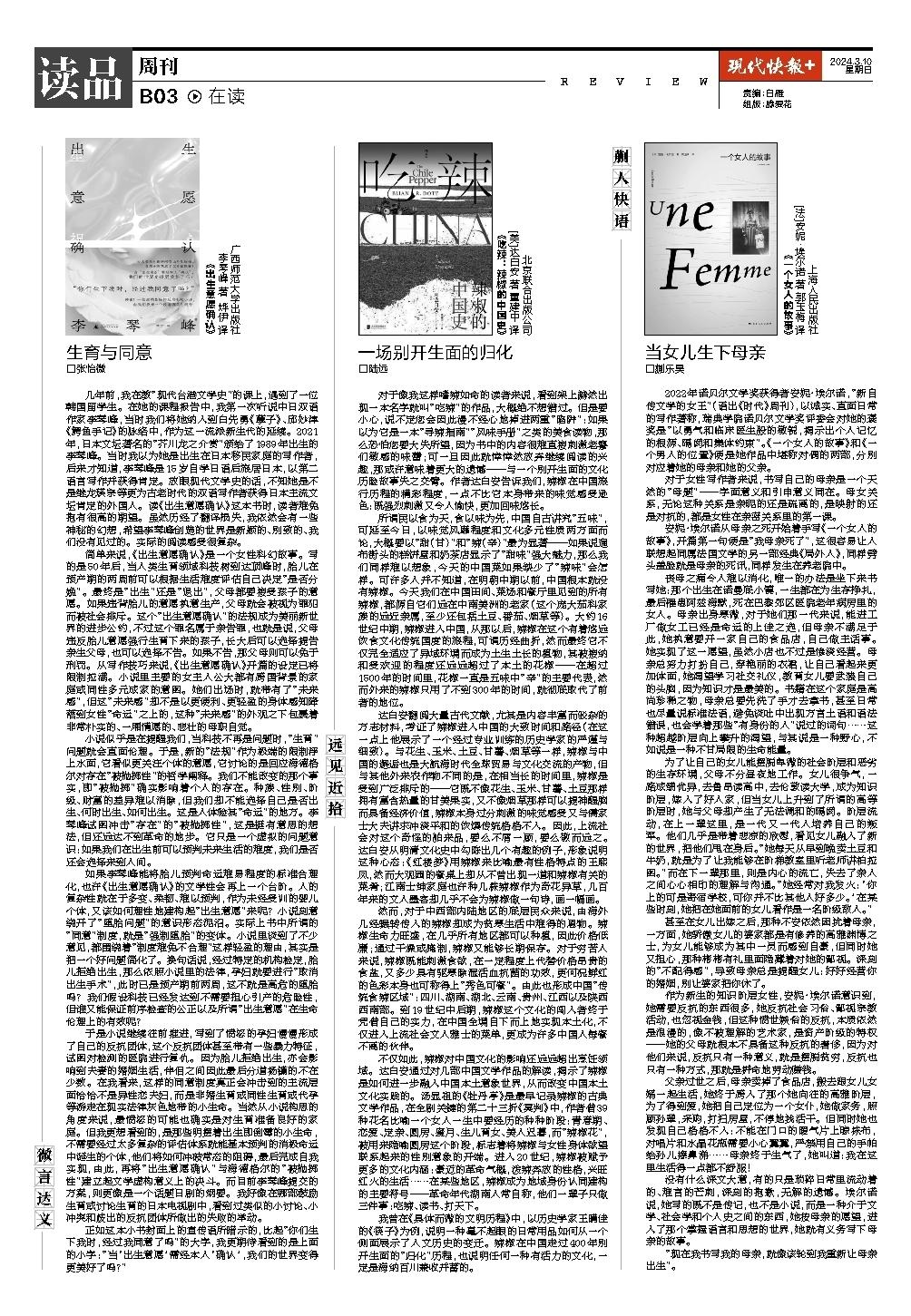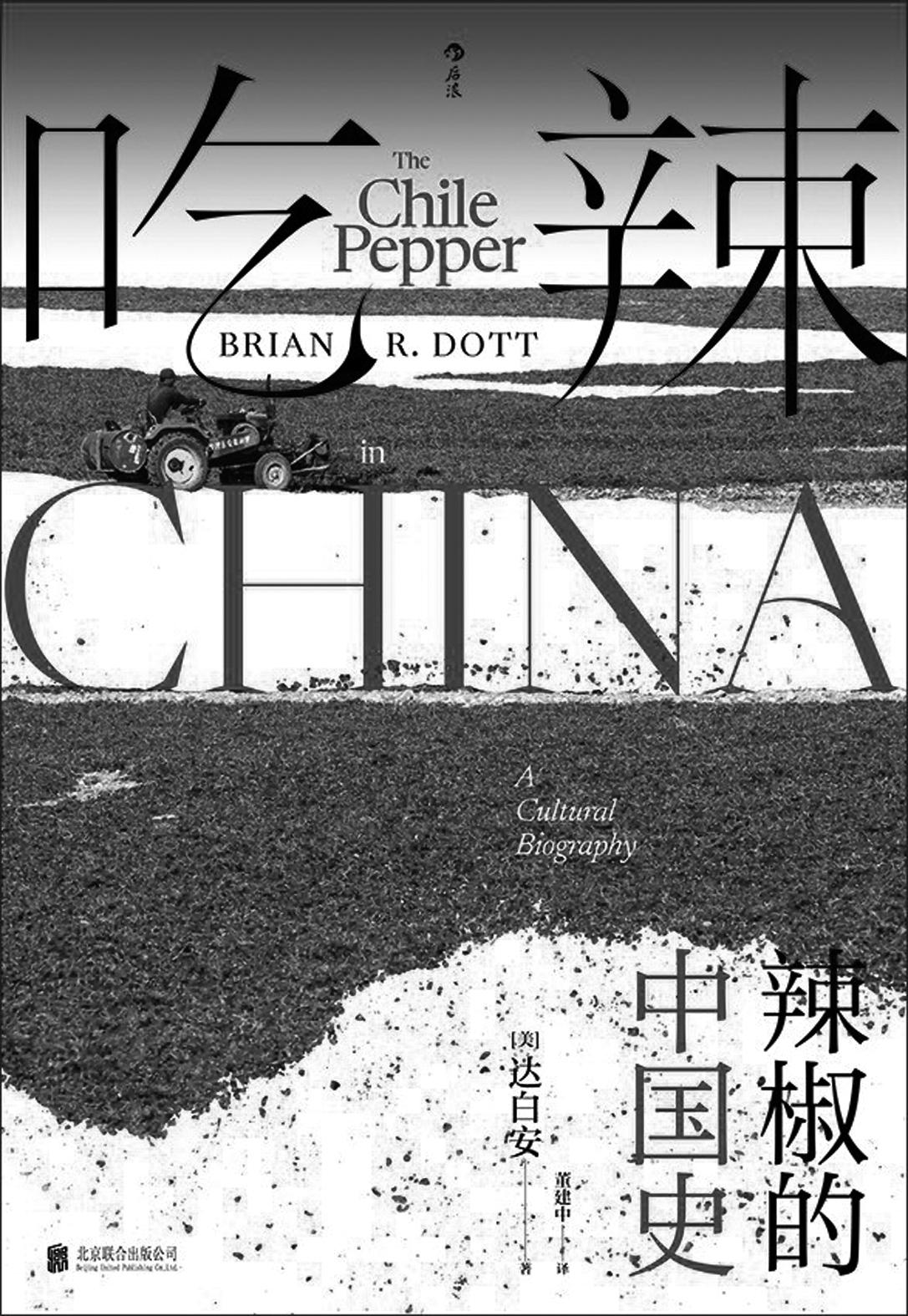□陆远
对于像我这样嗜辣如命的读者来说,看到架上赫然出现一本名字就叫“吃辣”的作品,大概绝不想错过。但是要小心,说不定您会因此漫不经心地掉进两重“陷阱”:如果以为它是一本“寻辣指南”“风味手册”之类的美食读物,那么恐怕您要大失所望,因为书中的内容很难直接刺激老饕们敏感的味蕾;可一旦因此就悻悻然放弃继续阅读的兴趣,那或许意味着更大的遗憾——与一个别开生面的文化历险故事失之交臂。作者达白安告诉我们,辣椒在中国旅行历程的精彩程度,一点不比它本身带来的味觉感受逊色:既强烈刺激又令人愉快,更加回味悠长。
所谓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中国自古讲究“五味”,可延至今日,以味觉风靡程度和文化多元性质两方面而论,大概要以“甜(甘)”和“辣(辛)”最为显著——如果说遍布街头的糕饼屋和奶茶店显示了“甜味”强大魅力,那么我们同样难以想象,今天的中国菜如果缺少了“辣味”会怎样。可许多人并不知道,在明朝中期以前,中国根本就没有辣椒。今天我们在中国田间、菜场和餐厅里见到的所有辣椒,都源自它们远在中南美洲的老家(这个庞大茄科家族的远近亲属,至少还包括土豆、番茄、烟草等)。大约16世纪中期,辣椒进入中国,从那以后,辣椒在这个有着悠远饮食文化传统国度的旅程,可谓历经曲折,然而最终它不仅完全适应了异域环境而成为土生土长的植物,其被接纳和受欢迎的程度还远远超过了本土的花椒——在超过1500年的时间里,花椒一直是五味中“辛”的主要代表,然而外来的辣椒只用了不到300年的时间,就彻底取代了前者的地位。
达白安翻阅大量古代文献,尤其是内容丰富而驳杂的方志材料,考证了辣椒进入中国的大致时间和路径(在这一点上他展示了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的严谨与细致)。与花生、玉米、土豆、甘薯、烟草等一样,辣椒与中国的邂逅也是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但与其他外来农作物不同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辣椒是受到广泛排斥的——它既不像花生、玉米、甘薯、土豆那样拥有富含热量的甘美果实,又不像烟草那样可以提神醒脑而具备经济价值,辣椒本身过分刺激的味觉感受又与儒家士大夫讲求冲淡平和的饮馔传统格格不入。因此,上流社会对这个奇怪的舶来品,要么不屑一顾,要么敬而远之。达白安从明清文化史中勾陈出几个有趣的例子,形象说明这种心态:《红楼梦》用辣椒来比喻最有性格特点的王熙凤,然而大观园的餐桌上却从不曾出现一道和辣椒有关的菜肴;江南士绅家庭也许种几株辣椒作为奇花异草,几百年来的文人墨客却几乎不会为辣椒做一句诗,画一幅画。
然而,对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底层民众来说,由海外几经辗转传入的辣椒却成为贫寒生活中难得的恩物。辣椒生命力旺盛,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可以种植,因此价格低廉;通过干燥或腌制,辣椒又能够长期保存。对于穷苦人来说,辣椒既能刺激食欲,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价格昂贵的食盐,又多少具有驱寒除湿活血抗菌的功效,更何况鲜红的色彩本身也可称得上“秀色可餐”。由此也形成中国“传统食辣区域”: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江西以及陕西西南部。到19世纪中后期,辣椒这个文化的闯入者终于凭借自己的实力,在中国全境自下而上地实现本土化,不仅进入上流社会文人雅士的菜单,更成为许多中国人每餐不离的伙伴。
不仅如此,辣椒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还远远超出烹饪领域。达白安通过对几部中国文学作品的解读,揭示了辣椒是如何进一步融入中国本土意象世界,从而改变中国本土文化实践的。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最早记录辣椒的古典文学作品,在全剧关键的第二十三折《冥判》中,作者借39种花名比喻一个女人一生中要经历的种种阶段:青春期、恋爱、定亲、圆房、蜜月、生儿育女、美人迟暮,而“辣椒花”,被用来隐喻圆房这个阶段,标志着将辣椒与女性身体欲望联系起来的性别意象的开端。进入20世纪,辣椒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豪迈的革命气概,泼辣奔放的性格,兴旺红火的生活……在某些地区,辣椒成为地域身份认同建构的主要符号——革命年代湖南人常自称,他们一辈子只做三件事:吃辣、读书、打天下。
我曾在《具体而微的文明历程》中,以历史学家王晴佳的《筷子》为例,说明一种毫不起眼的日常用品如何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人文历史的变迁。辣椒在中国走过400年别开生面的“归化”历程,也说明任何一种有活力的文化,一定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