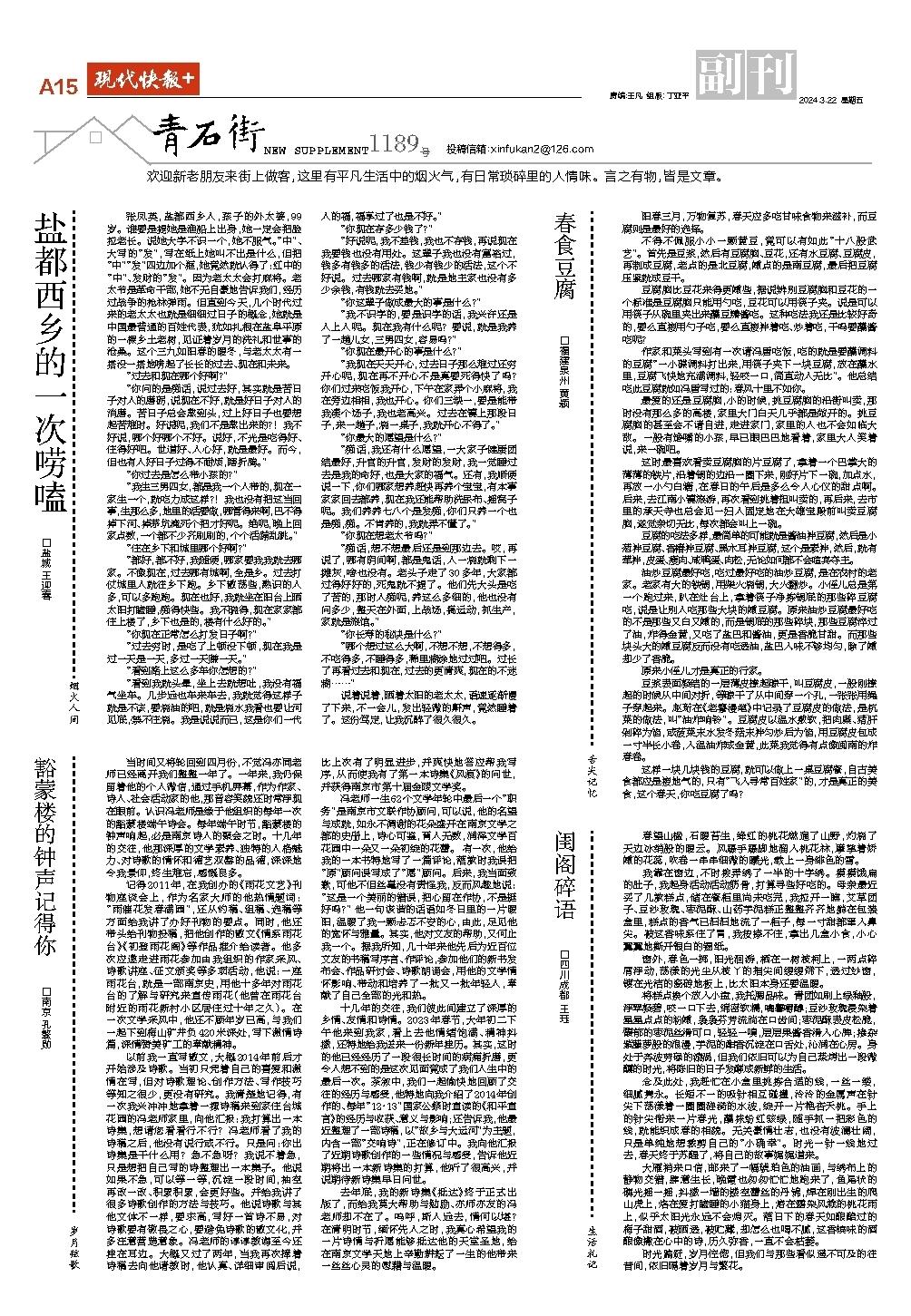□南京 孔繁勋
当时间又将轮回到四月份,不觉冯亦同老师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一年来,我仍保留着他的个人微信,通过手机屏幕,作为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的他,那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眼前。认识冯老师是缘于他组织的每年一次的豁蒙楼端午诗会。每年端午时节,豁蒙楼的钟声响起,必是南京诗人的聚会之时。十几年的交往,他那深厚的文学素养、独特的人格魅力、对诗歌的情怀和德艺双罄的品德,深深地令我景仰,终生难忘,感慨良多。
记得2011年,在我创办的《雨花文艺》刊物座谈会上,作为名家大师的他热情题词:“雨催花发春满园”,还从约稿、组稿、选稿等方面给我讲了办好刊物的要点。同时,他还带头给刊物投稿,把他创作的散文《情系雨花台》《初登雨花阁》等作品推介给读者。他多次应邀走进雨花参加由我组织的作家采风、诗歌讲座、征文颁奖等多项活动,他说:一座雨花台,就是一部南京史,用他十多年对雨花台的了解与研究来宣传雨花(他曾在雨花台附近的雨花新村小区居住过十年之久)。在一次文学采风中,他还不顾年岁已高,与我们一起下到梅山矿井负420米深处,写下激情诗篇,深情赞美矿工的奉献精神。
以前我一直写散文,大概2014年前后才开始涉及诗歌。当初只凭着自己的喜爱和激情在写,但对诗歌理论、创作方法、写作技巧等知之很少,更没有研究。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兴冲冲地拿着一摞诗稿来到家住台城花园的冯老师家里,向他汇报:我打算出一本诗集,想请您看看行不行?冯老师看了我的诗稿之后,他没有说行或不行。只是问:你出诗集是干什么用?急不急呀?我说不着急,只是想把自己写的诗整理出一本集子。他说如果不急,可以等一等,沉淀一段时间,抽空再改一改、积累积累,会更好些。并给我讲了很多诗歌创作的方法与技巧。他说诗歌与其他文体不一样,要求高,写好一首诗不易,对诗歌要有敬畏之心,要避免诗歌的散文化,并多注意营造意象。冯老师的谆谆教诲至今还挂在耳边。大概又过了两年,当我再次捧着诗稿去向他请教时,他认真、详细审阅后说,比上次有了明显进步,并爽快地答应帮我写序,从而使我有了第一本诗集《风痕》的问世,并获得南京市第十届金陵文学奖。
冯老师一生62个文学年轮中最后一个“职务”是南京市文联作协顾问,可以说,他的名望与成就,如永不凋谢的花朵盛开在南京文学之都的史册上,诗心可鉴,育人无数,润泽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又一朵初绽的花蕾。 有一次,他给我的一本书特地写了一篇评论,落款时我误把“原”顾问误写成了“愿”顾问。后来,我当面致歉,可他不但丝毫没有责怪我,反而风趣地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把心留在作协,不是挺好吗?” 他一句诙谐的话语如冬日里的一片暧阳,温暧了我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由此,足见他的宽怀与雅量。其实,他对文友的帮助,又何止我一个。据我所知,几十年来他先后为近百位文友的书稿写序言、作评论,参加他们的新书发布会、作品研讨会、诗歌朗诵会,用他的文学情怀影响、带动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光和热。
十几年的交往,我们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乡情、友情和诗情。2023年春节,大年初二下午他来到我家,看上去他情绪饱满、精神抖擞,还特地给我送来一份新年挂历。其实,这时的他已经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病痛折磨,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茶叙中,我们一起愉快地回顾了交往的经历与感受,他特地向我介绍了2014年创作的、每年“12·13”国家公祭时宣读的《和平宣言》的经历与收获、意义与影响;还告诉我,他最近整理了一部诗稿,以“故乡与大运河”为主题,内含一部“交响诗”,正在修订中。我向他汇报了近期诗歌创作的一些情况与感受,告诉他近期将出一本新诗集的打算,他听了很高兴,并说期待新诗集早日问世。
去年底,我的新诗集《抵达》终于正式出版了,而给我莫大帮助与勉励、亦师亦友的冯老师却不在了。呜呼,斯人远去,情何以堪?在清明时节,缅怀先人之时,我真心希望我的一片诗情与祈愿能够抵达他的天堂圣地,给在南京文学天地上辛勤耕耘了一生的他带来一丝丝心灵的慰藉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