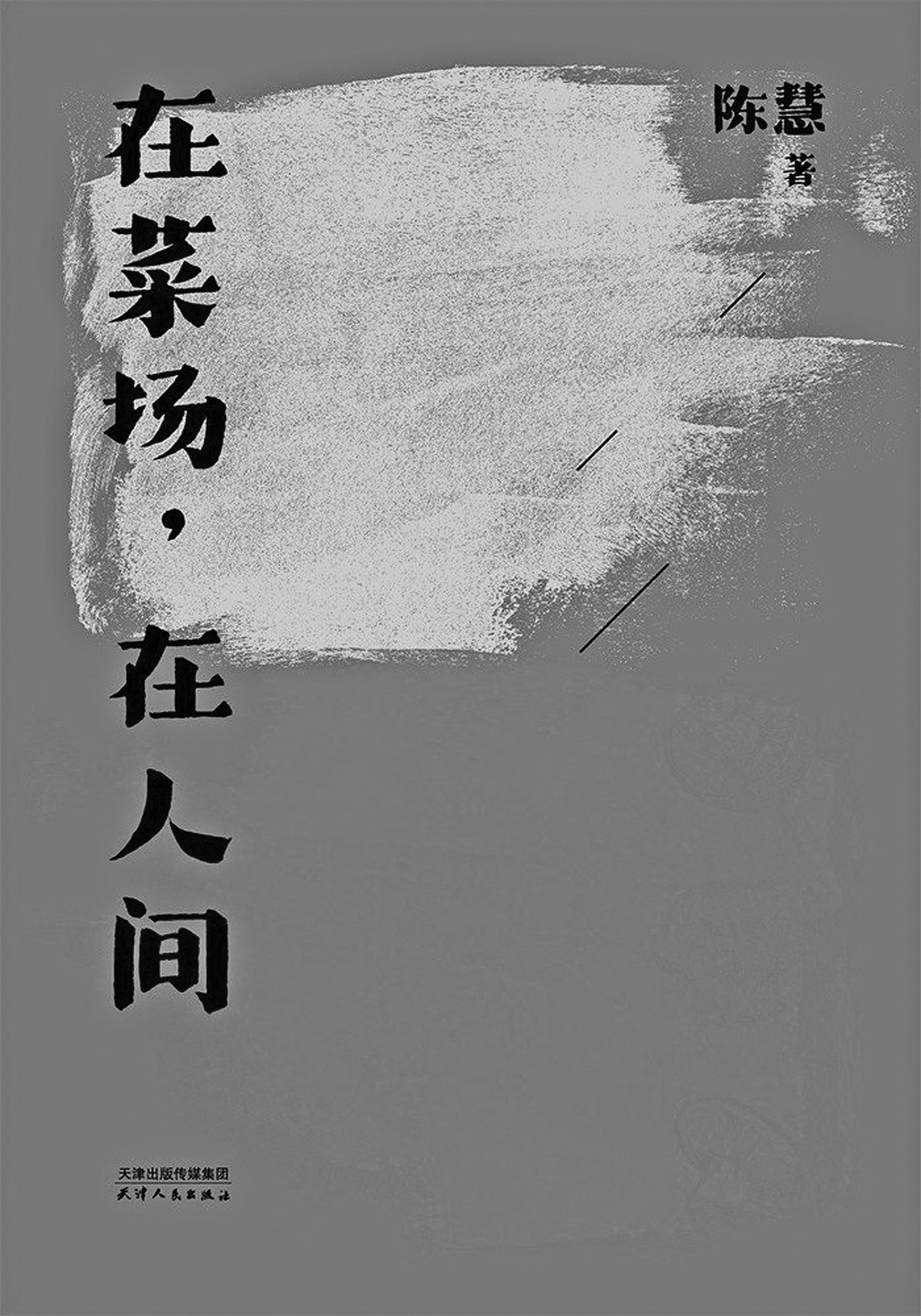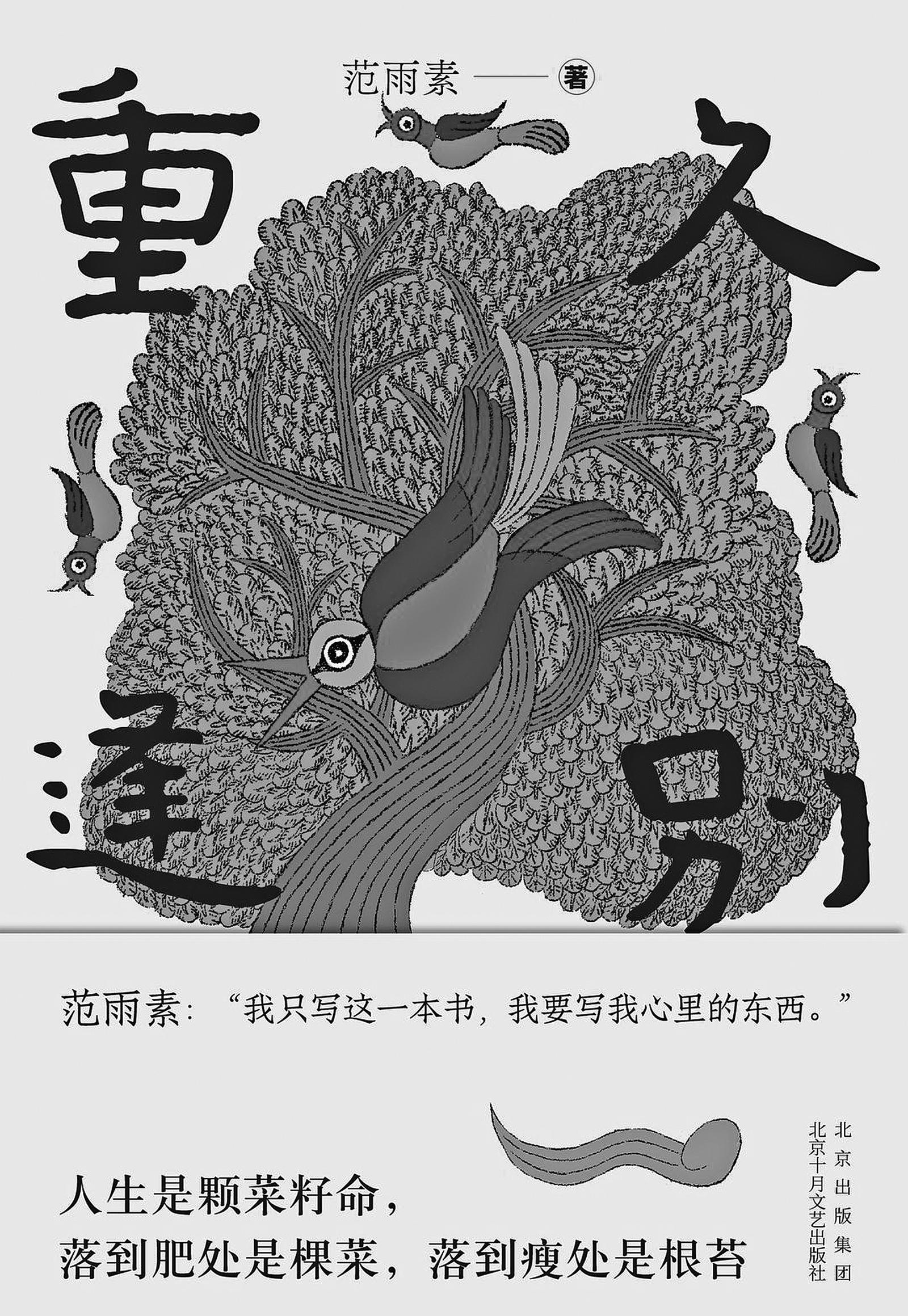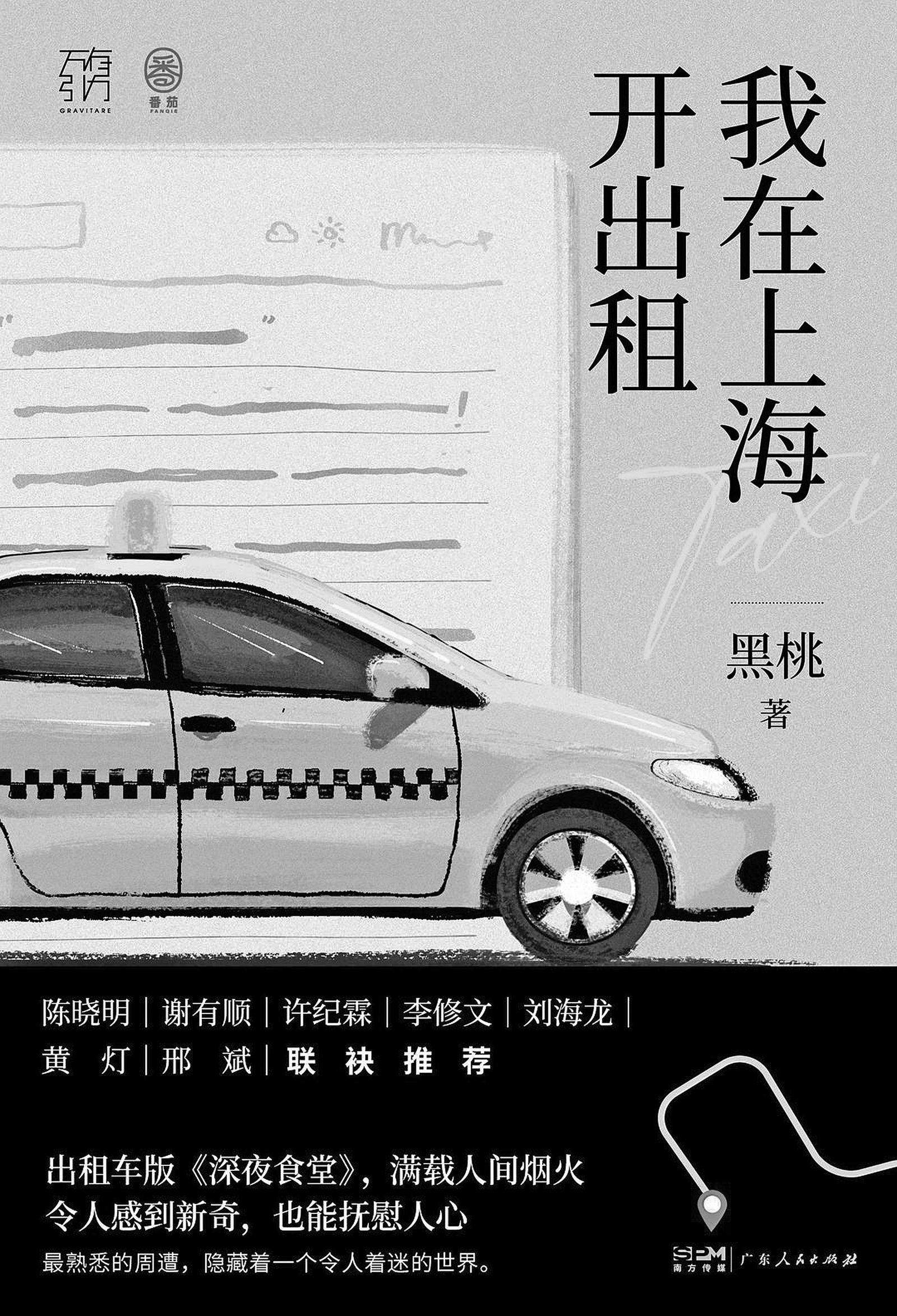菜场小贩陈慧,用文字记录市井百态;的哥黑桃,听形形色色的乘客讲故事,用文字重建正在消失的附近;家政工范雨素,借助文学在想象和现实中穿梭……近年来,越来越多来自不同行业、没有受过专业文学训练的写作者们,用朴素真挚的文字打动了广大读者。他们的写作,被冠以“素人写作”之名,成为当下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
在豆瓣2023年度读书榜单的10本年度图书中,“快递小哥”胡安焉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均在列。10位年度作家中,杨本芬、胡安焉入榜。“矿工作家”陈年喜、“农民作家”单小花、“煤矿诗人”榆木……去年10月,多位“素人作家”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正式会员。
为什么“素人写作”在近年来不断涌现、火爆出圈?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
“沉默的大多数”成为能言者
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素人作家”涌现的时间线。2015年,只上过一年半学的农村老太太秦秀英出版了《胡麻的天空》。2019年,矿工陈年喜出版首部诗集《炸裂志》。2020年,80岁的退休工人杨本芬推出处女作《秋园》。
“素人”出书渐成潮流是在近三年。上述3位作者在第一本书出版后,陆续推出新的作品。还有更多的“素人作者”推出第一本书。2022年,曾火爆全网的育儿嫂范雨素推出自传体长篇小说《久别重逢》,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村妇女裴爱民的日记被编辑成《田鼠大婶的日记》。2023年则可以说是“素人写作”的大年,在《文艺报》总结的几大年度关键词中,“被标注的身份/写作者”“素人写作”赫然在列。
素人,即平常人、普通人。“素人”一词,最初出现于娱乐综艺节目,节目里经常称被临时请来的、不是娱乐圈的普通人为“素人”。“素人作家”,则指非文学专业背景的普通人,他们无意于全面分析和思考社会,更多是记录日常的点滴和甘苦,讲述不易被看见的个体故事。也有人将这种写作称为“人间写作”“基层写作”。
更多人质疑“素人作家”这种提法,毕竟大部分作家在写作之初都是素人,莫言起初是士兵,余华曾是牙医,卡夫卡是保险公司职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注意到,“只有无业、低收入群体或者传统意义的劳动者,才标注出职业,被选择性关注,也反映出大众传媒、出版和文学界命名能力的贫乏。但即便如此,文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事业已是事实,这部分写作者被看到和注意,拓展了今天中国文学的版图。”
陈慧是“素人作家”中的一员。2021年,她的散文集《世间的小儿女》推出时,有推荐语说她“仅仅是把写作当成日常生活的一个出口,是忙碌之余的消遣,但正是因为如此,她的文字才有了一种特别的从容、不功利和不雕琢,如同清水芙蓉”。
陈慧是江苏南通如皋人,幼年时被送养、少年生病,27岁时嫁到浙江余姚,中年离异……为了生计,在孩子九个月大的时候,她将一辆儿童车改造成简易手推小“货车”,车上摆满了单价几块钱、利润微薄的生活用品。在菜市场摆摊至今的18年里,陈慧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相逢过无数小人物的命运,她选择用文字记录下生活的感悟与点滴。第二本散文集出版之后,陈慧上了央视,还被不少平台邀请开直播,但她并没有被流量裹挟,仍然在菜市场摆摊,仍然将写作“当成日常生活中一件有趣的事”。
黑桃是河南南阳人,曾在上海开出租车。这些年来,他遇到很多乘客,成为他们故事的倾听者。他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发表,被读者称为出租车版的《深夜食堂》。
在写作中,黑桃有意识地跟萍水相逢的人建立联系。文学除了可以当自己的精神寄托,还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在个体与个体间重建正在消失的附近。他观察到,现在这个世界有一些割裂,有普遍性的孤独,大家面对的是网络另一端的人,总看不到表情。而在出租车上,和乘客彼此陌生,难得有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时刻值得被记录。
“真实”与“敞开”,是“素人写作”引发讨论的高频关键词。《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留言:“谢谢你把我们的经历写出来”“当小人物拿起笔,整个世界都敞开了”“各行各业都不容易,正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真实体验才会如此感人”……在作家肖复兴看来,读这些作品犹如“见多吃多了装潢豪华的餐厅里的商务餐后,到乡间大集尝尝锅气和烟火气十足的家常菜,会感受到不尽相同的味道。”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项静认为,从实践效果来看,“素人写作”往往能够形成对时代精英写作的反拨和校正。当“沉默的大多数”成为能言者,从四面八方发出声音,哪怕粗糙却真切原生,汇成世间万象的平民手记,非虚构文学便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社会空间。
新媒体助推背后,是纯粹与坚持
事实上,“素人作家”的涌现并不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他们一直在写,只是很难被大众看见。当新媒体发挥力量,固有的传播局面终于开始松动。
近十年来,中国重要的门户网站创办了众多非虚构写作平台,如腾讯新闻的“谷雨故事”、网易的 “人间 the Livings”、界面的“正午故事”“真实故事计划”,以及“澎湃·镜相”“中国三明治”“ONE 实验室”等等,刊发了大量素人写作者书写的自身和他人的故事。
2017年,范雨素在微信公众号“正午故事”发表自传体叙事非虚构作品《我是范雨素》,在不到 24 小时的时间里,文章就引来了10万+的点击,并在各种媒介社交平台广泛流传。《我在北京送快递》的编辑普照,最初是在豆瓣看到胡安焉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受到关注与热议,便留了心,后又发现《在上海打工的回忆》一文,才生出了向胡安焉约稿的想法。
也有人会质疑,这种由新媒体“包抄”,因“贴标签”而获得人气的写作是不是在走捷径。实际上,对出版社来说,为素人“做嫁衣”的风险系数较高。很多素人作者花费数年心血完成的书稿,或因为选题不对路、或缺乏出版经验就此夭折,素人出书的门槛只会更高。身份反差不会直接导向图书购买行为,文字的品质与共情才能触发购买和阅读,打动人心的终究是体悟生活的内在力量。
很多出圈的“素人作家”,其实是一直坚持阅读和写作,最终厚积而薄发的结果。王计兵在诗集《赶时间的人》出版前就是文学青年。用他自己的话说,19岁时外出打工,晚间工友去逛公园,他就在路边旧书摊看免费书。偶然在杂志上看到投稿地址,他就发表了小小说处女作《小车进村》。范雨素在访谈中多次提到,她对读书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痴迷”,她曾到废品站给女儿买几斤书,认为“一本书从来没有人看过,跟一个人从没有好好活过一样,看着心疼”。《久别重逢》反复回忆童年时大哥哥、大姐姐读书、背书的场景,而且支撑“我”出走的动力以及出走的方向,全部来自于阅读和书的暗示。
这些“素人作家”在纸箱、废报纸上写,在弥漫着消毒水味的清洁间写,在纷扰喧嚣的仓库中写,在满是油烟的厨房写,在地底的矿道深处写……对他们来说,写作是出于纯粹的热爱,是自我纾解情绪的一种方式,没有太多功利色彩。
陈慧说,“我不是在文学作品当中体验生活,我是真正地在生活里面”,大家总认为文学是很高尚的东西,陈慧倒觉得文学不一定要在殿堂上,它随时随地化入生活浸润着我们,就像她出摊的时候,空了就随手掏出书读一读。在某次访谈中,胡安焉表示,他并不打算成为全职作家,“出于一种保护自己写作纯粹性的本能——我不希望自己的写作要去满足更多期待、要求或规限。”
《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出版方认为,编辑要创造条件尽量延长“素人作家”的创作生命。“素人写作”的魅力或许恰恰在于,他们不是程式化的专业作家,不遵循商业化道路,也没有“攀登高峰”的雄心,他们的写作更多是出自内心需要。这批“田野写作者”如同一棵长在哪里的树,就顺势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子。
延续平民文学的传统
其实,文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与普罗大众脱节的。源于《诗经》的脚踏实地、朴素自然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直贯穿于中国文坛。五四新文学发轫之时,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梳理过白话文学的线索,其中包含着对“素人”文学资源、生活经验和阅读的关照。鲁迅把平民的文学看作是未来中国文学:“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
这一文学理念绵延深远,1920年代中后期、1930年代的“革命文学”“文学大众化”;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出现的 “真人真事”写作,新中国成立后对工农兵作者的培养,及至21世纪初期的打工作家和底层书写等等。“素人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五四”时期鲁迅和对平民文学的期待,创作出了与“读书人”有差异的文学世界,让读者感受到来自民间文学蓬勃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可贵的回归。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项静指出,备受关注的“素人作家”们能否更进一步提升写作技术,在生活素材上保持对读者的吸引力和新鲜感,是他们接下来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在这些关卡上,每一步看似的前进恰恰可能是陷入窠臼,这是素人写作必须面对的悖论式困境,立足对纯文学反思的非虚构写作,反而又回撤到纯文学的机制中。”
陆续发表多篇作品的陈年喜,近几年对写作开始生出危机和瓶颈感。他在访谈中承认自己的创作故事性不足,缺乏技巧性,“全凭感觉在写”。另一方面是写作的持续性和重复的问题,乡村回忆和矿工故事之外,陈年喜期待自己的非虚构写作能够更进一步,尝试作为单纯叙事者书写他人的生活,比如《南地十年》《小城里的文人们》等,但由于缺乏调研能力,这几个故事比较平白,未达到他期待的效果,“没有新的体验,新的思考”。
范雨素的走红证明她的真实经历是最宝贵的东西,也是大众愿意看的,但她拒绝继续书写这些内容,出人意料地出版了一部科幻小说《久别重逢》。书中,范雨素从前世今生的角度,在突破界限的叙事中,强调了她对人类的平等的诉求。这本书故事性不强,写法有点像中国古典小说,以人物为核心,一个人物连着另一个人物、一个地方连着另一个地方,用散点、蔓延的方式把很多人与事串起来。但根据豆瓣评论区的反馈来看,读者们喜欢的还是书中涉及现实的部分。
当然,比起文学性,通过写作表达自我,与他人交流,呈现更广阔、更复杂的社会生活,这可能是“素人写作”更重要的价值。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多年来一直为包括范雨素在内的“皮村文学小组”提供支持,在他看来,“素人写作”有三重社会效应:“一是写作改造了主体,让落后的、愚昧的群众变成能够言说/书写的现代主体;二是写作改造大众媒介,使得单向传播的报纸变成具有参与感和互动性的双向媒体;三是写作改造了基层社会,以写作为媒介的基层传播塑造了基层组织内部的社会性和有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