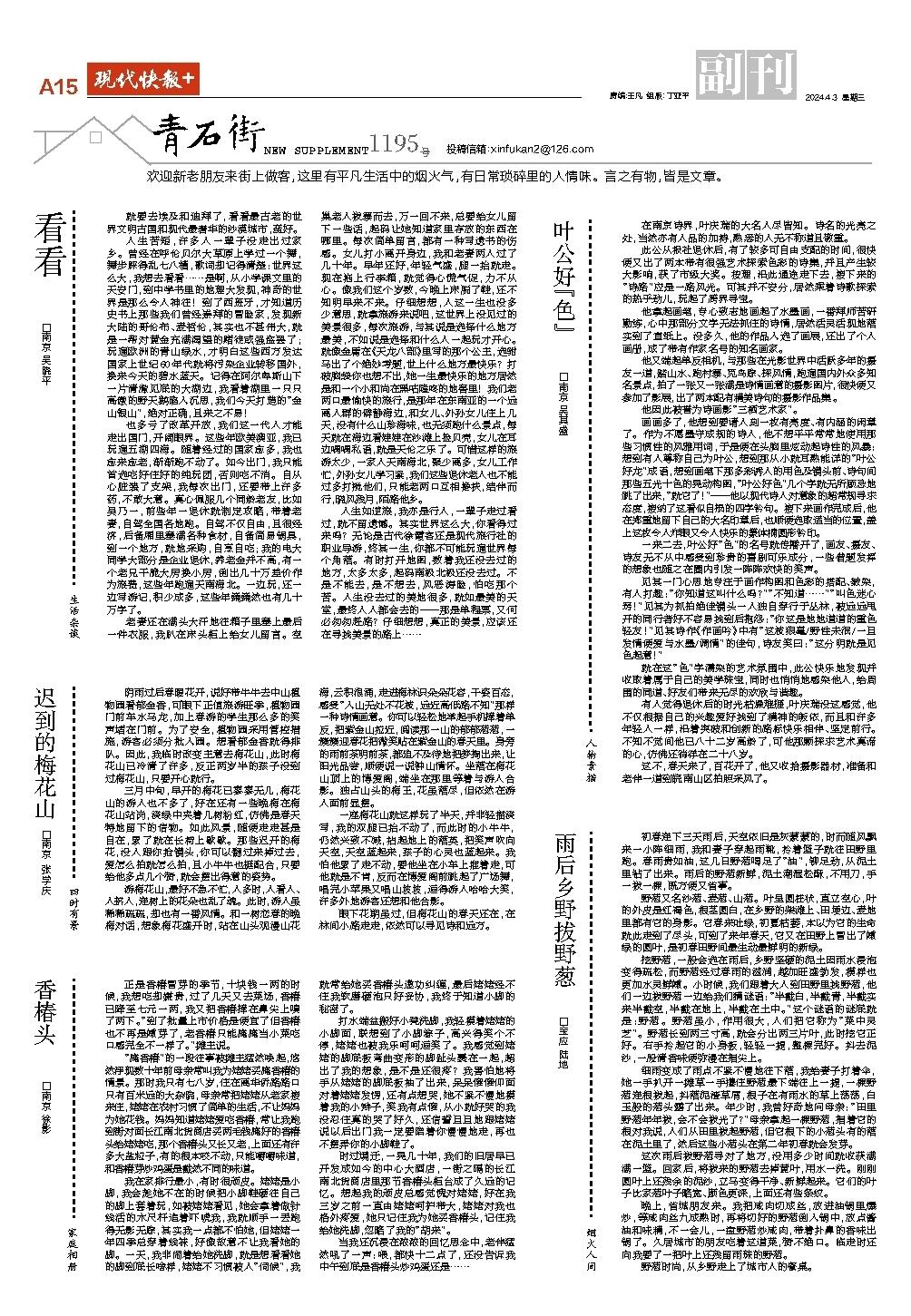□南京 徐影
正是香椿冒芽的季节,十块钱一两的时候,我想吃却嫌贵,过了几天又去菜场,香椿已降至七元一两,我又把香椿捧在鼻尖上嗅了两下。“到了批量上市价格是便宜了但香椿也不再是嫩芽了,老香椿只能腌腌当小菜吃口感完全不一样了。”摊主说。
“腌香椿”的一段往事被摊主猛然唤起,悠然浮现数十年前母亲常叫我为姥姥买腌香椿的情景。那时我只有七八岁,住在离华侨路路口只有百米远的大杂院,母亲常把姥姥从老家接来住,姥姥在农村习惯了简单的生活,不让妈妈为她花钱。妈妈知道姥姥爱吃香椿,常让我跑到街对面长江南北货商店买两毛钱腌好的香椿头给姥姥吃,那个香椿头又长又老,上面还有许多大盐粒子,有的根本咬不动,只能嚼嚼味道,和香椿芽炒鸡蛋是截然不同的味道。
我在家排行最小,有时很顽皮。姥姥是小脚,我会趁她不在的时候把小脚鞋硬往自己的脚上套着玩,如被姥姥看见,她会拿着做针线活的木尺杆追着吓唬我,我就顺手一丢跑得无影无踪,其实我一点都不怕她,但姥姥一年四季总穿着线袜,好像故意不让我看她的脚。一天,我非闹着给她洗脚,就是想看看她的脚到底长啥样,姥姥不习惯被人“伺候”,我就常给她买香椿头邀功纠缠,最后姥姥经不住我软磨硬泡只好妥协,我终于知道小脚的秘密了。
打水端盆搬好小凳洗脚,我轻摸着姥姥的小脚面,联想到了小脚粽子,高兴得笑个不停,姥姥也被我乐呵呵逗笑了。我感觉到姥姥的脚底板弯曲变形的脚趾头裹在一起,超出了我的想象,是不是还很疼?我害怕地将手从姥姥的脚底板抽了出来,呆呆傻傻仰面对着姥姥发愣,还有点想哭,她不紧不慢地摸着我的小辫子,笑我有点傻,从小就好哭的我没忍住真的哭了好久,还信誓旦旦地跟姥姥说以后出门我一定要陪着你慢慢地走,再也不摆弄你的小脚鞋了。
时过境迁,一晃几十年,我们的旧居早已开发成如今的中心大酒店,一街之隔的长江南北货商店里那节香椿头柜台成了久远的记忆。想起我的顽皮总感觉愧对姥姥,好在我三岁之前一直由姥姥呵护带大,姥姥对我也格外疼爱,她只记住我为她买香椿头,记住我给她洗脚,忽略了我的“胡来”。
当我还沉浸在浓浓的回忆思念中,老伴猛然吼了一声:喂,都快十二点了,还没告诉我中午到底是香椿头炒鸡蛋还是……